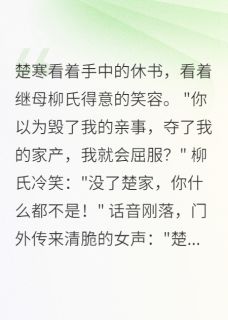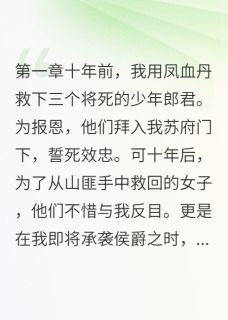北京出租屋的晨光里,还飘着昨夜没散尽的喜糖甜香。窗台上的红双喜剪纸被风吹得轻轻晃,阿燕正把楚南带来的腊鱼切成小块,准备塞进冰箱——那是母亲硬塞给她的,说“晋北没有这口鲜”。
阿明从身后轻轻抱住她,下巴抵在她肩上。新婚的羞涩还没褪尽,他的声音带着点刚睡醒的沙哑:“别忙了,今天不上班,歇会儿。”
“不忙哪行,”阿燕转过身,鼻尖蹭到他胸口,“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了,得拾掇得像个样子。”
阿明看着她眼里的光,忽然松开手,往床头柜走去。他从钱包里抽出一张银行卡,捏在手里摩挲了半天,像捧着什么滚烫的东西。
“阿燕,这个给你。”他把卡递过去,指尖微微发颤。
是他的工资卡。北漂三年,这张卡是他在这座城市立足的凭证,也是他藏着自卑与骄傲的角落。此刻递出去,像交出了自己的半个世界。
阿燕愣了一下,没接:“给**嘛?你自己拿着方便。”
“家里你做主。”阿明的语气很认真,带着点不容置疑的执拗,“我花钱大手大脚惯了,以前才欠了债。现在有你管着,我放心。”
他顿了顿,看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以后家里的钱,怎么花,存多少,都听你的。我就负责好好上班挣钱。”
阿燕的心跳漏了一拍。这张小小的卡片,比任何情话都实在。它不是楚南的银饰,也不是晋北的彩礼,是一个男人把日子交托给她的信任。她想起自己放弃编制远嫁时的决心,想起母亲塞给她银锁片时的叮嘱,眼眶忽然有点热。
“那你留着点零花钱,”她接过卡,指尖触到他的温度,“同事聚餐什么的,总不能没钱。”
“不用,”阿明笑了,左脸颊的疤痕在晨光里柔和了些,“我没什么应酬,公司管饭,花不着啥钱。”
阿燕把卡放进自己的钱包,压在最里层,贴着楚南带回来的全家福照片。她拿出手机,点开备忘录,认真地问:“里面现在有多少?我记一下。”
“上个月工资刚发,扣完社保还剩八千七,”阿明报出数字,又补充道,“年终奖估计下个月发,能有个三万多。”
阿燕在屏幕上敲下“8700”,后面画了个小小的存钱罐表情。她盯着数字看了会儿,忽然抬头笑了:“等年终奖发了,加上彩礼剩下的钱,我们就能凑个小首付的零头了。”
“不急,”阿明摸了摸她的头发,“你怀着孕,别太累。钱慢慢赚,房子总会有的。”
“得急,”阿燕晃了晃手机,“我算过了,每月除了房租和生活费,能存五千。年终奖存起来,再加上你的公积金,三年,最多三年,我们就能在燕郊付个首付了。”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像藏着星星,把未来的日子算得清清楚楚。阿明看着她认真的样子,忽然觉得那十万块负债、两地的差异、父母的不解,都不算什么了。
有个人愿意陪着你,把日子掰开揉碎了规划,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为了一个共同的家努力,这大概就是婚姻最好的样子。
阿燕把钱包放进抽屉,钥匙串上挂着的楚南银锁片轻轻碰撞,发出细碎的响。她转身抱住阿明,下巴抵在他胸口:“放心吧,我会管好孩子,也会管好钱,等我们有了自己的房子,就把墙上的照片都换成我们一家三口的。”
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在地板上投下一道暖光。那张小小的工资卡躺在抽屉里,像一颗种子,在两个年轻人的期盼里,悄悄埋下了扎根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