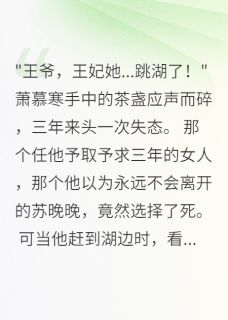我捡了个男人,以为是天赐良缘。他身受重伤,昏迷不醒,几乎将要断气。为了救活他,
我花光了全副身家。甚至,还去借了印子钱。可他待我,总是疏离冷淡,眉眼倦怠。不打紧,
一辈子那么长,再冷的心总能捂热。直至那日,我放牛晚归,
听闻同村的人说:「沈春桃捡的男人跑了。」偏巧印子铺的人上门讨债,把我堵在门口,
恶声恶气:「再不还钱,就把你卖去青楼。」1.「还跪着呢?」
周家小厮平安在门前探头探脑。平乐脸上为难,却也并未赶我走。「姑娘,您先起来吧。」
见不到周意,我执意不起。泰和酒楼前围观的人群,无不对我指指点点。
「又一个妄图攀周家高枝的。」「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山野村姑。」
「兴许想飞上枝头变凤凰呢。」我直了直腰杆,对旁人的话充耳不闻。几日前,
印子铺的人上门讨债。扬言再不还钱,就卖我去青楼。可我攒的银两,都拿去给周意看病了,
现下身无分文。同村的吴寡妇一拍大腿,怂恿我去县上找周意要钱。
「那小子不是说自己是周家公子吗?「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你去周家堵他。」
周家是松山县的大户人家,我连门都没摸着,就被门子轰走了。一连蹲了几日,
今日才蹲到周意。楼上咿咿呀呀的唱曲声终了。周意慵懒地推开窗,一身锦衣华服,
丝毫不见当初落魄的模样。他斜倚朱窗,居高临下地望着我:「沈春桃,
你不在桃花村好好待着,跑来这里做甚?」似是想起了什么,
他满眼讥讽:「难不成还真想做周家少夫人?」他一口一个少夫人,可我只想拿回药钱。
当初为了救他,我花光了全副身家。甚至,还去借了印子钱。九出十三归,
利滚利滚到了十八两。「要不你还我点钱吧,不多,就十八两。「你我之间的恩情,
一笔勾销。」周意冷笑:「像你这样贪图周家富贵,欲擒故纵的女人,我见多了。」而后,
他从袖中掏出一物,朝我抛来。我心中升起希冀,忙俯身捡起。不是钱,是布老虎。
是我给周意做的布老虎。刚捡到周意时,他昏迷得厉害,几日不曾醒来。
我便做了个布老虎放在他枕边,以寄驱除病魔,早日康健。没几天,周意身子好转,
可性子却差得厉害。「你做的什么丑东西?」他一脸嫌弃地丢开。「布老虎,保平安。」
周意嗤笑:「画虎不成反类犬。」旺财不满,朝他叫了几声。我当他还病着,笑便笑吧,
不然整日愁眉苦脸的,对身子不好。「没想到你这般见钱眼开,破布还当宝了。」他这番话,
让我顿时如坠冰窟,浑身发寒。我低眉垂眼,涩然道:「周意,还不上这十八两,
明日印子铺的人就要把我卖进青楼了。」周意身形一滞,抬起眼皮,
眼底尽是嘲弄:「沈春桃,收起你那无用的苦情计。」周意的狐朋狗友凑到窗前,
纷纷调笑打趣:「周兄前头,招惹的都是些千金**,楚馆行首。「怎地如今,
招惹了个乡野村姑?」「难不成家花没有野花香?」好友笑得意味不明。周意闻言,
原本阴沉的脸色,更加难看了。他啪地摔窗,拂袖而去。「沈春桃,你好自为之。」
2.好自为之,我又该如何好自为之?一路浑浑噩噩回到了桃花村。今夜,微云暗度,
不见新月。天上的点点星子,洒满河面,像是细碎的银子。「要真是银子就好了。」
我坐在河边,有一下没一下地捞着。枯坐良久,悲从中来。我一介孤女,无依无靠,
又有谁能救得了我?「要寻短见换个地方,别在我家门口。」吴寡妇嘴里一边嗑着瓜子,
一边毫不留情道。我抽抽噎噎地起身,闷闷说了句对不住。
吴寡妇是桃花村出了名的牙尖嘴利。怕她看我笑话,忙擦去脸上的泪痕。「那小子见着没?」
我摇摇头。吴寡妇啐了一口,白眼翻上天:「我早说过了,那小子不是什么好人。」
翠儿找来时,我正在吴寡妇的糖水铺哭成泪人。甜丝丝的莲子百合糖水,
我却喝出了苦涩的滋味。「你呀,指缝疏,易漏财,是个存不住钱的。「看吧,
钱拿去救那混小子,他翻脸不认人。」我垂下眼眸,细细端详自己疏阔的指缝。也是,
不然我长这么大,为何一分钱都存不下?先头好容易攒下的二两银子,还没捂热乎,
就给周意治病了。平日捡柴火,卖河鲜赚来的零碎,总会有两三文给了村口的小乞丐。
那小乞丐同我一般,无父无母,隔三差五便来讨钱。「春桃姐,我今日头痛。」「春桃姐,
我昨日摔了腿,腿疼。」小乞丐拿到两文钱后,端着破碗颠颠地跑了。周意冷眼旁观,
轻哂了句「傻子。」「没看出他在骗你吗?」我没理会他的冷嘲热讽,
背起竹筐继续埋头前行。「人总归有困难的时候,能帮则帮。」兴许我日后落难,
有好心人拉我一把呢?周意见我冥顽不化,十足的榆木脑袋,骂道:「蠢货,世人逐利,
一个小乞丐能帮你什么?」「寡妇,你对春桃说了什么?」翠儿夺门而入,护在我身前。
「我说那小子就一烂桃花。」钱没要到,明日印子铺的人上门,我心底发愁。「春桃,
你欠了多少?」「十八两。」「什么?!」翠儿骤然拔高音量:「什么药这么金贵?」
「所以我才说她,给那白眼狼花钱,不值当。」吴寡妇在旁凉凉道:「这下好了,
把自己搭进去了。」翠儿怏怏支颐,同我一般愁眉苦脸。「法子倒是有,只是……」
我知她想说什么。无非两条出路。要么找个有钱的郎君嫁了,但希望渺茫。要么嫁给老乡绅,
做他的第五房小妾。只是,老乡绅最喜磋磨人,好好的姑娘进去,没多久便被抬了出来。
「那赵员外一把年纪,都可以做你俩的阿爷了。」吴寡妇看出我俩的小九九,淡淡道。
「难道要眼睁睁看着春桃明日被抓走,卖去青楼吗?「要不,春桃你今晚收拾包袱,跑了吧?
」可天大地大,我又身无分文,能跑去哪儿?3.我终归没跑成。
印子铺的人把我抓回桃花村。吴寡妇拿出了她的养老钱。翠儿省下了买头花的钱。
乡亲们左拼右凑,才堪堪凑够三两。小胡子掌柜睨了眼这笔钱,鼻孔朝天,
不屑道:「打发叫花子呢?」说罢,便命左右的随从,把我捆了抓去青楼。
粗壮的汉子步步逼近,翠儿和村民们被拦在一旁。眼瞧着要落入虎口,旺财守在我身边,
冲他大叫。原本在篱落下觅食的大公鸡,忽地扑了过来。尖锐的喙,
毫不留情地啄向汉子蒲扇般的大手。旺财见状,也扑了上去,撕咬壮汉的裤腿。一时间,
鸡飞狗跳。戏台上,伶人水袖翻飞。「少爷,您不去看看沈姑娘吗?」平乐在旁端茶递水,
试探道:「万一,真被卖进青楼?」周意正摇头晃脑地听曲,时不时喊一声好。
伶人唱到精彩处,他拊掌欢颜,撒下托盘里的赏钱。白花花似雪片,看官无不叹,公子风流,
豪掷千金。「她这种拙劣的伎俩,我见多了。」周意抿茶,一脸的漫不经心。
他自小在锦绣堆里长大。遇到的女人,形形**,无不算计他的家产。思及此,
周意厌恶地扔下茶盏:「且看,过几日她还会上门。」大公鸡被撇到一边,
壮汉抬脚要踹旺财,我冲上去死死抱住他的腿。「造孽啊。」吴寡妇和村长看不下去了,
同印子铺的掌柜说了情。小胡子让人牵走了后院的老黄牛。老黄牛朝我哞哞,铜铃般的双眼,
留下两行清泪。奶奶留下的老房子,也被贴上封条,我无家可归了。「一个月后,
再见不到钱,我就把你卖去青楼。」可短短的一个月,我身无长物,
如何才能凑到这余下的十五两。世人常言,一文钱难倒英雄好汉。更遑论这十五两,
压得我直直喘不过气。村长看出了我的难处,给我找了份赶鸭的活计。「这份苦差钱少,
早晚都要盯着,你吃得消吗?」我忙不迭应下,钱少也是钱,到时候再想旁的出路。
村长脸色有些为难,踟蹰道:「只是,与你结伴的,还有个书生。你可愿意?」
我没有选择的余地,自然愿意。村长松了口气:「这人,你也认识。」4.我也认识?
远山叠翠,水雾缭绕,陈元临一袭青衫,笼着寒烟立在船首。「沈姑娘,别来无恙。」
江雾迷蒙,我瞧不清他的眉眼。一如五岁那年,凉茶铺门首,腾起的袅袅轻烟。
那会子我时常身上不利索,不是头疼发热,便是染了风寒。奶奶总会领我到临街的凉茶铺。
一来二去,我成了常客。「春桃,哪儿不舒服呀?」韩姨摸摸我的脑袋,柔声问道。
「这孩子,半夜睡觉老爱踢被子,着了凉。」奶奶牵着我的手,一脸无奈。我头脑昏沉,
趴在柜台上等凉茶。柜台对面,有位小少年正伏案看书。水烟轻飏,少年眉眼模糊。「元临,
给春桃妹妹端去。」少年轻轻应了声,黑黢黢的药呈至面前。「仔细烫。」我皱起眉头,
还没喝,嘴里便一阵阵地泛苦。待磨蹭到凉茶温时,这才不情不愿地端起,一饮而尽。
我吐着舌头,小脸皱成苦瓜,陈元临适时递来陈皮。我赶忙含在嘴里,苦意这才冲淡些许。
一抬眼,便瞧清少年郎的模样。嗯,倒也长得不错。凉茶好像没那么苦了。炎光起,轻烟散,
云气蓬。远处的山,近处的水,化作故人温润的眉眼。「陈家哥哥?」我很是意外。
陈元临微微颔首。「你怎么来了?你不是在松山书院念书吗?」韩姨在时,
左右街坊时常夸赞陈元临是村里最有出息孩子。窗外露冷风清,我尚在呼呼大睡时,
他已负起书囊,在去往书院的路上。后来,他确也如街坊所言的那般,寒窗苦读,
现下是松山书院的学子,师承大儒。这等前程无限,这般风光霁月的人,
又怎么会出现在破败的乌篷船上?「读书费钱,花销如流水。」陈元临似看出我心头的疑惑,
淡淡道。想来也是,不然他也不会在韩姨过世后,关了凉茶铺子,一心求学。经年未见,
如隔云烟,我顿时局促不安起来。幼时对凉茶的惧怕,长大后,成了对他的畏怯。
惟恐他同周意一般,嫌我是大字不识的村姑。故而,略略叙过家常后,我便不再言语。
我照看白日的鸭群,他值守夜间。渔火隐隐,灯火莹莹。陈元临在船首一面温书,
一面看向夜宿的鸭群。我因没钱买灯油,便蜷缩在帘内,借烛光摇曳,做起绣活。
笸箩搁置的欠条,上头密密麻麻的划痕,似银针般戳着我,钻心的疼。我不识字,
便画了十八道线,即欠的十八两。吴寡妇她们东拼西凑,帮我还了三两,还差十五两。
现下帮人赶鸭养鸭,一月一两银子,实在是杯水车薪。还债日日渐临近,
我心头如压了块巨石般,喘不过气。只盼着绣活能卖出去,好挣些零碎。可若卖不出呢?
不由了泄气,毕竟,周意曾嫌弃我做的难看。可若不做,没了这笔进项,还债依然遥遥无期。
几近绝望地倚于船壁厢,难道,我真的要被卖入青楼吗?眼泪忽地簌簌而下,
洇湿了手中的字条,我捂住嘴,试图掩盖断断续续的抽噎声。江上岑寂,偶有沙汀上的宿鸟,
鸣叫几声。帘外,时不时传来陈元临几不可闻的抄书声。烛火影影绰绰,
我揉揉哭得酸涩的眼睛。日子再难,还是要继续的。次晚,天色将暮。陈元临掀帘而入,
在船内点了一盏灯。「沈姑娘,我怕夜间多有不便,便点了灯。你歇息时,可将它熄灭。」
我抬手遮掩哭得像桃子的双眼,点点头。灯火温温,我好像没那么难过了。每隔几日,
陈元临便到县上交书稿。我厚着脸皮,托他帮我把做的绣活,捎到绣坊。
「若是……若是绣坊的人不收,劳烦元临哥帮我处置了。」我捏着衣角,声如蚊蚋。
「便是扔了,也无妨的。」「怎会?沈姑娘心灵手巧,自会有识货之人,定能卖出好价钱的。
」我垂首侧目,低低应了声,彼时江风轻柔,掠起点点涟漪。陈元临走后,
我便独自一人对着偌大的鸭群。连日吃素,嘴里实在寡淡。只能望鸭解馋。夕岚起,暮云碧,
陈元临抱书晚归,手里还提着油纸包。好香!我立马嗅到烧鸭诱人的香味。
「今日老师府上治席,我见没人动筷,便拿了些回来。」这……这居然是给我的?
我一时受宠若惊。「你不吃吗?」陈元临摇摇头:「我用过了。「这是绣活卖的钱。」
我接过沉甸甸的银袋,险些怀疑自己拿错。这般不堪入目的绣活,竟也有人买?
难不成真如他所言那般,有识货之人?陈元临淡淡一笑,示意我收下。白日里,他鲜少歇息,
只一味伏案抄书。入夜,仍旧埋头苦读。我不由感叹,陈元临真是用功。这日,
他又到岸上交书稿。我百无聊赖坐在船头,手里的长竹竿有一下没一下地拨动着。「咏鸭。
「鸭,鸭,鸭。「曲项向天嘎——别游远了!」还未来得及诗兴大发,便撞见一只青头鸭,
愈游愈远,意欲逃窜。要是鸭子飞了,可要赔不少钱。我忙凫水去抓那只狡黠的青头鸭。
待凫到沙汀时,忽然黑云翻墨,下起滂沱大雨。水势漫涨,我和鸭子被困在重重雨幕里。
完了,心底不住地哀嚎。钱还没还完,难不成要葬身于此了吗?5.再睁眼时,
已是乌篷船内。帘外传来熟悉的药香。我头脑昏涨,挣扎着起身,
却发现身上披了件干爽的外袍。「沈姑娘,药好了,趁热喝吧。」陈元临掀帘而入,
黑乌乌的药汁,像极了小时候常喝的。我硬着头皮吹凉,在陈元临的注视下,一饮而尽。
如往常般,他照例递来几小包陈皮。药汁在嘴里发苦,苦得我直蹙眉,可不知为何,
心底却甜甜的。兴许是陈皮的缘故,苦尽甘来。「对了,那丢失的青头鸭?」若是没抓回来,
想到要赔钱,我一阵肉疼。「且放宽心,它在外头呢。」我见水面浮着只七倒八歪的青头鸭,
心里拔凉。甫一靠近,它又支棱起来,向水深处游去。我松了口气,真狡黠。
我没钱买米买肉,故而吃得简单。船头架起小火炉,砂锅里咕噜咕噜煨着白粥。若运气好,
兴许能捞上几只河虾,做成虾仁粥。但今日,我运气属实不好,扑棱了老半天,
好容易捞到手的河虾,被眼尖的青头鸭叼走。罢了,白粥也能喝出些许滋味。
我切了一小碗萝卜干,倏地想起陈元临还未用过朝食,便招呼他过来。「多谢沈姑娘。」
「元临哥客气了,我没谢你的救命之恩呢。」我笑道,招呼他落座,殷勤献上萝卜干。
猛地想起为了给周意治病,银钱紧缺,肉和菜留给他,自己吃萝卜干就粥。周意觑见,
好看的眉头皱起,一脸嫌弃:「把这臭东西拿开。」思及此,我手一滞,放也不是,
拿也不是,便讪讪道:「元临哥,这个臭,要不我端开?」陈元临笑着摇摇头,拿起筷子,
夹了几块金黄的萝卜干。「萝卜干香得很,最易佐粥,春桃手艺不错。」他眼底的笑意,
盛满潋滟水光。船外青山耸翠,江水澄明。竟比不上他的温温一笑。我一时看呆了,
心底生出了些旖旎的心思。罢,我还欠着钱,不该有这样的遐想。「春桃,你怎么来这了?」
奶奶常说,肚里有食,心中不慌。一碗粥下肚,我也有了说出来的勇气。「我欠债了。」
6.欠的桃花债。我住在桃花村。村里有座桃花庵。庵里供奉了位桃花仙。相传,
桃花仙在庵前种了棵桃花树。若逢适龄男女,在桃花树下相遇,便是天赐良缘。那日,
我背着沉甸甸的柴火下山,路过桃花树。树下,躺着身受重伤,奄奄一息的男子。
甫见我走近,他费力地睁眼,声息几不可闻:「救……救我。」彼时,春风乍起,
桃花吹满头。一时分不清,是周意的玉面红,还是这桃花红。我登时鬼迷心窍,
想来这是天赐姻缘,岂能白白错过?二话不说,扔了柴火,把周意捡了回家。将养几日,
花光了积攒的银子,周意适才悠悠醒转。看着这张脸,我忽然也没那么心疼花掉的银子了。
「这是哪?你是谁?我怎么在这?」天降的夫君,话还挺密的。也好,有人能陪我说说话。
「这是桃花村,我叫沈春桃,你受了伤,我把你捡回来了。」周意拍了拍脑袋,
我忙上前阻止,怕他把自己拍傻了。「滚开,别碰我。」周意猛地甩开我的手,一脸嫌弃。
好嘛,天降夫君脾气还挺爆的,跟小炮仗一样。「春桃,听说你捡了个天仙一般的夫君。」
吴寡妇嗑着瓜子串门,倚在门前,笑呵呵道。周意冷冷转身,用被子蒙住脸,不搭理她。
吴寡妇打量了几眼,啧了一声。「这就是你捡的夫君?「我说春桃啊,你个大馋丫头,
吃点好的吧。」说完拍拍手,瓜子壳一甩,扭着小腰离去。「她几个意思?」
周意猛地掀开被子,憋红的脸带着愠色。「本少爷可是松山县远近闻名的美男。」
「没……没什么,你听错了。「饿了吧?我先去做吃的。」遂脚底抹油,溜到厨房。
这几日花钱如流水,厨房也没什么吃的。惟有笸箩里,孤零零躺着的老南瓜。炊烟升起,
趴在院门的旺财,颠颠跑了过来。绵绸金黄的南瓜粥,并酥软甜糯的南瓜饼,是我最拿手的。
周意看了一眼南瓜粥,又看了一眼旺财,嫌弃道:「这粥是不是被这狗偷食过?」怎会?
我连连摆手,旺财乖得很,从不偷食。周意犹面带狐疑:「它嘴上的污痕,不是偷吃,
是哪来的?」这可冤枉旺财了,它天生的。旺财因为嘴筒一圈焦黄,没人要。我给它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