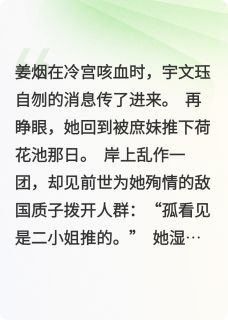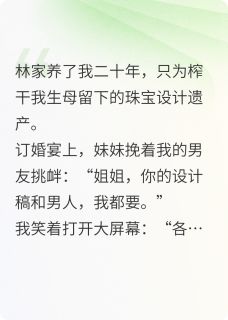
客厅里巨大的水晶吊灯折射着冰冷的光,晃得人眼睛发涩。
空气里弥漫着昂贵香薰刻意营造的甜腻,却盖不住那股子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疏离和冰冷。
我蹲在光洁得能照出人影的大理石地板上,手里捏着一块柔软的绒布,
小心擦拭着面前那双镶满碎钻的JimmyChoo高跟鞋的鞋尖。钻石硌着指腹,
微微的凉。这是林薇薇的鞋。半个小时前,她参加完某个名媛下午茶回来,一边抱怨着脚疼,
一边随手就把这双价值不菲的鞋子甩在了玄关正中央,差点绊倒路过的佣人张妈。“哎呀,
姐姐,”林薇薇娇嗲的声音像裹了蜜糖的刀子,从不远处的沙发飘过来,
带着毫不掩饰的刻薄,“你擦那么仔细干嘛?这种伺候人的活儿,让张妈做就好啦。
你可是我们林家的‘养女’,虽然……呵,身份是低了点,但也不能真把自己当下人使唤呀。
”她尾音上扬,带着一种恶意的愉悦。我擦鞋的动作没有停顿,甚至更加专注,
仿佛那鞋尖上沾了什么顽固的污渍。长长的睫毛垂下来,遮住了眼底所有翻涌的情绪。
习惯了。在这个金碧辉煌的牢笼里活了二十年,这种带着施舍和羞辱的“提醒”,
早已是家常便饭。“薇薇,怎么跟你姐姐说话呢!”林母苏曼的声音紧接着响起,
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虚伪的责备。她坐在林薇薇旁边,
保养得宜的手轻轻拍了拍女儿的手背,眼神却连一丝余光都没分给我,语气更是轻飘飘的,
毫无分量,“晚晚也是好心,怕张妈粗手粗脚的弄坏了你的鞋。不过晚晚啊,
”她这才把目光转向我,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擦干净了就赶紧放回薇薇衣帽间去,
别在这儿碍眼了。”心口像是被细密的针扎了一下,泛起熟悉的钝痛。
我低声应道:“知道了,妈。”就在这时,玄关传来指纹锁开启的轻微“嘀”声。
一个挺拔的身影走了进来,是沈墨。他穿着剪裁合体的深灰色西装,头发打理得一丝不苟,
英俊的脸上带着惯常的、无可挑剔的温和笑意。他是林薇薇的未婚夫,
也曾是我掏心掏肺爱了整整三年的男朋友。“伯父,伯母,薇薇。”沈墨微笑着打招呼,
目光在掠过蹲在地上的我时,没有丝毫停留,仿佛我只是角落里一件无关紧要的摆设。
他径直走向沙发区,将手里一个印着知名珠宝品牌Logo的精致小袋子递给林薇薇,
语气宠溺:“薇薇,路过看到新到的**款手链,觉得特别衬你,就买了。”“哇!
墨哥哥你最好啦!”林薇薇立刻雀跃起来,扑过去抱住沈墨的手臂,**般地瞥了我一眼,
声音甜得发腻,“我就知道你心里只有我!不像某些人,整天摆着张苦瓜脸,看着就晦气!
”沈墨笑着揉了揉她的头发,眼神温柔得能滴出水来。我攥紧了手里的绒布,
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就在这时,林薇薇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猛地站起身,
手里还端着那杯喝了一半的卡布奇诺。她脚步轻快地朝我这边走来,
脸上挂着天真又残忍的笑容。“哎呀,姐姐,你还在擦呀?”她走到我面前,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然后,毫无预兆地,她手腕轻轻一抖。
温热的、带着浓郁咖啡香气的液体,精准无比地泼洒下来,
瞬间浸透了我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棉质家居服的前襟。褐色的污渍迅速晕染开,
黏腻地贴在皮肤上,狼狈不堪。“啊呀!对不起对不起!”林薇薇立刻捂住嘴,夸张地惊呼,
眼睛里却闪烁着恶作剧得逞的光芒,“我不是故意的姐姐!手滑了一下!你看你,
怎么也不躲开呀?笨手笨脚的!”一股热血猛地冲上头顶,
愤怒和屈辱让我几乎控制不住身体的颤抖。我猛地抬起头,
对上林薇薇那双写满得意和挑衅的眼睛。“林薇薇!”我的声音带着压抑不住的愤怒。
“林晚!”几乎是同时,林父林国栋威严而不耐烦的声音如同惊雷般在客厅炸响。
他不知何时也从书房出来了,站在沙发旁,眉头紧锁,眼神锐利得像刀子一样刮在我身上,
“吵什么吵?一点小事就大呼小叫,还有没有点规矩?薇薇又不是故意的!一件破衣服而已,
值得你摆脸色给谁看?还不快滚回你房间去!”他的呵斥毫不留情,
带着一种理所当然的偏袒和厌弃。我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冰水,那股愤怒的火焰瞬间被浇灭,
只剩下刺骨的寒冷和麻木。我死死咬着下唇,直到尝到一丝血腥的铁锈味,
才勉强压下喉咙里的哽咽。我慢慢站起身,看也没看那对得意洋洋的父女,
也没看一旁眼神冷漠的苏曼,
更没看那个自始至终置身事外、甚至带着一丝嫌恶瞥了我一眼的沈墨。我挺直了背脊,
尽管前襟一片狼藉,一步一步,沉默地走向楼梯,
走向我那位于别墅最偏僻角落的、狭小得像个储藏室的房间。身后,
传来林薇薇故作委屈的撒娇声:“爸,你看姐姐,她是不是生我气了呀?
人家真的不是故意的嘛……”还有林国栋带着安抚意味的回应:“好了好了,薇薇乖,
别理她。一个养女,脾气倒不小。沈墨啊,让你见笑了。
”沈墨温和的声音传来:“伯父言重了,晚晚她……可能心情不太好。”那一声“晚晚”,
在此刻听来,虚伪得令人作呕。回到那个只有一扇小窗的房间,关上门,
隔绝了楼下虚伪的欢声笑语。我背靠着冰冷的门板,身体控制不住地滑落,跌坐在地板上。
眼泪终于决堤,汹涌而出,不是因为那杯咖啡,不是因为弄脏的衣服,
而是因为那深入骨髓的、日复一日的否定、羞辱和彻骨的寒冷。二十年了。从我有记忆起,
我就生活在这个华丽而冰冷的“家”里。我小心翼翼地讨好着每一个人,努力做到最好,
拼命学习,不敢有丝毫懈怠,只为了能配得上“林家养女”这个身份,
只为了能得到一点点可怜的认可和温暖。可无论我怎么做,在真正的林家血脉林薇薇面前,
我永远都低人一等,永远都是那个需要感恩戴德、随时可以被牺牲、被丢弃的“外人”。
我的存在,似乎只是为了衬托林薇薇的高贵和优越。而沈墨……那个曾经对我温柔体贴,
许诺过未来的男人,在林薇薇回国后,就毫不犹豫地倒戈,成了她最忠诚的骑士。
他看我的眼神,从曾经的深情,变成了如今毫不掩饰的疏离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
他撕碎我视若珍宝的生母设计草图一角时,那冷漠的话语,至今还在我耳边回响:“识相点,
别挡我们的路。那是属于林家的东西!”林家……林家!我猛地抬起头,
胡乱擦掉脸上的泪水。不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像个懦夫一样,只会在角落里哭泣。
一股强烈的、想要弄清楚一切的冲动攫住了我。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对我如此刻薄?
仅仅因为我是养女吗?还是……有什么我不知道的秘密?
我的目光落在床头柜最底层那个上了锁的小抽屉上。那里面,
放着我关于生母唯一的念想——几张模糊泛黄的老照片,
还有一本边角磨损严重、画满了各种珠宝设计草图的旧笔记本。那是我生母留下的唯一遗物,
也是我设计梦想最初的启蒙。林薇薇曾无数次鄙夷地嘲笑它是“垃圾”,
沈墨也曾不屑地撕碎过它的衣角。生母……那个在我襁褓中就离世的女人。
林家从未详细提及她,只说她是苏曼一个早逝的、没什么背景的闺蜜。但我总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林家对我生母留下的东西,尤其是那些设计草图,
似乎有种异乎寻常的在意,却又极力贬低。一个念头如同闪电般劈入脑海,
带着令人战栗的可能性。我深吸一口气,心脏在胸腔里狂跳起来。今晚,
林国栋和苏曼似乎在书房谈了很久,气氛有些不同寻常。也许……我能发现点什么?深夜,
整栋别墅陷入一片死寂。月光透过我小窗的缝隙,在地上投下一条惨白的光带。
我像幽灵一样赤着脚,悄无声息地溜出房间。走廊铺着厚厚的地毯,吸走了所有的脚步声。
我屏住呼吸,心跳声在寂静中震耳欲聋,一步一步靠近书房那扇厚重的实木门。
门缝里透出微弱的灯光,里面果然还有人!我小心翼翼地伏低身体,
将耳朵紧紧贴在冰凉的门板上。“……那份‘荆棘王冠’的最终设计稿和署名权,
必须尽快拿到手!不能再拖了!”是林国栋的声音,压得很低,却透着一股焦躁和狠厉,
完全不同于平日里的儒雅沉稳。我的心猛地一沉。“荆棘王冠”?
那不是我生母草稿本里反复出现、却始终未能完成的核心设计吗?林国栋怎么会知道?
还要“拿到手”?紧接着,苏曼的声音响起,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和心虚:“我知道!
可那小**把那破本子看得跟眼珠子似的,藏得死紧!直接要,她肯定不会给。
而且……我总觉得她最近有点不对劲,看人的眼神冷冷的。”“哼!
一个养了二十年的玩意儿,还能翻出什么浪花?”林国栋冷哼,
语气充满了不屑和掌控一切的傲慢,“沈墨和薇薇的订婚宴就在下周,等他们顺利订了婚,
拿到沈家的支持,我们的地位就更稳固了。到时候……”他的声音陡然转冷,像淬了毒的冰,
“找个由头,把她赶出去!或者,直接送走,送到国外哪个偏僻地方,眼不见为净!
省得夜长梦多!”轰隆——!仿佛一道惊雷在我脑中炸开!浑身的血液瞬间冲上头顶,
又在下一秒冻结成冰!赶出去?送走?眼不见为净?原来如此!原来我在他们眼里,
从来就不是什么养女,而是一件用完了就可以随意丢弃的工具!
一件妨碍了他们“亲生女儿”林薇薇和“乘龙快婿”沈墨美好未来的绊脚石!他们养着我,
就是为了榨取我生母留下的设计遗产的价值!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或者成了潜在的威胁,
就会像垃圾一样被清理掉!那“荆棘王冠”……难道就是他们觊觎的目标?
那是我生母的心血!是他们害死了她,然后调换了她的孩子,
现在还要掠夺她唯一留下的瑰宝?愤怒像滚烫的岩浆,
瞬间冲垮了所有的理智和二十年积攒的卑微隐忍!
一股毁天灭地的恨意从心底最深处疯狂滋生,瞬间席卷了四肢百骸!我死死咬住自己的手背,
用尽全身力气才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咸腥的血味在口腔里弥漫开。就在这时,
苏曼带着哭腔的声音又传了出来,充满了怨毒:“都怪那个短命鬼!
当年要不是她死抱着那个设计不放,不肯交出来,
我们也不用……不用听信张兰(林薇薇生母)那个疯女人的主意,
在医院把孩子……把孩子换了!现在好了,留了个定时炸弹在身边!
我天天看着那张和她越来越像的脸,我就……”后面的话,如同最锋利的冰锥,
狠狠扎进了我的心脏!医院……孩子……换了?!不是抱错!是故意的调换!
是谋杀和掠夺之后的又一次精心策划的犯罪!为了“荆棘王冠”,为了利益,
他们联手偷走了我的人生!让我顶着“养女”的屈辱身份,
在他们的施舍和践踏下活了二十年!而林薇薇,那个鸠占鹊巢的假货,
却享受着本应属于我的一切——父母的宠爱,优渥的生活,甚至……我爱过的男人!
滔天的恨意几乎要将我的灵魂撕裂!身体因为极致的愤怒和冰冷而剧烈地颤抖着。
我扶着冰冷的墙壁,才勉强支撑住自己摇摇欲坠的身体。书房里的对话还在继续,
讨论着如何在订婚宴后“处理”我,如何确保“荆棘王冠”万无一失。那些冰冷算计的字眼,
每一个都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心上。不知过了多久,书房里的灯灭了,脚步声远去。
我像一尊被抽走了所有生气的石像,僵硬地、一步一步挪回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背靠着门板滑坐到地上,黑暗瞬间将我吞噬。眼泪已经流干了,
只剩下刻骨的恨意和一片冰冷的死寂。黑暗中,我摸索着,
从抽屉最深处拿出那本边缘被沈墨撕破了一角的草稿本。粗糙的纸张触感,
上面是我生母留下的、充满了生命力的线条和构想。指尖抚过那些设计,
尤其是那反复勾勒、试图臻于完美的“荆棘王冠”雏形——缠绕的荆棘藤蔓,
守护着中心一颗光芒内敛、却蕴含着无尽力量的宝石。它象征着挣扎、束缚,
也象征着冲破一切、浴火重生的力量。“妈妈……”我无声地呢喃,将本子紧紧抱在怀里,
仿佛能汲取到一丝早已消逝的温暖。“对不起……女儿太没用了,
被他们骗了二十年……”冰冷的恨意如同藤蔓,缠绕着心脏,越收越紧。但这一次,
恨意没有让我崩溃,反而像淬炼的火焰,将心底最后一丝软弱和犹豫焚烧殆尽。
“复仇”这个念头从未如此清晰、如此强烈地占据了我的全部心神。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
我的身份!我母亲的心血!我要让这些鸠占鹊巢、虚伪狠毒的掠夺者,付出百倍千倍的代价!
我要把他们最在意的东西——名誉、地位、虚伪的幸福——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踩进泥里!
林薇薇不是想在万众瞩目的订婚宴上,挽着我的前男友,接受所有人的祝福,
彻底将我踩在脚下吗?很好。那就在她的“大喜之日”,送她一份永生难忘的“贺礼”!
一个疯狂而清晰的计划,在极致的恨意和冰冷的理智中,迅速成型。
我擦干脸上最后一点湿痕,眼神在黑暗中,亮得惊人。第一步,证据!我需要铁证!
能彻底撕开他们伪善面具,将那个肮脏的调换婴儿的阴谋公之于众的铁证!
书房里的对话只能算孤证,我需要实物,需要能呈现在所有人眼前的东西!第二天,
我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平静地出现在早餐桌上。甚至比以往更加“温顺”了几分。“爸,
妈,薇薇,”我主动开口,声音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低落”和“讨好”,
“沈墨哥和薇薇的订婚宴快到了,我……我想帮忙做点什么。毕竟,我也是薇薇的姐姐。
”我顿了顿,看向苏曼,“妈,我能不能……去书房帮您整理一下宾客名单?
或者看看还有什么需要准备的?我……我也想为家里尽一份心。”苏曼正优雅地喝着燕窝,
闻言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审视。林薇薇则嗤笑一声:“就你?
别添乱就不错了!宾客名单那么重要的东西……”“薇薇!”林国栋打断了她,
放下手中的财经报纸,目光深沉地落在我脸上。他似乎在评估我的“价值”和“威胁”。
几秒钟后,他脸上露出一丝看似温和实则掌控的笑容:“晚晚有这个心是好的。
你妈妈最近为订婚宴操劳,确实有些累。这样吧,你下午去书房,
帮她把需要最终确认的宴会流程和座位表再核对一遍,仔细点,别出纰漏。
”他像在施舍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任务。“谢谢爸!我一定会仔细核对的!”我连忙低下头,
掩饰住眼底一闪而过的冷光。机会来了。下午,我准时进入书房。林国栋和苏曼都不在,
大概是出去为订婚宴做最后的采买或应酬了。我反手轻轻关上门,心脏在胸腔里擂鼓。
书房很大,厚重的红木书柜顶天立地,散发着沉稳而压抑的气息。
巨大的办公桌收拾得很整洁。
我的目标很明确——林国栋习惯把重要的、不想被外人看到的文件,
锁在他右手边最底下的那个抽屉里。钥匙……钥匙会在哪里?我快速扫视桌面。笔筒,
文件架,台历底座……都没有。我的目光落在桌角一个不起眼的、装饰用的青铜镇纸上。
那镇纸是一只卧虎的形状。心头一动。林国栋属虎。我拿起镇纸,入手微沉。翻过来,
底部有一个小小的凹槽!轻轻一按,“咔哒”一声轻响,凹槽弹开,
里面赫然躺着一把黄铜小钥匙!强压下心头的激动,我迅速用钥匙打开了那个抽屉。
里面整齐地码放着几份文件夹。我快速翻找,心跳如雷。终于,
在一个标着“私人医疗档案(旧)”的牛皮纸文件袋里,我找到了我要的东西!
一份二十年前的妇产科住院记录复印件!纸张已经泛黄。
上面清晰地记录着:产妇苏曼(林母),于X年X月X日X时X分,产下一名女婴,
体重3.2kg,健康状况良好。记录末尾的签名,是一个陌生的医生名字。而另一份,
则是一份陈旧的银行汇款凭证!收款人:张兰。汇款人:苏曼。金额不小。
时间……就在我生母去世后不久,以及林薇薇出生后几个月!连续好几笔!
张兰……林薇薇那个早已“病逝”的生母!苏曼的“闺蜜”!
我的手因为激动和愤怒而微微颤抖。就是这些!
医院记录能证明苏曼当年确实在同一家医院生产!而给张兰的巨额汇款,
就是她参与调换婴儿、事后又被封口的铁证!我迅速拿出手机,调至静音模式,
将这几页关键证据清晰地拍摄下来。每一个字,每一个签名,都拍得清清楚楚。锁好抽屉,
放回钥匙和镇纸,将文件袋恢复原状。整个过程不过几分钟,我却感觉像打了一场仗,
后背已被冷汗浸湿。刚把手机藏好,书房门就被推开了。是苏曼,她手里拿着几个首饰盒,
似乎是刚购物回来。“晚晚?核对完了吗?”她随口问道,眼神扫过桌面。“快……快好了,
妈。”我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指了指摊开的流程表,“这个贵宾区的座位,
李董和王总的安排好像有点冲突,我再仔细看看。”“嗯,你看仔细点,这种细节不能错。
”苏曼不疑有他,把首饰盒放在桌上,又出去了。我长长舒了一口气,手心全是汗。第一步,
成了!接下来几天,我表现得异常“积极”和“顺从”。
主动包揽了许多订婚宴筹备的琐碎工作,跑前跑后,对林薇薇的各种刁难更是逆来顺受,
仿佛真的被那晚林国栋的威胁吓破了胆,只想在最后时刻多“表现”一下,求得一丝怜悯。
我的“识相”显然让林家人很满意。林国栋看我的眼神少了些审视,多了几分掌控者的睥睨。
林薇薇更是变本加厉地使唤我,享受着最后的“胜利”。“林晚,我的礼服裙摆有点皱了,
去给我熨好!要小心点,弄坏了把你卖了都赔不起!”“喂,我渴了,去给我榨杯果汁,
要现榨的,不要外面买的!”“林晚!订婚宴上我要戴的那套红宝石首饰呢?
快给我找出来试试!”每一次,我都低着头,默默照做。只是在转身离开时,
眼底的冰霜又厚了一层。忍。必须忍到那一刻。同时,我利用一切外出的机会,
寻找着那个名字——陈律师。生母草稿本扉页上,
用极淡的铅笔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个模糊的电话号码:陈明远。下面还有一行小字:信他。
这是我唯一的线索。我尝试拨打那个号码,是空号。二十年了,物是人非。但我没有放弃。
我跑遍了市内几家老牌的律师事务所打听,借口是家里长辈遗留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一家位置偏僻、门面古旧但口碑极佳的“明正律师事务所”里,
我找到了他!陈明远律师已经年过六旬,头发花白,戴着金丝眼镜,眼神却依旧锐利清明。
当我报出生母的名字——姜玥时,他拿着茶杯的手猛地一顿,茶水泼洒出来些许。他抬起头,
目光如电,仔细地、长久地审视着我的脸。“像……真像……尤其是这双眼睛。”他喃喃道,
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和追忆。他挥退了助理,关上了办公室的门。“孩子,
你……你真的是姜玥的女儿?”他的声音有些沙哑。我拿出那本珍贵的草稿本,翻到扉页,
指着那行字:“陈伯伯,我是林晚。这是我妈妈留下的。她让我……信您。
”看到那熟悉的字迹和那个草稿本,陈律师的眼眶瞬间红了。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再抬头时,眼神里充满了复杂的情绪:有悲痛,有愤怒,更有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孩子,
这些年……苦了你了。”他长长叹了口气,向我讲述了一段尘封的、令人发指的往事。
我的生母姜玥,当年是才华横溢、崭露头角的珠宝设计师。她与苏曼是大学好友。
姜玥在设计上的天赋让苏曼既羡慕又嫉妒。姜玥怀孕期间,灵感迸发,
构思出了足以震撼业界的“荆棘王冠”系列,但只来得及画出核心草图和理念。
她预感到自己可能因为体质问题生产艰难,提前立下了遗嘱,
将所有设计版权、署名权及相关权益,明确指定由她的亲生女儿继承。这份遗嘱一式两份,
一份由她信任的陈明远律师保管,另一份她本打算交给丈夫(我的生父,
一位同样有才华但早逝的工艺师),可惜未来得及。“你母亲产后大出血……走得太突然。
”陈律师的声音低沉而压抑,“我得到消息赶到医院时,只看到苏曼抱着一个婴儿,
哭得伤心欲绝,说那是她的女儿。当时情况混乱,我也沉浸在悲痛中,
加上苏曼和你母亲关系亲密,她丈夫林国栋又在一旁作证……我完全没有怀疑!
”“直到后来,我整理你母亲遗物,发现她日记里隐晦地提到对苏曼的担忧,
曾向我提过的一个细节:她给孩子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刻着荆棘缠绕新月图案的银质长命锁,
是她亲手设计的雏形。可苏曼抱着的那个女婴(林薇薇)身上,并没有这个锁!
”陈律师眼中迸射出愤怒的光芒:“我起了疑心,暗中调查。发现当年负责接生的护士张兰,
在姜玥去世后不久就辞职离开了本市,行踪成谜。而我辗转查到,苏曼在差不多的时间,
曾多次向一个匿名账户汇款,数额巨大!我怀疑张兰就是被收买的执行者!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