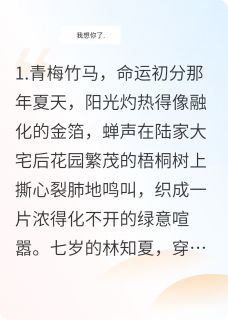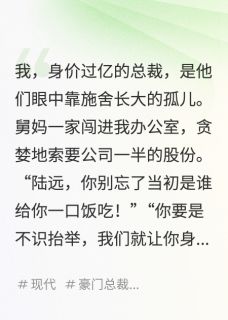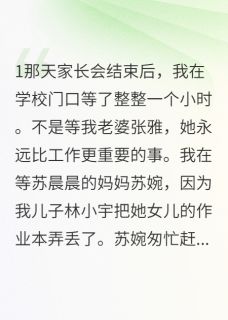温瓷给沈聿白设计的婚戒还差最后一道工序,却在他西装上闻到了林晚意的香水。
那是他亲手为林晚意调制的“罪欲”,我曾笑着说这名字不吉利。“沈聿白,
你的气味背叛了你。”我摘下婚戒留在调香台上。三年后国际拍卖会上,
他天价拍下温瓷设计的“赎罪”钻戒。“温瓷,这枚戒指我熔了三十瓶‘罪欲’才做成。
”他当众单膝跪地时,我闻到他袖口熟悉的蓝桉香——那是我们初遇时他身上的味道。
林晚意突然冲进来哭喊:“当年是我把香水喷遍他衣帽间!”闪光灯中,
带有蓝桉香的沈聿白将戒指推进我指间:“闻的到吗?它现在只为你心跳。
”温瓷的指尖悬停在那枚即将完成的戒指上方,铂金戒圈在无影灯下流淌着清冷的光泽。
镶嵌槽位已经精准开好,只等最后一步,将那颗纯净度极高的主钻稳稳落位。这枚戒指,
她命名为“共生”,是她为沈聿白设计的婚戒,每一根线条都浸透了她对未来的描摹。
空气里弥漫着工作室特有的、混合了金属冷冽与蜡模温润的气息,
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蓝桉香——沈聿白身上惯有的味道,像雨后森林,干净、疏离,
却让她安心。她放下镊子,揉了揉因长时间专注而微微发酸的后颈。窗外,暮色四合,
将城市切割成一片片灯火岛屿。沈聿白说今晚有个推不掉的应酬,晚些时候会来接她。
温瓷的目光扫过调香台一角,那里静静躺着一个深蓝色丝绒小盒,
里面是她耗时数月、失败无数次才最终定稿的“共生”设计稿。就在这时,
工作室的门被轻敲两下推开。沈聿白高大的身影带着室外的微凉空气走了进来。
他脱下剪裁完美的深灰色西装外套,习惯性地搭在温瓷工作椅的椅背上。“抱歉,等久了?
”他的声音低沉,带着一点不易察觉的疲惫,却依旧温柔。他走近,
身上那股清冽的蓝桉气息随之靠近,像一张无形的网,轻易就捕获了温瓷的感官。
温瓷自然地迎向他,想汲取这份熟悉的气息作为慰藉。然而,就在她微微倾身,
鼻尖距离他搭在椅背上的西装外套仅半尺之遥时,一股极其突兀、极具侵略性的香气,
蛮横地撞进了她的嗅觉世界。甜腻、浓烈、带着某种近乎腐朽的华丽感,像开至荼蘼的罂粟,
散发着危险又诱惑的尾调。温瓷的身体瞬间僵住,血液似乎在这一刻凝固。
这味道……她绝不会认错!沈聿白的手刚触碰到她的肩膀,温瓷却猛地后退一步,
动作快得带起一阵风。她脸上的血色褪得一干二净,那双总是盛着温柔笑意的眼睛,
此刻只剩下冰冷的震惊和难以置信。她的视线死死钉在那件西装外套上,
仿佛那是一件沾满了致命病菌的污染物。“怎么了,瓷瓷?”沈聿白的手落空,
看着她骤变的脸色,英挺的眉宇间浮起清晰的困惑和担忧,他下意识地又朝她靠近一步。
“别过来!”温瓷的声音尖锐得几乎破音,带着一种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颤抖和恐惧。
她再次后退,后背重重撞在坚硬的调香台上,发出沉闷的声响。瓶瓶罐罐轻轻晃动,
空气中各种香料的分子似乎也因她的情绪而躁动不安。她的目光,
终于从那件“罪证”般的外套上,缓缓移到沈聿白的脸上。那双深邃的眼眸里,
此刻清晰地映着她苍白失魂的模样,写满了真切的担忧。多讽刺啊!
温瓷的胸腔里有什么东西在剧烈地翻搅,痛得她几乎无法呼吸。“沈聿白,
”她的声音低了下去,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齿缝里艰难地挤出来,冰冷得没有一丝温度,
“你身上的味道……背叛了你。”沈聿白微微一怔,
随即低头嗅了嗅自己的衬衫袖口:“味道?你是说……”他似乎想到了什么,眉头锁得更紧,
试图解释,“今晚的应酬是临时安排的,对方是林氏的人,林晚意也在场。
她……”“林晚意?”温瓷轻轻重复着这个名字,嘴角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弧度,
眼神彻底黯淡下去,如同燃尽的灰烬,“‘罪欲’……是你亲手为她调制的‘罪欲’。
”她记得太清楚了。当年林晚意缠着沈聿白为她定制一款独一无二的香水,
沈聿白最终调出了“罪欲”。温瓷当时还半开玩笑地说过,这名字透着一股不祥。
沈聿白只是揉揉她的头发,说不过是个名字而已。原来,不祥的预感,早已埋下伏笔。
“瓷瓷,你听我说!”沈聿白急切地想要抓住她的手臂,语气焦灼,“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今晚是林董突然心脏病发作,就在隔壁包间,现场一片混乱。晚意她……她吓得手足无措,
我当时离得近,不得不扶了她一把,可能……可能是不小心沾上了!仅此而已!
”他语速很快,额角甚至渗出了细密的汗珠,那份担忧和急于辩解的神情,看起来如此真实。
可温瓷的感官世界里,只剩下那股粘腻浓稠、挥之不去的“罪欲”香气,像无数只冰冷的手,
扼住了她的喉咙,也扼杀了她心中最后一丝侥幸。她缓缓低下头,
目光落在自己左手的无名指上。那里还戴着一枚简单的铂金素圈,
是他们订婚时沈聿白亲手为她戴上的。戒指温热的触感此刻却像烧红的烙铁,
灼痛了她的皮肤,也灼痛了她的心。温瓷的动作很慢,带着一种近乎凝固的决绝。
她抬起右手,指尖冰凉,轻轻地、却又无比坚定地,将那枚素圈戒指从无名指上褪了下来。
戒指脱离指根的那一刻,留下了一圈微不可察的,浅浅的印记。她没有再看沈聿白一眼,
仿佛他和他身上那股令人作呕的香气,都已与她无关。她只是转过身,
走向那张承载了她无数灵感与心血、此刻却显得无比冰冷的调香台。台面上,
还散落着她为“共生”戒指试验的各种香料小样。她将褪下的那枚素圈戒指,
轻轻放在了调香台的正中央,金属与玻璃台面碰撞,发出“叮”的一声脆响,
在死寂的工作室里显得格外刺耳,也格外空茫。那一声轻响,像是一道休止符,
斩断了过去所有甜蜜的乐章。温瓷没有回头,径直走向工作室的门。她的背影挺得笔直,
却又单薄得像一张随时会被风吹走的纸。门被拉开,外面走廊的光线涌进来,
在她身后拖出一道长长的、孤寂的影子。“瓷瓷!你去哪?!”沈聿白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
带着前所未有的惊惶和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下意识地抬步就要追。“别跟着我。
”温瓷的脚步没有半分停顿,声音平静得可怕,像结了冰的湖面,“沈聿白,我们结束了。
”门在她身后关上,隔绝了那个充满“罪欲”气息的空间,也隔绝了她与他之间的一切可能。
沈聿白僵在原地,伸出的手徒劳地停在半空。空气中,
那股属于林晚意的甜腻香气和他自己身上清冽的蓝桉气息诡异而绝望地交织着。
他猛地看向调香台中央,那枚孤零零的素圈戒指在灯光下反射着冰冷的光,
像一只嘲讽的眼睛。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痛得他几乎弯下腰去。
他踉跄着扑到门边,用力拉开——走廊里,早已空无一人。只有电梯下行的指示灯,
冰冷地闪烁着。他追出去,夜色如墨泼洒下来,冰冷的雨丝毫无征兆地开始飘落,
迅速淋湿了他的头发和昂贵的衬衫。街道上车灯在雨幕中连成模糊的光河,行人匆匆,
撑着伞汇成流动的色块。他茫然四顾,视线疯狂地扫过每一个相似的背影,
徒劳地搜寻着那个刻入骨髓的身影。“温瓷——!
”他的呼喊被淹没在都市的喧嚣和越来越大的雨声中,显得苍白而绝望。
雨水顺着他棱角分明的下颌线不断滴落,分不清是雨水还是别的什么。
他失魂落魄地回到那间充斥着背叛气息的工作室,颓然跌坐在她常坐的那张工作椅上。
冰冷的湿意透过衣料渗入皮肤,却远不及心底那灭顶的寒意。
他拿起那枚被她遗弃的素圈戒指,冰冷的金属硌在掌心,
那圈微凹的指痕仿佛还残留着她指尖的温度。他低头,将脸深深埋进掌心,
肩膀无声地垮塌下去。原来,有些失去,真的只需要一瞬间的“气味”,便足以致命。
三年时间,足够温瓷的名字在顶级珠宝设计圈里淬炼成一块熠熠生辉的金字招牌。
从最初那个带着破碎之心,只身远赴异国他乡的年轻设计师,
到如今各大拍卖行争相邀约的“幽灵之手”,她走过的路,
每一步都踩在自己沉默的倔强之上。她设计的作品,线条凌厉,构思奇诡,
总带着一种穿透表象的锋利感,像在无声诉说一个关于失去与重塑的故事。“温老师,
这是本次日内瓦‘瑰色纪元’拍卖会的压轴拍品目录,您的‘赎罪’位列其中。
”助理将一本厚重精美的册子轻轻放在她面前宽大的设计台上,
声音里带着压抑不住的兴奋与崇敬。温瓷的目光从正在打磨的一颗海蓝宝原石上移开,
落在目录封面烫金的徽标上。她伸出手,指尖拂过那凹凸的质感,
最终停留在印着她那件作品图片的位置。图片上,
一枚结构极其复杂的钻戒在黑色丝绒的衬托下,折射出冷冽而璀璨的光芒。
主钻并非传统的圆钻,
而是一颗被无数细密铂金荆棘包裹、切割成不规则泪滴形状的稀世黄钻,
荆棘间点缀着细小的无色钻石,像凝固的冰棱,又像无声的控诉。戒托的设计更是惊心动魄,
仿佛从内部崩裂开,却又被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行弥合,留下永久的、充满张力的裂痕。
整个作品,美得惊心动魄,也痛得淋漓尽致。“赎罪”——这是她赋予它的名字。
灵感源于某个被蓝桉香气和浓烈罪欲彻底撕裂的雨夜,是她用三年时光,一锤一凿,
将心底最深的伤口锻造成了这枚惊世骇俗的戒指。助理继续汇报:“另外,温老师,
‘幽灵岛’项目的最终规划图已经送到。
那位神秘的买家……依然坚持要您亲自去岛上确认最后的核心展馆设计。
”助理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困惑和谨慎。这个名为“幽灵岛”的私人岛屿开发项目,
投资额巨大得令人咋舌,买家身份成谜,行事风格更是诡异。最令人费解的是,
对方从项目伊始就指名道姓,必须由温瓷担任首席设计师,并且所有关键节点,
都必须她本人亲临。温瓷微微蹙眉。“幽灵岛”……这个名字本身就透着一种不祥的暗示。
动着一小块蓝桉叶的干燥标本——这是她工作室里唯一允许存在的、与过去有关的微弱气息。
三年来,她总是能在深夜工作时,隐约捕捉到一丝极淡、极新鲜的蓝桉冷香,如同幻觉,
却固执地萦绕不散。她曾以为是思念作祟,或是嗅觉记忆的欺骗,直到此刻,
“幽灵岛”和这似有若无的香气微妙地重叠在一起。一丝冰冷的警惕,悄然爬上她的脊背。
“知道了。”她淡淡应道,合上拍卖目录,目光重新落回那颗未完成的海蓝宝上,
仿佛刚才那一瞬间的异样只是错觉,“准备行程吧,先去日内瓦。”助理应声退下。
工作室里恢复了寂静,只有打磨机低沉的嗡鸣。温瓷拿起那片小小的蓝桉叶,凑近鼻尖。
干燥的叶片,只余下极淡的木质清气。可空气里,那丝若有似无的新鲜冷冽气息,
似乎又隐约浮动了一下。她松开手,叶片飘落在图纸上。无论“幽灵岛”背后是谁,
无论那香气是巧合还是……她都必须去。为了“赎罪”,
也为了彻底斩断所有飘渺的、可能将她拉回过去的丝线。日内瓦湖畔的贝格酒店宴会厅,
水晶灯的光芒如同融化的星河,倾泻而下。
空气里浮动着名贵香水、雪茄和陈年佳酿混合而成的,属于顶级财富圈层的独特气味。
衣香鬓影,觥筹交错,低语与笑声在华丽穹顶下回荡。温瓷坐在拍卖厅前排预留的贵宾席上,
一身简洁的黑色丝绒礼服,长发松松挽起,露出纤长优美的脖颈。
她像一株遗世独立的水墨兰,与周遭浮华的喧嚣格格不入。她的目光平静地扫过台上,
看着一件件天价艺术品、稀世珠宝被槌声敲定归属。她的“赎罪”作为压轴,序号是最后。
当拍卖师终于以充满煽动性的语调介绍起“赎罪”时,整个大厅瞬间安静下来,
所有目光都聚焦在那枚被升降台缓缓托起的钻戒上。聚光灯下,
那颗被荆棘缠绕的泪滴形黄钻折射出惊心动魄的光芒,戒托上充满力量感的裂痕,
在强光下更显触目惊心。“起拍价,八百万瑞士法郎。”拍卖师的声音清晰地回荡。
竞价瞬间白热化。号码牌此起彼伏,价格像失控的火箭,一路飙升。“一千两百万!
”“一千五百万!”“两千万!”数字的每一次跳动,都引发现场一阵压抑的惊呼。
她的指尖无意识地、一遍又一遍地摩挲着手腕内侧一处极其细微的、几乎淡去的疤痕。
那是在三年前那个冰冷的雨夜,她失魂落魄地冲出工作室后,在异国他乡陌生的街头,
被一个飞车党猛地抢夺挎包时,粗糙的包带在她皮肤上狠狠撕裂留下的印记,
那瞬间的剧痛和随之而来的巨大无助感。在此刻,伴随着台上戒指的每一次加价,
都无比清晰地复苏了。那道疤,是她狼狈逃亡的起点,是刻在身体上的耻辱标记,
与台上那枚象征着心碎巅峰的“赎罪”,隔着三年的时光遥遥呼应。她的表情依旧沉静如水,
甚至可以说是冷漠。然而,那双望向拍卖台的眼睛,却彻底出卖了她。
它像两泓结了厚冰的湖泊,表面是死寂的平静,
深处却倒映着台上那枚戒指冰冷璀璨的光芒——那光芒如此刺眼,灼烧着她的视网膜,
也灼烧着她试图尘封的记忆。那枚价值连城的“赎罪”,
承载着她所有无法言说的痛楚、被彻底碾碎的信任,
以及支撑她独自走过荆棘岁月的、冰冷坚硬的恨意。它越是耀眼,
她的心就越像沉入无光的深海。“两千五百万!还有加价吗?
两千五百万第一次……”拍卖师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拔高。就在这时,
一个低沉、冷静、穿透力极强的男声,从拍卖厅后方最角落的阴影里响起,
清晰地盖过了所有的嘈杂:“五千万。”这声音并不高亢,
却像一颗投入绝对静默湖面的巨石,瞬间盖过了所有细微的嘈杂,
清晰地、不容置疑地砸进了每一个人的耳膜。全场死寂。所有的目光,包括温瓷的,
都像被无形的线牵引着,猛地投向那个声音的源头。阴影缓缓褪去,露出一个挺拔的身影。
男人穿着剪裁完美的黑色礼服,一步一步,从容不迫地从后方走向前排。灯光追随着他,
照亮了他深刻如雕琢的轮廓,紧抿的薄唇,和那双此刻正穿越人群,
精准无比地锁住温瓷并且深不见底的眼眸。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倒流。温瓷的心脏,
在听到那个声音的第一个音节时,就像被一只从冰窟里伸出的巨手狠狠攥住!骤然停止跳动!
巨大的冲击让她眼前猛地一黑,身体不由自主地微微晃了一下,
指尖死死掐住座椅扶手才勉强稳住。随即,那颗停滞的心脏又像被重锤狠狠擂击,
疯狂地、失控地在胸腔里冲撞起来!咚!咚!咚!沉闷而巨大的回响在她自己的头颅里震荡,
震得她耳膜嗡嗡作响,几乎要盖过外界的一切声音。
她全身的血液似乎在这一刻完成了两个极致的转换:先是“轰”的一声全部冲向头顶,
让她脸颊瞬间滚烫,紧接着又在零点一秒内褪得一干二净,
留下彻骨的冰凉和一种濒死的麻木感。她感到指尖冰冷,连呼吸都变得困难。
阴影在无数道聚焦的视线中,仿佛被无形的力量缓缓拨开。
一个挺拔、修长、气场强大到令人窒息的身影,从容不迫地从那片黑暗的幕布后走了出来。
男人穿着一身剪裁完美到毫厘不差的黑色礼服,衬得他肩宽腿长,
宛如古希腊神话中走出的神祇。昂贵的面料在灯光下流淌着低调而奢华的光泽。
他的步伐沉稳有力,每一步踏在厚软的地毯上,都发出轻微而沉闷的声响,
在死寂的大厅里被无限放大,如同踩在紧绷的鼓面上,更像是精准地、一步一步,
踩在温瓷那根已经绷到极限、随时会断裂的神经之上!追光灯如同拥有生命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