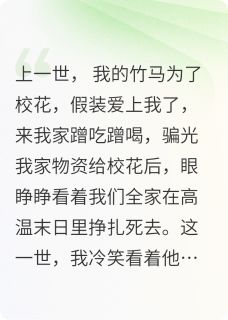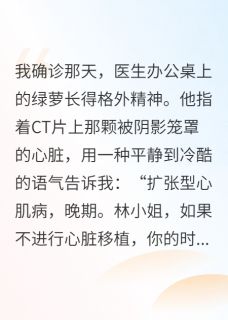第十日倒计时开始,人类集体收到“十日终焉”通知。富人们斥巨资建造“方舟”,
穷人们则在街头疯狂放纵。我是一名临终关怀医生,选择留在医院照顾无家可归者。第八日,
富商带雇佣兵闯进医院抢夺医疗舱。他女儿突然挡在病童面前:“我的命,我自己选。
”富商强行带走女儿后,
我发现她留下的平板里藏着骇人真相:“培养皿人类观察实验第7次重置,
实验对象自我意识突破临界。”屏幕亮起,无数漂浮在宇宙中的透明培养皿正反射着微光。
……第十日。这数字像一枚冰冷的图钉,被无形之手狠狠摁进全人类意识的中央,
清晰、尖锐、无法回避。通知简洁到残酷,没有前因,没有后果,
只有一行字烙印在视网膜上,回荡在神经末梢:十日终焉。倒计时,开始。秩序,
那个人类花了数千年才小心翼翼搭建起来的脆弱沙堡,在第一个浪头打来时便轰然垮塌。
城市的心脏——那些曾彻夜流淌着欲望与活力的街道——瞬间被抽干了血液,
只剩下疯狂在断壁残垣间奔突。玻璃碎裂的尖叫此起彼伏,
火焰贪婪地舔舐着橱窗里昂贵的残骸,浓烟如同绝望的旗帜,在浑浊的天空下扭曲升腾。
空气中弥漫着劣质酒精、汗液和某种更深沉、更原始的恐惧蒸腾出的酸腐气息。
有人纵声狂笑,笑声像生锈的铁片刮擦着耳膜;有人蜷缩在阴影里,无声地颤抖,
像被遗弃的破布娃娃。末日像一个巨大的漩涡,
把理智、尊严、还有那层薄薄的名为“文明”的油彩,毫不留情地卷了进去,搅得粉碎。
城市的另一端,却是另一种死寂的喧嚣。临海的峭壁被粗暴地削平,
钢铁的骨架在探照灯惨白的光柱下日夜疯长,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那是“方舟”,
富人们用天文数字的金钱和无数底层劳工的血汗浇筑的诺亚方舟。
巨大的合金外壳在阴沉的天空下闪烁着冰冷无情的光泽,像一头匍匐的钢铁巨兽,张开巨口,
吞噬着从全球搜刮来的物资、技术精英,还有那渺茫到近乎虚无的生存希望。高墙内外,
泾渭分明。墙外是地狱的狂欢,墙内是通往未知彼岸的、用黄金和特权铺就的栈桥。
偶尔有穿着考究的人影在戒备森严的入口匆匆闪过,脸上没有表情,
只有一种被巨大恐惧压缩到极致的、近乎麻木的平静。我关掉了平板,
屏幕上“方舟”直播那令人作呕的“人类文明火种保存计划奠基仪式”画面瞬间熄灭。
病房里浑浊的空气带着消毒水和绝望发酵后特有的微甜腐败气息,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我是一名临终关怀医生,陈默。我的战场,就在这座被遗弃的城市角落里,
这座同样被遗弃的慈济医院。走廊里挤满了人,大多是老人和孩子,
像被潮水冲上岸的、失去了光泽的贝壳,密密麻麻地躺在担架上、铺在冰冷地板上的薄毯上,
甚至蜷缩在墙角。空气里弥漫着浑浊的叹息、压抑的呜咽,还有止痛药也压不住的低低**。
浑浊的空气带着消毒水和绝望发酵后特有的微甜腐败气息,沉甸甸地压在胸口。
“陈医生…水…”角落里传来嘶哑的气音。我端着水杯走过去。那是一个瘦得脱了形的老人,
浑浊的眼睛费力地睁开一条缝,嘴唇干裂。扶起他枯柴般的手臂,
小心地将温水一点点喂进去。水顺着他的嘴角流下,在脏污的衣襟上晕开深色的痕迹。
他喉咙里发出咕噜的声音,像一架破旧的风箱在艰难地抽动。“谢谢…陈医生…”他闭上眼,
气息微弱,“第十天了…真快啊…”我轻轻擦去他嘴角的水渍,喉头哽着,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是啊,第十天了。时间像一把钝刀,悬在所有人的头顶。刚直起身,
一股蛮横的力量猛地撞开我旁边的护士小李。我踉跄了一下,水杯脱手,在地上摔得粉碎。
“药!止痛药!还有吃的!
”一个满脸横肉、眼睛赤红的男人挥舞着不知从哪里捡来的半截钢管,唾沫星子喷溅,
“都他妈拿出来!老子不想最后几天还活受罪!
”他身后还跟着几个同样衣衫褴褛、眼神凶狠的人。恐慌瞬间在拥挤的走廊里炸开,
压抑的哭泣声变成了惊恐的尖叫。人群像受惊的沙丁鱼群,本能地向后缩去,
却又被后面的人堵住,混乱地推搡着。“仓库空了!”小李护士被推得撞在墙上,
声音带着哭腔和愤怒,“最后一点储备,昨天就分给孩子们了!”“放屁!”男人根本不信,
钢管“哐当”一声砸在旁边的金属病历推车上,发出刺耳的巨响,“不给?老子自己找!
”他像头发狂的公牛,猛地冲向护士站旁边紧闭的配药室门。“砰!砰!砰!
”钢管砸在门锁上,火星四溅。那扇薄薄的门板在暴力的撞击下痛苦地**、变形。
我的心跳得如同擂鼓,血液冲上头顶。不能让他进去!
那里还有最后几支留给几个晚期癌症孩子的强效止痛针剂!
那是他们仅存的、在剧痛中保留最后一点尊严的可能!“住手!”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身体下意识地扑过去,试图去抓他挥舞钢管的手臂。太慢了,也太无力了。“滚开!
”男人反手一抡。钢管带着风声,狠狠砸在我的左臂上。剧痛!
像一根烧红的铁钎瞬间捅穿了骨头和肌肉。我闷哼一声,眼前发黑,
整个人被巨大的力量带得向后摔去,重重撞在冰冷的墙壁上。左臂瞬间失去了知觉,
软软地垂落下来,钻心的疼痛却清晰地传遍全身。“陈医生!”小李的尖叫刺破了混乱。
那男人看都没看我一眼,狞笑着,一脚踹开了已经变形的配药室门,带着同伙冲了进去。
里面立刻传来柜子被拉倒、玻璃瓶碎裂的刺耳声响,
以及他们发现“战利品”后兴奋的粗野叫骂。**着墙,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的白大褂。
左臂的疼痛尖锐地提醒着我现实的残酷。身体在叫嚣着反击,
但更深沉的无力感像冰冷的潮水,一点点淹没上来。秩序?规则?在绝对的自私和暴力面前,
薄如蝉翼。我挣扎着想站起来,但左臂的剧痛和撞击带来的眩晕让我动弹不得。小李扑过来,
试图扶我,眼泪在她脏污的脸上冲出两道痕迹。配药室里乒乒乓乓的洗劫声持续了几分钟,
如同钝刀反复切割着紧绷的神经。终于,那男人和他的同伙心满意足地冲了出来,
怀里抱着几盒被撕开包装的抗生素、几瓶生理盐水,还有几包皱巴巴的压缩饼干。
他们像一群得胜的鬣狗,撞开挡路的人群,狂笑着消失在走廊尽头弥漫着烟尘的昏暗里,
只留下一片狼藉和更加深重的绝望。小李搀扶着我,艰难地挪到配药室门口。门框歪斜着,
玻璃碎片像尖锐的钻石,铺满了地面。柜子东倒西歪,抽屉全被暴力拉开,里面空空如也。
地上散落着被踩扁的药盒、撕碎的标签和翻倒的药瓶流出的浑浊液体,
混合成一片肮脏的泥泞。空气中刺鼻的药味里,混杂着一股暴戾和贪婪留下的腥膻气。
我的目光,死死钉在墙角那个被撬开的、加固的冷藏小药柜上。柜门洞开,里面空空荡荡。
那几支珍贵的、淡黄色的止痛针剂,连同存放它们的特制泡沫盒,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是小杰、小娟他们最后的希望。小杰才七岁,骨癌的疼痛能让他整夜整夜地哭嚎,
直到嗓子彻底嘶哑;小娟稍微大点,十一岁,
神经母细胞瘤的折磨让她瘦得像一片随时会飘走的枯叶,只有注射后那短暂的片刻,
她才能蜷缩在破毯子里,像个普通孩子一样沉沉地睡去一会儿。一股冰冷的绝望,
比左臂的骨折更甚,瞬间攫住了我的心脏,让它沉甸甸地坠入无底深渊。
拳头在身侧无意识地握紧,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带来一丝尖锐的刺痛。
愤怒在胸腔里左冲右突,烧灼着五脏六腑,却找不到任何出口。我能做什么?追出去?呵斥?
在这末日的地狱里,道理和怜悯早已被践踏成泥。
“陈医生…您的胳膊…”小李带着哭腔的声音把我从冰窟里拉回一丝现实。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软垂的左臂,肿胀已经开始显现,皮下淤血蔓延开一片狰狞的青紫色。
疼痛尖锐而持续。我深吸一口气,那浑浊的空气带着尘埃和绝望的味道,呛得肺叶生疼。
不能倒下。至少现在不能。“没事,”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异常干涩沙哑,像是在砂纸上磨过,
“找点夹板…或者硬纸板,再撕点布条,先固定一下。
”我指了指旁边被砸倒的金属病历推车,“那个…拆一根横杆下来。”小李含着泪点头,
手忙脚乱地去翻找。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儿童病区。每一步都牵扯着左臂的剧痛,
但更痛的是即将面对的画面。还没走到门口,
那熟悉的、撕心裂肺的哭嚎声已经穿透薄薄的隔板门,像无数根针扎进我的耳膜。推开门。
昏暗的光线下,小杰小小的身体在窄小的病床上痛苦地扭动、翻滚,像一条被抛上岸的鱼。
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嶙峋的脊椎在单薄的病号服下清晰地凸起。汗水浸透了他稀疏的头发,
粘在苍白的额头上。他张着嘴,喉咙里发出不成调的、野兽般的嚎叫,
那是骨头深处被癌细胞啃噬的剧痛,无法用言语形容,只能用最原始的声音嘶喊出来。
他妈妈,一个同样憔悴不堪的女人,死死抱着他,试图按住他因剧痛而痉挛的身体,
眼泪无声地汹涌而出,滴落在孩子滚烫的额头上。旁边的小娟蜷缩在毯子里,
像一只受惊的雏鸟。她没有哭喊,只是死死咬着嘴唇,下唇已经被咬破,渗出细细的血珠。
她瘦得颧骨高高凸起,眼睛因为持续的疼痛而深深凹陷下去,里面没有泪,
只有一片空洞的、令人心悸的麻木和忍耐。每一次细微的呼吸似乎都牵扯着她脆弱的神经,
带来一阵无法抑制的颤抖。病房里的其他孩子,大多也醒着,睁着恐惧的眼睛,
沉默地看着这人间地狱般的一幕。空气沉重得如同凝固的铅块,
只有小杰那持续不断的、令人心碎的嚎叫在撞击着墙壁。我僵在门口,
左臂的疼痛仿佛消失了,只剩下一种巨大的、令人窒息的无力感。我像个闯入者,
一个带着希望却又亲手将希望碾碎的骗子。我甚至不敢去看小杰妈妈那绝望到空洞的眼神。
喉咙里堵得发慌,我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就在这时,
一个身影快步从我身边掠过,带起一阵微弱的风。是林晚。她径直走到小杰床边,
动作轻柔却坚定地拂开小杰妈妈紧抱着孩子的手,然后俯下身,
小心翼翼地避开孩子因剧痛而绷紧的身体,伸出双手,
极其轻柔地捧住了小杰因为痛苦而扭曲、满是汗水和泪水的小脸。“小杰,看着我。
”她的声音不高,却奇异地穿透了那撕心裂肺的哭嚎,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平静力量,
“看着我,小杰。”奇迹般地,小杰那因剧痛而涣散失焦的眼睛,艰难地转动了一下,
视线竟然真的落到了林晚脸上。他布满泪痕的小脸上,
那双被剧痛折磨得几乎失去神采的眼睛,艰难地转动着,视线挣扎着,
终于聚焦在林晚的脸上。“痛…姐姐…好痛…”他嘶哑地挤出几个破碎的音节,
眼泪再次汹涌而出。“我知道,小杰,我知道很痛。”林晚的声音依旧平稳,
像沉入深潭的玉石,带着一种奇异的抚慰人心的力量。她没有试图否定孩子的痛苦,
只是用指腹极其轻柔地擦拭着他额头上冰冷的汗珠和滚烫的泪水,
动作温柔得像对待一件稀世珍宝。“痛就哭出来,没关系。姐姐在这里。”她一边说着,
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干净柔软的素色手帕,仔细地、一点点地擦去小杰脸上的汗和泪。
然后,她微微侧过身,从旁边的小桌上拿起一个普通的塑料水杯。她没有用吸管,
而是自己先含了一小口水,又吐掉——一个细微到几乎无法察觉的动作,确保水温是适宜的。
接着,她小心翼翼地倾斜杯沿,让几滴清水极其缓慢地浸润小杰干裂出血的嘴唇。
“喝一点点,小杰,润润嗓子。”她的声音低柔得像耳语。
小杰下意识地、极其轻微地啜吸了一下。也许是那几滴水的凉意,
也许是林晚身上那种超越年龄的沉稳和专注带来的奇异安抚,他身体那令人心惊的剧烈痉挛,
竟真的稍稍平缓了一些。虽然痛苦的低吟依旧断断续续,
但那撕心裂肺的嚎叫终于暂时停歇了。他像一只耗尽了所有力气的小兽,
瘫软在姐姐的臂弯里,只剩下沉重的喘息。林晚没有停。她保持着半跪在床边的姿势,
一只手依旧稳稳地托着小杰的头,另一只手则伸向旁边蜷缩着的小娟。
她轻轻拂开小娟额前汗湿的头发,指尖触碰到她冰冷汗湿的额头。“小娟,睡一会儿?
”林晚的声音更轻了,像一片羽毛拂过。小娟没有睁眼,
只是极其轻微地、几乎无法察觉地点了点头。她咬破的嘴唇微微松开,
紧蹙的眉头似乎也舒展了那么一丝丝。林晚拿起旁边一块干净的湿毛巾,没有拧得太干,
带着恰到好处的凉意,极其轻柔地擦拭着小娟的脸颊和脖颈,
避开她因疼痛而敏感脆弱的身体部位。她的动作专注、细致,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温柔。
病房里那股令人窒息的绝望和尖锐的痛苦,竟在这无声的抚慰中,
被悄然撕开了一道微小的缝隙。连小杰妈妈那无声的汹涌泪水,
也仿佛暂时找到了停泊的港湾,她怔怔地看着林晚,
眼神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感激和一种更深的、无法言说的悲怆。我站在门口阴影里,
左臂的疼痛又清晰地回来了,带着一种灼烧感。但更清晰的,是一种震动。林晚,
林振雄的独女,那个本该在“方舟”里享受最后安宁的金丝雀,
却留在了这艘注定沉没的破船最底层的船舱里,做着最卑微也最伟大的救赎。
她的平静不是麻木,她的温柔不是软弱。
那是一种超越了身份、超越了末日、甚至超越了生死的强大力量。她站起身,
目光扫过病房里每一双恐惧或麻木的眼睛,最后落在我身上。她的眼神平静依旧,
但深处似乎燃着一小簇幽微却执拗的火苗。“陈医生,”她走到我面前,声音不高,
却清晰地传入我耳中,“药没了,但人还在。我们得做点什么。
”她的视线落在我用简易硬纸板和布条固定的左臂上,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您的手…需要重新处理。”第八日的晨光,透过布满灰尘和污渍的窗户,吝啬地洒进走廊,
像一层惨淡的灰烬。
空气里弥漫着消毒水、汗液、还有伤口溃烂混合成的、令人作呕的甜腥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