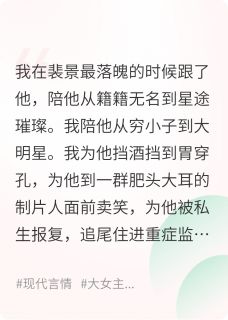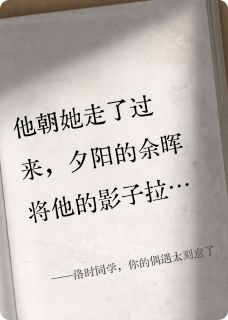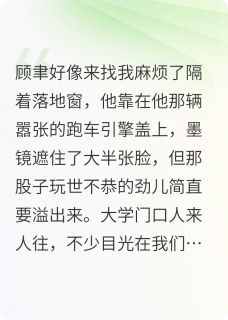齐萧爱上了那个来刺杀他的女人。她认出我是当年灭她满门的杀手,对我百般折磨。
齐萧每每在我还剩一口气的时候出现,温柔将她揽入怀中:“她对齐家还有用。
”但他不知道,我在等科举放榜那天。[1]梁乐春又一次将我的头按进水缸。
辣椒水顺着我的眼鼻耳,钻进每寸毛孔。她一把拽起我湿透的头发:"第八次,你退步了啊。
""嗯?你怎么就有脸活着?"我呛得不住咳嗽,答不出话。她也没指望我回答。
她翻来覆去都不过是自语。为什么她和和美美的一家人死了,
我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还活着?本来我能撑更久。可她来时,我刚从贡院出来。
五千字策论耗尽了我大半气力。暗室外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齐萧缓步而入,
拿了块雪白的帕子,一点点拭净她的手。眸光温柔:"该用晚膳了。"自始至终,
未曾分给我半个眼神。也好。我从未让他看过我的狼狈。
"今日让人做了你最喜欢的桂花糖藕。"梁乐春原是江南贵女,生就一副挑剔胃口。
[2]她或许不明白,我这样的人,无论如何都是要活下去的。十四年前,
我在长安书院的外墙角偷听。我最爱听女夫子讲《尚书》。晔朝真好,女子也可以读书识字。
日日都要从这经过的华丽马车忽然掀开帘角。我和长着双温柔桃花眼的少年对视了一眼。
也仅仅是一眼。后来,我在肮脏的后巷,跟三四个高我一头的孩子抢一个脏馒头。
我发了疯似的护着那馒头,任拳脚雨点般落在身上,几口吞完了难得的饱餐。那时,
我又看见了那双眼睛。"可愿意跟我走?"在他那样温和的语气下,我甚至忘了犹豫。
"愿意。"他给我取名叫阿敛。十年苦训,我成了齐家的一把刀,杀人不见血的刀。
常州知府梁敞一家,在睡梦中死于我手。除了他们躲在床下发抖的小女儿。她以为我看不见,
我也权当看不见。那是我第一次单独行动。回到齐府,我的手才停下颤抖。
沐浴焚香后我去见齐相汇报。退出来时,在门口遇见齐萧。他嗓音懒懒:"回来了。
江南春色如何?""没留意。”"下次带你去看看姑苏的桃花。"我暗暗记在心里。
只是至今还未曾实现。[3]一年前,府里新进了个丫鬟。活泼伶俐,不久就入了齐萧的眼。
某个深夜,她在齐萧的床头挥起匕首。可惜被眼疾手快的暗卫一秒制服。谁知齐萧不但没恼,
反而纵着她。于是,
下毒、放火、趁他沐浴时从天而降搞偷袭……她把刺客能干的活练了个遍。情愫这东西,
本就无道理可讲。往往爱恨之间隔着一层薄纸,一捅就破,再也分不清彼此。
她不再尝试杀了齐萧,却认出了我。“把她给我。”“好。”那丫鬟是梁乐春。乐春。
真是个喜气洋洋的名字。我在梁府房檐上蛰伏的时候,见过他们一家人的其乐融融。那之后,
她将恨意尽数倾泻于我。其实也还好。我从五岁开始接受杀手训练,吃过肉体的苦不计其数。
只是,杀手最忌讳的不过是求饶。这是齐萧教我的。而她只想看我求饶。
[4]过几日是齐萧的生辰。大晔朝中,齐家仍为世家翘楚。自齐相半退后,
事务逐渐移交到齐萧手里。长安权贵都会来为齐萧庆生。梁乐春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我。
虽无正式名分,她已经俨然齐府女主人做派。宴席当日,华灯结彩,宾客如云。
梁乐春伴在齐萧身侧,宛如一对璧人。我隐在暗处扫视人群。突然一道冷光闪过,
直指齐萧后心。我闪身而出,用手握住了匕首。登时鲜血如注。齐萧护着梁乐春后退,
捂住了她的眼睛。小厮模样的刺客被制住,只见他头一歪。不好,吞了毒药。
我掌心血流不止,怕是割断了筋脉。却连眉头都不敢皱一下。我比以前慢了。
从前我能夺刀反制而毫发无伤,如今却只能用血肉挡刀。
昨夜他将我叫去书房:“生辰宴上恐有异动。你多盯着些。”可我比以前慢了。
齐萧声色如常:“下去包扎。”宾客散尽后,齐萧独坐庭中,月光洒在他身上,温柔如水。
他对我招手:“过来。”递来一杯酒,默认我用右手去接。我没有犹豫,
任凭掌心的伤口崩裂,鲜血慢慢染红纱布。“方才慢了半拍,”他轻叹,语气仍然温柔,
“下次,别让我失望。”“是。”他起身拍了下我肩膀,正好碰到我的伤处。
我下意识皱了下眉头。半月前梁乐春刺伤了我的琵琶骨。“好好养伤,别废了。”废了,
便是死路一条。[5]或许真是让我静心养伤,梁乐春竟然一连七八日没再叫我去。
直到听府里的人传。齐萧要成亲了。我五岁进齐府,至今认识他十四年。
齐萧身边几乎没有女人。我是他家趁手的兵器,并不是一个女人。哪怕我每次任务回来,
都要沐浴焚香。生怕玷了那片刻见他的清净。他要和梁乐春成亲了。我头一次藏于自家屋檐,
做了那窥伺之人。齐萧携着梁乐春的手,漫步庭院。他折下一枝桃花,簪到梁乐春鬓边。
她便旋了个身,裙裾拂开一朵柔软的浪。手中把玩着海棠花,突然皱眉:“这花可恶,有刺。
”齐萧忙捉住她手细看,眉头紧蹙。那块他从不离身的玉佩,转瞬在他掌心化作细腻的粉,
亲自为她敷上。瓦片硌着掌心,一抽一抽地疼。原来爱是这样。急切的心疼,
舍不得她受半点苦。齐萧对我一直很温柔。那种温柔似乎是他的本性。非只对我一人。
可梁乐春不同,他爱她。所以可以让她随意处置齐家的兵器。我曾幻想过,
或许他的温柔有几分因我。可如今意识到,那和怜惜一把锋利的刀没什么不同。
[6]我从一个屋檐跳上另一个,不知疲倦。直到天黑。我早就是个流不出眼泪的人了,
我试过。一直到看见红墙绿瓦,我才知竟然到了四九城。禁地森严,忙敛了气息。
却听底下传来一道低沉嗓音:“方圆,你说朕这个皇帝当得有意思吗?”我心头一跳,
紧接着听到尖细的回答:“陛下九五至尊,天下臣服……”皇帝轻笑,
笑声中尽是凉薄与自嘲。“齐家的人把朕当傻子。你可知齐萧前日说什么?
”我连呼吸都不敢大声,等着他们走远。晔朝自先帝起,世家大族掌实权,而皇权旁落。
所以齐家可以豢养杀手,暗杀政敌,形同私兵。我心情复杂地回到齐府。齐萧正在等我。
“伤好些了?”我点头:“劳公子挂心,已无大碍。”“我说的不是手。
”是梁乐春给我的那些。他叹口气:“乐春年幼失孤,性子难免乖戾。这是齐家欠她的,
往后……也就慢慢好了。我代她,与你赔个不是。”我只是摇头:“公子言重了。
”可我替齐家杀第一个人的时候,也只有十四岁。“你比从前话少了些。
”他递来两个瓷瓶:“这是西域来的伤药,白瓶内服,黑瓶外敷。好得快。”“谢公子。
”我伸手去接的时候,他轻轻拢住我的手腕,端详着手心粗粝的长疤。“阿敛,
没有你我可怎么办。”我眼睫轻颤,但只是垂下眼帘。齐萧走了。
我腕上仿佛还残留了抹沉香气息。[7]齐萧叫了我去书房布置任务。
门内传来梁乐春亲昵低语。我始终低着头,不想直视他们任何一个的眼睛。
齐萧派我去岭南刺杀流寇首领。此行凶险在瘴气遍布,是个九死一生的活。
出发前他在廊下拦住我,递来一枚平安符。温声道:“保你无恙。
”我接过时指尖擦过他温热掌心,敛眉掩饰了那半分慌乱。岭南的雨粘腻,
我在沼泽地里趴了三日。毒虫啃噬,伤口溃烂起了高烧。仍取了叛贼首级。
医馆老郎中剜腐肉时,嗅了一口我紧攥着的平安符。“引虫草配鹤顶红,好狠的方子。
”我的伤口开始疼得要命。随着呼吸更疼,快喘不上气来。我回去时,齐萧在书房等我。
温润如常:“辛苦了。”我没做声,只将平安符递还给他。
梁乐春倚在门口:“你怎么还不死?”我笑,淡淡道:“命硬。”回府之前,
我已在贡院门前看过杏榜。“温敛”二字赫然在列。我记得自己的姓氏。那本从不离身的书,
字迹被血污湮没了。我扔了,反正早已倒背如流。[8]婚期定在四月十八,良辰吉日。
除了整座齐府披红挂彩,焕然一新以外,一百六十八抬朱漆箱笼,
一早便流水般抬进三条街外的宅子。填满了那座崭新的梁乐春的“娘家”。这排场,
既是齐家对梁家孤女的补偿,骨子里还是显出齐萧的愧有多重,爱有多深。
偏这冠绝长安的婚礼,与殿试是同一日。我还在换衣服,便听到外头的门落了锁。
“阿敛姑娘,今日是公子大婚,您就在屋里待一日吧。饭菜会有人送来。”我皱起眉。
梁乐春应当明白这道门锁是困不住我的。我心下狐疑,卯足了劲踹门。
反正前头的喜乐震天响。但门闩纹丝不动,我还越来越乏力。门上有迷香。我捂住口鼻,
匕首利落地划过手腕,强迫自己清醒。倒地之前听到木门吱呀一声,
一双纤尘不染的皂靴出现在眼前。再醒来时,手腕包扎完好,离宫门不过几步之遥。
我带着满腹疑问进了保和殿。是谁能在隐秘的齐府小房间里救了我?又为什么要帮我?
勉强收回心思,试纸上的题目竟然是论寒门擢升之道。正是皇帝多年的心思。我早有准备,
答得一气呵成。只是右手字迹不如以前好看了。考完出宫的时候回看了一眼巍峨皇城。
出了成绩我就离开长安。今夜是齐萧的洞房花烛,我在等我的金榜题名。特意挨到深夜回府。
灯却亮着。齐萧竟像候了我多时。一身大红喜袍尚未换下,更衬得他眉目温润如玉。“阿敛,
今日殿试,我听闻了,答得不错。”我心下大乱。“直言不讳,削弱世家寒门当立,
这份胆子,整个晔朝也找不出几个来。”怕是皇帝也是这个时间才看到文章。
他的手竟然伸得这样长。我后退两步低头跪下,却不言语。齐萧走近,
我猛然看到了那双簇新的靴子。我瞪大了眼睛。他拿挑盖头的玉如意挑起我的下巴:“阿敛,
你倒和小时候一般好学。只是,考中玩玩也就够了,往后把这份心收了吧。”我这才看清,
案上搁的正是我的策论。我对他行了三个大礼。四年前救他一命换来的那个承诺,
就在此刻用掉了。“公子,我仍然想考。”我伏在地上。良久,头顶传来一声:“好。
”[9]天蒙蒙亮,我背着包袱离开了齐家。十几年来我留下的东西很少,几本书几件衣裳。
所有女孩家的东西,都没有。除了一支金簪。是及笄那年齐萧送的。他说阿敛也是女孩,
该有件首饰。那簪子,只在他亲手替我簪到发间时戴过那一次。
后来我用它在巷战中扎穿过人的脖子。便不再往头上戴了。出门时洒扫的丫鬟闲话,
说东院的喜烛燃了一夜。听到时像被什么钝物狠狠撞了一下,不痛,只是闷。离开吧,
离开就好了。我挤到人群中,今日迟迟没放榜。“温大人,请随我来。
”丫鬟打扮的女子叫住我。我跟她左拐右拐到了一处院子。院中男子负手而立。
一身低调白衣,却透出难掩的贵气。他转过身:温敛。这声音透着熟悉,是我本不该知道的。
我从未见过圣颜。"齐萧到底是有本事,亲手培养出来的人也是文武双全。
”他忽然发问:“朕的考题,有人答‘寒门当安于农事’。温大人对此,有何高论?
”"若有报国之心,不分寒门士族。“半晌,他突然低声笑起来。
目光扫过我手上的血痂:"齐萧连殿试的策论都敢换,却留着你这双会写字的手。
“我仍保持着行礼的姿势。心里却已翻江倒海。难怪齐萧那么轻易就让我出了齐家。
"温大人起来吧。“我这才不动声色看一眼皇帝。与齐萧差不多年岁,气质却截然不同。
齐萧是温润的玉,而他,是锋利的美。我立即认出,这是八年前冷宫我见过的小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