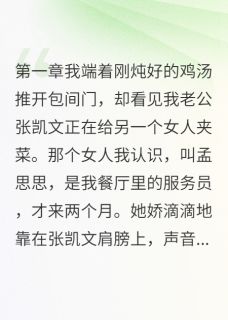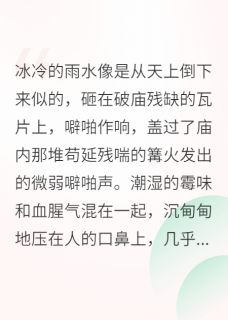
1雨夜救王爷冰冷的雨水像是从天上倒下来似的,砸在破庙残缺的瓦片上,噼啪作响,
盖过了庙内那堆苟延残喘的篝火发出的微弱噼啪声。潮湿的霉味和血腥气混在一起,
沉甸甸地压在人的口鼻上,几乎令人窒息。我,此刻正用尽全身力气,
把一块还算干净的布条死死按在一个男人胸口那狰狞的伤口上。血,
温热的、带着铁锈味的血,依旧透过布料的缝隙,顽固地渗出来,
染红了我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手指。这男人穿着价值不菲的锦袍,
虽然被泥泞和血污糟蹋得不成样子,但那料子骗不了人,是顶顶好的云锦。
他身份绝对不简单。更要命的是,他腰上那块被血浸透的玉佩,
龙纹的爪子清晰得刺眼——这是位王爷!这哪是救了个贵人,分明是捡了个天大的麻烦!
一个不好,我这小小的脑袋就得搬家。可眼下,不救,他马上就得死透。
我咬了咬冻得发紫的下唇,手上力道又加重了几分。“呃……”一声压抑的痛哼突然响起,
低沉沙哑,像砂纸磨过喉咙。我吓得手一抖,差点把布条扔了。猛地抬头,正对上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不知何时睁开了,在跳跃的昏暗火光映照下,深不见底,像两口结了冰的寒潭。
里面翻涌着浓稠的痛苦,但更深处,却是冰封千里的警惕和一种近乎野兽般的凶狠,
死死地攫住了我,仿佛要将我的灵魂都钉在原地。那眼神里的重量,压得我几乎喘不上气。
“你是谁?”他开口了,声音又低又哑,每一个字都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带着血腥气。
他的右手极其缓慢地、却又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力道抬起,冰冷得像块铁,
猛地扼住了我的脖子!指尖的力道瞬间收紧,卡在我的喉骨上,窒息感如同冰冷的潮水,
瞬间灭顶。“说!”他逼视着我,那眼神锐利得能穿透皮肉,直刺灵魂深处。
死亡的恐惧像一只冰冷的手攥住了我的心脏,血液似乎都在倒流。我被他掐得眼前发黑,
徒劳地扒着他铁钳般的手腕,从牙缝里挤出断断续续的声音:“放…放手!
我…我是救你的人!药…药篓…旁边…”我的手指拼命地指向丢在旁边的藤编药篓。
他布满血丝的眼珠极其缓慢地转动了一下,扫过那只沾满泥泞的药篓,
又落回我因缺氧而憋得通红的脸上。那眼神里的暴戾和杀意,如同退潮般缓缓消散了一些,
但那份冰冷的审视和深不可测的警惕,却丝毫未减。扼住我喉咙的手,力道终于松了一线。
新鲜的空气猛地涌入肺叶,呛得我剧烈地咳嗽起来,眼泪都咳了出来。
“救…救我……”他喘着粗气,每一个字都带着胸腔里血沫翻涌的嗬嗬声,
那只手虽然松开了我的脖子,却依旧冰冷地搭在我的肩颈处,仿佛随时准备再次发力拧断它。
他死死盯着我,眼神锐利得惊人,仿佛在评估一件货物的价值,
“条件…你开…”我捂着**辣的脖子,大口喘息,心脏还在疯狂擂鼓。开条件?
跟一个随时能捏死自己的王爷开条件?这简直是刀尖上跳舞!“我……”我嗓子疼得厉害,
声音嘶哑,“小女子只求…只求活命!绝不敢……不敢奢求其他!”“活命?
”他扯了扯嘴角,那弧度冰冷而讽刺,牵动了胸口的伤,又是一阵压抑的闷哼。他缓了缓,
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牢牢锁住我,一字一顿,如同冰冷的铁锤砸下,“好,当本王的王妃,
或者……现在就死!”什么?!我猛地抬头,难以置信地看着他。王妃?他在说什么疯话?
这身份,这血海深仇的处境……让我当他的王妃?这和直接把我架在火上烤有什么区别?
“王…王爷?”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您…您伤得很重,烧糊涂了吧?
小女子只是个乡野医女,粗鄙不堪,怎敢……”“本王清醒得很!”他打断我,
眼神凌厉如刀锋,带着不容置疑的决断。“听着,只三年!三年假凤虚凰,
做场戏给外面的人看。三年后,本王放你自由,保你一世富贵平安。他喘息着,
眼神却锐利地刺向我,“这是你唯一能活命的机会。”“点头,活。”“摇头,死。”“选!
”他搭在我肩颈处的手,指尖微微收紧,那冰冷的触感如同毒蛇的信子,
瞬间让我全身的血液都冻住了。死亡的阴影从未如此刻般清晰、迫近。破庙外,
冷雨依旧倾盆,哗啦啦地冲刷着整个世界。庙内,
只有篝火燃烧的噼啪声和他压抑的、带着血腥味的喘息。巨大的恐惧攫住了我,
像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我的心脏,几乎要把它捏碎。当王妃?假扮的?
这根本就是一条通往悬崖的独木桥!可……不答应?我毫不怀疑,
下一刻我的脖子就会被他轻易折断,像碾死一只蚂蚁。活命。只有活命才有以后。
我死死咬住下唇,直到尝到一丝铁锈般的腥甜。浑身抑制不住地颤抖,牙齿咯咯作响。
在这令人窒息的死寂里,我耗尽了全身的力气,才极其轻微地、幅度小到几乎看不见地,
点了一下头。“好……”喉咙里挤出一个破碎的音节。他似乎耗尽力气,
紧绷的身体骤然松懈下来,那只扼住我命运咽喉的手也无力地垂落下去。
那双深潭般的眼睛缓缓闭上,浓密的睫毛在火光下投下两片阴影,气息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
“契约……”他唇瓣翕动,吐出最后两个字,便彻底昏死过去。
2契约王妃看着那张即使昏迷也透着凛冽寒意的俊脸,我浑身脱力,
瘫坐在冰冷潮湿的地上,后背的衣衫早已被冷汗浸透。篝火的光芒跳跃着,
映照着他苍白的脸和我自己同样惨白的脸。王妃?
我低头看着自己沾满血污和泥泞、冻得通红的双手。这双只会捣药、采草的手,
怎么去握住那象征着泼天富贵和滔天风险的金册宝印?冷雨敲打着残破的屋檐,那声音,
一下下,像是敲在我的心上,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嘶——轻点!
”一声压抑着不耐的低喝在静室内响起,带着刚睡醒的沙哑。
我跪坐在宽大的紫檀木拔步床边,手里捏着蘸了温水的软布,
正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床上男人手臂上一道狰狞的刀伤边缘。布料的摩擦似乎牵动了伤口深处,
引得他眉头紧锁,薄唇抿成一条锋利的线。“王爷恕罪”我立刻缩回手,垂下眼睫,
声音放得又轻又平,“这处伤口太深,粘连了血污,若不清理干净,恐会生脓溃烂。
”我顿了顿,补充道,“奴婢……会尽量再轻些。”王妃?在他眼里,
我大概连个得脸的婢女都不如,不过是件暂时用得顺手的工具罢了。这“王妃”二字,
此刻叫出来,连我自己都觉得讽刺。床上躺着的,
正是那夜破庙里用死亡逼我签下卖身契的煞神——靖王萧珩。
距离那场惊心动魄的雨夜已过去月余,他身上的致命伤在我的全力救治下已无性命之忧,
但失血过多加上伤口反复,让他整个人依旧透着一种病态的苍白和挥之不去的阴沉戾气。
“哼”萧珩从鼻子里哼出一声,算是回应。他闭着眼,俊美却凌厉的侧脸线条绷得很紧,
显然在极力忍耐着疼痛和不耐烦。他不再说话,
室内只剩下我极轻的动作声和他偶尔压抑的抽气声。终于处理完手臂的伤,
我拿起一旁温着的药碗。浓黑的药汁散发着刺鼻的苦味。我舀起一勺,轻轻吹了吹,
递到他唇边。萧珩睁开眼,那双深不见底的黑眸扫过药勺,又落在我脸上,带着审视。
他没有立刻喝,反而开口,声音因伤痛而低哑,
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压迫感:“府里……近来如何?”来了。我心中了然。这月余他重伤卧床,
王府内外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我这个突然冒出来的“救命恩人”兼“准王妃”,
不知被多少双眼睛盯着,明里暗里的试探和刁难从未停过。我稳稳端着药勺,
垂眸恭敬回禀:“回王爷,府中诸事……大体安泰,只是……”我斟酌着用词,
“柳侧妃昨日遣人送来一支百年老参,说是给王爷补身。还有赵夫人,
送来几匹江南新贡的云锦……都收在库房了。”“柳如烟?”萧珩眉梢极细微地挑了一下,
唇角似乎勾起一丝若有若无的冷嘲,“她倒是‘有心’。”他顿了顿,
目光锐利地钉在我脸上,“没人为难你?”为难?我心中苦笑。何止是为难。
柳侧妃送来的那支参,内侍监的老太监私下验过,参是好参,但那装参的锦盒夹层里,
却浸染了极淡的、与参药相冲的寒毒。赵夫人送来的云锦,
其中一匹的丝线用特殊药水浸泡过,接触久了会让人身上起红疹奇痒难耐。这些手段,
既阴毒又隐蔽,若非我自小学医,嗅觉和触觉都远超常人,恐怕早已着了道。“回王爷,
”我面上依旧平静无波,将药勺又往前递了半分,“奴婢身份低微,谨守本分,不敢逾越。
诸位贵人……待奴婢都甚是和善。”和善?那笑容背后的刀子,我每一日都感觉得清清楚楚。
萧珩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锐利得似乎能穿透我的伪装,直看到心底去。他没有再追问,
只是微微偏头,就着我的手,将那勺苦涩的药汁含了进去。
他的薄唇不可避免地碰到了温热的瓷勺边缘。我的指尖微微一颤。“这药……”他咽下药汁,
眉头皱得更紧,语气是毫不掩饰的嫌弃,“苦得倒胃口。”“良药苦口利于病,王爷。
”我又舀起一勺,“您失血太多,元气大伤,这方子加了黄芪、当归、熟地,最是补气养血。
再喝三剂,您就能试着下床走动了。”这药里,我还特意加了一味极珍稀的“血竭”,
化淤生肌有奇效,只是那味道……确实令人作呕。萧珩没说话,只是皱着眉,一口接一口,
就着我的手,沉默地把那一碗浓黑的苦药喝得干干净净。药碗见底,
他额角已渗出细密的冷汗,脸色更白了几分,显是忍耐到了极限。“下去吧。
”他疲惫地闭上眼,挥了挥手,声音带着浓重的倦意。“是。”我如蒙大赦,
迅速收拾好药碗布巾等物,起身准备退下。刚走到门边,身后又传来他低沉的声音,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探究:“你叫……苏妙?”我脚步一顿,心猛地一跳。他记得我的名字?
那夜破庙,我似乎只提过一次。我转过身,垂首应道:“是,奴婢苏妙。”他依旧闭着眼,
仿佛只是随口一问,再无下文。我轻轻带上房门,隔绝了内室的气息。背靠着冰凉的门板,
才惊觉自己的手心全是冷汗。每一次靠近他,都像在万丈深渊的边缘行走。那双眼睛,
即使闭着,也仿佛能洞察一切。苏妙……他为什么特意问这个名字?
仅仅是因为……需要记住这个契约工具的名字吗?
……3深宫惊魂日子在表面的平静与暗地的汹涌中滑过。萧珩的身体恢复得比预想中更快,
那碗碗苦得钻心的汤药功不可没。他已能在侍从的搀扶下在室内行走,
眉宇间的阴鸷虽未散去,但那股萦绕不散的沉疴死气,已淡了许多。这意味着,
我作为“医女”的价值正在减弱。而作为“契约王妃”的戏码,似乎也该提上日程了。
这日午后,阳光难得晴好。我正坐在自己那间狭小却收拾得干净整洁的偏房里,对着铜镜,
笨拙地尝试挽一个稍显复杂的发髻。镜中人眉眼清秀,只是肤色带着点不健康的苍白,
眼神里也总藏着一丝挥之不去的谨慎和疏离。王妃?看着镜子里这张脸,
连我自己都觉得有些荒谬。手指绕了几次发丝,却总是滑脱,弄得一团糟。
“啧”我有些懊恼地放下手。“王妃这是要学梳妆了?
”一个带着笑意的温婉声音在门口响起。我惊得手一抖,梳子差点掉在地上。回头望去,
只见一位丽人扶着门框,巧笑倩兮地看着我。她穿着水红色绣缠枝莲的宫装,身段玲珑,
面若芙蓉,一双水盈盈的眸子顾盼生辉,
正是靖王府如今后院地位最高的女人——侧妃柳如烟。她身后还跟着一个端着托盘的丫鬟,
托盘上放着一碗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羹汤。“柳侧妃?”我连忙起身,屈膝行礼。
“不知侧妃驾临,有失远迎,请侧妃恕罪。”心中警铃大作。柳如烟主动来找我?
黄鼠狼给鸡拜年。“快起来,快起来。”柳如烟莲步轻移,亲自上前虚扶了我一把,
笑容温婉得无懈可击,“都是自家姐妹,何须如此多礼?
”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和凌乱的发髻上扫过,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关切。
“妹妹这发髻……可是想梳个‘朝云近香’?这式样是有些难为妹妹了。要不要姐姐帮你?
”她说着,竟真的伸手要来碰我的头发。我下意识地微微侧身避开,
低声道:“不敢劳烦侧妃,奴婢……我自己慢慢学就好。
”她的指尖带着一股淡淡的、甜腻的脂粉香,却让我莫名地脊背发凉。柳如烟的手停在半空,
脸上的笑容僵了一瞬,眼底飞快地掠过一丝不悦,但转瞬即逝,
又被更浓的笑意取代:“瞧妹妹说的,什么奴婢不奴婢的。王爷既然开了金口,
妹妹迟早是咱们王府正经的主子,这‘王妃’的称呼,早晚要习惯的。”她话锋一转,
示意身后的丫鬟,“姐姐今日新得了一罐上好的血燕,想着妹妹日夜照料王爷辛苦,
特意炖了碗燕窝羹送来,给妹妹补补身子。”那丫鬟立刻上前一步,将托盘奉到我面前。
白瓷碗里,晶莹剔透的燕窝羹冒着热气,香气扑鼻,看着诱人至极。我看着那碗羹,
心中冷笑。血燕?恐怕是加了料的“毒燕”吧?柳如烟的手段,我领教过不止一次了。
上次的寒毒参,上上次的痒疹丝线……这次又是什么?“侧妃厚爱,奴婢感激不尽。
”我垂眸,语气惶恐,“只是……只是奴婢刚用过午膳,此刻实在腹中饱胀,
怕辜负了侧妃的一片心意。不如……”“哎呀,一碗羹汤而已,
妹妹莫不是嫌弃姐姐手艺粗陋?”柳如烟立刻打断我,笑容带上了一丝委屈和不容置疑,
“还是说,妹妹觉得姐姐送来的东西……不干净?”她最后三个字说得又轻又慢,
眼神却陡然变得锐利起来,带着审视和压迫。空气瞬间凝固。她这是拿话在挤兑我,
逼我不得不喝。我心中飞快盘算。硬抗?她毕竟是侧妃,身份压我一头。喝?
谁知道里面加了什么要命的东西?我目光扫过那碗羹汤,
鼻翼微不可察地翕动了一下——除了燕窝的清甜,
似乎……还夹杂着一丝极淡的、几乎被掩盖过去的酸涩气。是夹竹桃的花粉!剂量极微,
一次两次吃不死人,但会慢慢沉积在体内,损伤心脉!好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毒计!
冷汗瞬间浸湿了后背。怎么办?喝是死路一条,不喝……眼前这关怎么过?就在我骑虎难下,
柳如烟眼中得意之色渐浓时,
一个低沉冷冽、带着明显不悦的男声骤然在门口响起:“吵什么?”如同冰水浇头,
屋内的空气瞬间冻结。我和柳如烟同时转头望去。只见萧珩不知何时已站在门口,
身上只披着一件玄色暗纹的常服,脸色依旧带着大病初愈的苍白,但身姿挺拔,
那股久居上位的威势已恢复了大半。他眉峰紧蹙,目光冷冷地扫过屋内,
最后落在我和柳如烟身上,带着明显被打扰的不耐烦。“王…王爷!
”柳如烟脸上的得意和凌厉瞬间消失无踪,
换上的是恰到好处的惊喜、关切和一丝丝被惊扰的惶恐。她连忙屈膝行礼,
声音柔得能滴出水来,“您怎么起身了?您身子还未大好,
太医说要多静养……”她一边说着,一边快步走向萧珩,伸手想去搀扶他。
萧珩却像是没看到她伸过来的手,目光越过她,直接落在我身上,语气平淡无波,
听不出喜怒。“怎么回事?”柳如烟的手尴尬地停在半空,脸色微微一白。我心中念头电转。
柳如烟逼我喝毒羹,萧珩突然出现……这是个机会!一个或许能暂时摆脱柳如烟纠缠的机会,
但更可能……是把自己推向更危险的境地。我深吸一口气,屈膝行礼,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回王爷,柳侧妃体恤奴婢辛苦,特意送了燕窝羹来。
奴婢……感激不尽。”我避重就轻,只提好意,不提逼迫。柳如烟立刻接口,
声音带着委屈:“王爷,妾身只是心疼妹妹。可妹妹似乎……不太领情呢。”她眼波流转,
楚楚可怜地看向萧珩。萧珩的目光在我低垂的脸上停留片刻,
又瞥了一眼丫鬟手中那碗犹自冒着热气的燕窝羹。他薄唇微启,声音不高,
却带着一种奇异的穿透力:“王妃亲手熬的药,本王都一滴不剩地喝了。”他顿了顿,
目光转向柳如烟,眼神陡然变得锐利如刀锋,语气也沉了下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
“怎么,本王王妃的手艺,还比不上你一碗燕窝羹?”这话一出,如同平地惊雷!
柳如烟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干干净净,娇躯晃了晃,难以置信地看着萧珩,又猛地看向我,
那眼神里充满了震惊、怨毒和一丝被当众羞辱的难堪。王妃……他竟当着柳如烟的面,
直接称我为“王妃”!虽然契约里定了名分,
但这还是他第一次在府中其他人面前如此明确地宣示!我猛地抬头看向他,心脏狂跳,
几乎要冲破胸腔。他疯了吗?这戏……演得是不是太过了?!萧珩却不再看柳如烟,
径直朝我走了过来。他的脚步还有些虚浮,但每一步都带着迫人的气势。
在柳如烟惨白如纸的脸色和几乎要喷出火的目光中,他走到我面前,停住。然后,
在所有人惊愕的注视下,他忽然伸出手,一把扣住了我的手腕!
他的掌心带着病后初愈的微凉,力道却大得惊人,不容我丝毫挣扎,猛地将我往前一带!
我猝不及防,整个人踉跄着撞进了他怀里!
一股混合着淡淡药味和冷冽松柏气息的男性气息瞬间将我包围。“王…王爷?
”我惊得魂飞魄散,下意识地挣扎,声音都变了调。他却置若罔闻,
一只手已经拿起我方才慌乱中放在旁边矮几上的、那碗我给自己熬的、晾凉了些的补气药汤。
他垂眸,目光落在我因为挣扎而微微抬起的手上。我的指尖,
还残留着一点刚刚不小心沾上的深褐色药渍。在柳如烟几乎要杀人的目光里,
在满屋子死一般的寂静中,萧珩低下头,
做了一个让所有人血液都几乎凝固的动作——他竟伸出舌尖,轻轻舔舐过我指尖的那点药渍!
温热的、濡湿的触感,如同电流般瞬间窜遍我的全身!我整个人僵在他怀里,大脑一片空白,
连挣扎都忘了。他抬起头,薄唇上沾染了一点药汁的深褐色,
配上他那张苍白俊美却冷厉的脸,竟有种惊心动魄的邪气。
他看也没看旁边面无人色的柳如烟,目光只沉沉地锁在我因极度震惊而瞪大的眼睛上,
声音不高,却清晰地回荡在落针可闻的房间里,
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霸道和……诡异的亲昵:“王妃亲手熬的,一滴都不许浪费。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碗被我喝了一半的药汤,又落回我脸上,
唇角似乎勾起一个极浅、却足以让柳如烟如坠冰窟的弧度,“也包括这一碗。
”柳如烟的身体剧烈地晃了一下,被身后的丫鬟死死扶住才没摔倒。她死死地盯着萧珩,
又死死地盯着被他强行禁锢在怀里的我,那眼神,怨毒得如同淬了剧毒的利刃,
要将我千刀万剐。萧珩却已不再理会她,仿佛刚才那场无形的交锋从未发生。
他松开钳制我的手,却顺势将我手里那半碗温凉的药汤拿了过去,当着所有人的面,仰头,
一饮而尽。喉结滚动,碗底见空。他随手将空碗丢回矮几上,发出清脆的一声响。那声响,
像是砸在柳如烟的心上,也砸在我混乱不堪的心上。“都出去”他冷冷地下了逐客令,
目光甚至没有在柳如烟身上停留一秒,“本王乏了。”柳如烟嘴唇哆嗦着,脸色由白转青,
最后狠狠地剜了我一眼,那眼神里的恨意几乎要化为实质。她终究没敢再多说一个字,
带着满腔的怨毒和羞愤,在丫鬟的搀扶下,踉跄着退了出去。房门被轻轻带上。
屋内只剩下我和萧珩。空气里还残留着燕窝羹的甜香、药汤的苦涩,
以及他身上那股冷冽的气息。我僵在原地,指尖被他舌尖舔过的地方,
那温热的、濡湿的触感,如同烙印般灼烫。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擂动,几乎要撞碎肋骨。
刚才那一幕幕冲击太过强烈,我的大脑一片混乱,根本无法思考。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仅仅是为了震慑柳如烟?还是……这契约里的戏,他演得太过投入,连自己都骗过了?
萧珩却仿佛只是做了一件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他抬手,用指腹随意地抹去唇边残留的药渍,
动作自然。然后,他转过身,深邃的目光落在我依旧煞白的脸上。“吓着了?”他开口,
声音恢复了一贯的低沉平静,听不出任何情绪,
仿佛刚才那个当众做出惊世骇俗之举的人不是他。我猛地回神,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拉开距离,声音带着无法控制的颤抖:“王…王爷……您…您这是何意?
”指尖残留的奇异触感还在提醒我方才的惊悚。萧珩向前逼近一步,
高大的身影带着无形的压力笼罩下来。他微微低下头,那张俊美却冷硬的脸离我极近,
近得我能清晰地看到他深邃眼瞳中自己惊慌失措的倒影。“何意?”他薄唇轻启,
呼出的气息拂过我的额发,带着一丝药味的微苦,声音压得极低,
却字字清晰地敲打在我的耳膜上,带着一种令人心惊的玩味和警告:“契约第一条,做戏,
要做足。”他的目光如同冰冷的探针,刺入我慌乱的眼睛深处,声音更低,更沉,
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掌控力:“苏妙,记住你的身份。在所有人眼里,
你必须是本王‘心爱’的王妃。收起你那点微不足道的害怕和犹豫。”他顿了一顿,
眼神锐利如刀锋,仿佛要将我所有的心思都剖开,“否则,本王能给你活路,也能随时收回。
”冰冷的警告如同淬了冰的针,狠狠扎进我的心脏,
瞬间将那点因他反常举动而生出的、不合时宜的混乱和悸动冻结成冰。是啊,契约。
只是做戏。他刚才所做的一切,那令人窒息的拥抱,那惊世骇俗的举动,
不过是为了在柳如烟面前,将这个“宠爱王妃”的戏码演得更加逼真,更加无懈可击。
为了堵住悠悠众口,为了暂时压下府中蠢蠢欲动的暗流。至于我的感受?我的恐惧?
我的羞耻?在他眼中,恐怕连尘埃都不如。我只是一个签了卖身契的工具,
一个必须完美扮演“心爱王妃”的傀儡。指尖残留的那点温热触感,此刻只余下冰冷的讽刺。
心口深处,那点连自己都未曾完全察觉的、被那极致霸道亲昵所撩拨起的细微波澜,
瞬间被这彻骨的寒意碾得粉碎。“是……奴婢明白。”我垂下眼睫,
将所有翻涌的情绪死死压回心底最深处,声而平板,
干涩重新变回了那个温顺、恭敬、谨守“本分”的契约工具,“谢王爷……提点。
”萧珩似乎满意于我瞬间的驯服。他直起身,那股迫人的压力随之稍减,
但眼神依旧锐利地审视着我,仿佛在确认一块工具是否足够趁手。
“明白就好”他淡淡地丢下这句话,转身走向内室,背影挺拔却依旧带着大病初愈的虚弱感。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消失在屏风后,才缓缓抬起手,
用力地、反复地擦拭着方才被他舌尖触碰过的指尖。皮肤被擦得发红发烫,
可那种被烙下的、带着羞辱和警示的奇异感觉,却顽固地残留着,挥之不去。
做戏要做足……心爱的王妃……指尖的刺痛感提醒着我这虚幻身份下的冰冷现实。
这靖王府的富贵囚笼,每一刻的呼吸,都伴随着致命的危机。而那个掌控着生杀予夺的男人,
心思深沉如海,冷酷如刀。他刚才的举动,与其说是“宠爱”,
不如说是一种更深的警告和掌控——提醒我认清位置,提醒我这“王妃”的冠冕下,
拴着的是一条随时会被收紧的锁链。阳光透过窗棂,在地面投下斑驳的光影。我静静地站着,
只觉得这满室的“富贵”气息,都带着一股令人作呕的、冰冷的血腥味。
……4太后病危萧珩的身体以惊人的速度恢复着。那碗碗苦药和珍贵的药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