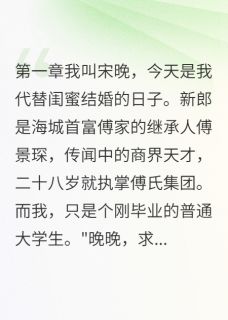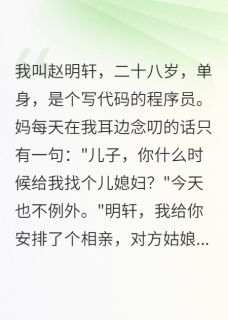第一章:温柔的陷阱十七岁的夏天,本该是橘子汽水和冰西瓜的味道。
窗外的香樟树被阳光晒得懒洋洋的,蝉鸣声像永不疲倦的催眠曲。我坐在画架前,画板上,
是邻家那个叫江澈的少年。他穿着白色的T恤,坐在篮球架下,仰头喝着水,喉结滚动,
汗水顺着他利落的下颌线滑落。我叫林未,一个在父母和老师眼中,有些“孤僻”的女孩。
他们不懂,为什么我不喜欢和同龄人出去逛街看电影,却愿意花一整个下午的时间,
用画笔和色彩,构筑一个只属于我自己的世界。他们更不懂,这个世界里,唯一的常驻民,
是江澈。江澈比我大四岁,是那种所有父母都喜欢的“别人家的孩子”。
他考上了最好的大学,是校篮球队的主力,性格阳光,笑容温暖,像这个沉闷夏日里,
唯一的一缕清风。他从不觉得我孤僻。他会搬个小马扎,坐在我的画室里,看着我调色,
一待就是一下午。他会带我去我从没去过的、城市边缘的废弃工厂,说那里的光影和线条,
有种颓败的美感,适合我的画风。他会认真地看我的每一幅画,然后用他那好听的声音,
准确地说出我藏在色彩背后的、那些说不出口的情绪。他是我的知己,是我晦暗青春里,
唯一的光。所以,当姐姐林静,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笑着走进我的画室时,
我并没有感到任何不对劲。林静是另一个“别人家的孩子”,是我的反面。她品学兼优,
温柔懂事,会弹钢琴,会跳芭蕾,在父母面前永远是那副乖巧可人的模样。
她是我们家的骄傲,也是我……永远无法企及的榜样。“未未,画得真好。”她站在我身后,
看着画板上的江澈,声音一如既往的温柔,“你和阿澈,感情真好。”我“嗯”了一声,
没有回头。我不知道该如何与她相处。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姐妹,却又像是活在两个世界的人。
“对了,未未,”她放下果盘,状似无意地提起,“下周,爸妈想送你去一个地方。
是一个全封闭的艺术夏令营,请的都是国内顶尖的老师,可以系统地学画画和创作。我觉得,
特别适合你。”我停下了画笔,有些惊讶地回头看她。爸妈……会这么好心?
他们一向觉得我画画是“不务正业”,是“浪费时间”。“真的吗?”“当然是真的。
”林静的笑容,无懈可击,“爸妈也是看你快高考了,压力大,想让你出去散散心,顺便,
也能为你的艺考加分。他们知道你喜欢,特意托了好多关系才报上名的。不过,
”她话锋一转,“那个夏令营是全封闭式管理,不能带手机和电脑,
说是为了让学生能更专心地投入创作。所以,你得做好准备哦。”不能带手机?我皱了皱眉。
这意味着,我将有半个月的时间,无法和江澈联系。似乎是看出了我的犹豫,
林静又笑着补充道:“你放心,我都跟阿澈说过了。他也很支持你去呢,说等你回来,
就能看到一个更厉害的小画家了。”听到“江澈”的名字,我心中最后的一丝疑虑,
也打消了。我天真地以为,这真的是父母迟来的关爱,是姐姐对我未来的支持。我甚至,
还因此对他们,生出了一丝久违的、温暖的愧疚感。接下来的一周,
家里充满了一种诡异的、其乐融融的氛围。妈妈不再唠叨我整天待在房间里,
还特意为我买了新衣服和画具。爸爸也难得地,没有板着脸教训我,
甚至还主动问我钱够不够用。姐姐林静,更是对我无微不-至。她帮我收拾行李,
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要注意身体,要和老师同学好好相处。她的眼神里,
充满了“关切”和“不舍”,真实得让我都有些动容。出发那天,江澈也来了。
他揉了揉我的头发,笑着说:“未未,在那边好好学。等你回来,我带你去看海边的日出。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我以为,我即将踏上的,
是一条通往艺术殿堂的金色大道。我以为,等待我的,是更广阔的天空,
和江澈那个关于日出的、浪漫的约定。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满心欢喜地,主动地,
走上的是一条……由我最亲的家人,为我铺设的,通往地狱的,不归路。
第二章:黑车出发那天,是个阴天。天空灰蒙蒙的,
像是被一块巨大的、湿漉漉的脏抹布盖住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暴雨将至的沉闷气息。
一辆黑色的、没有悬挂任何牌照的商务车,准时停在了我家的楼下。
车上下来两个穿着黑色T恤的男人,身材魁梧,表情冷漠,剃着寸头,
手臂上还有着狰狞的纹身。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下意识地觉得有些不对劲。
艺术夏令营的老师……会长成这样吗?“别怕,未未。”姐姐林静笑着,挽住了我的胳膊,
声音温柔地安抚我,“这是夏令营的生活教官,他们是退伍军人,要求比较严格而已。
都是为了你们好。”爸爸妈妈也站在旁边,脸上带着我看不懂的、复杂的表情。
妈妈的眼眶有些红,她走上前,抱了我一下,在我耳边说:“未未,去了那边,要听话,
知道吗?要……好好改造。”改造?我愣住了。夏令营……为什么要用“改造”这个词?
我心中的不安,越来越强烈。“妈,你们到底要送我去哪里?”我挣脱她的怀抱,
警惕地看着他们。“就是夏令营啊,傻孩子。”爸爸板着脸,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说,
“别问那么多了,快上车吧,别让老师等急了。”他说着,就和那两个黑衣男人一起,
半推半搡地,将我往车门口送。“我不去!”我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开始激烈地反抗,“你们放开我!这不是什么夏令营!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我试图向站在一旁的江澈求救,但他也被我父母拦住了。“阿澈,你别管,
这是我们的家事。”爸爸用一种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对江澈说。江澈的眉头紧锁,
他想上前,却被我爸死死地挡住。而就在我挣扎的时候,那两个黑衣男人,
失去了所有的耐心。其中一个,用一只铁钳般的大手,捂住了我的嘴。另一个,
则粗暴地反剪我的双手,将我整个人,像拖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样,
拖向了那辆黑色的商务车。车门被拉开,里面,是密不透风的黑暗。我惊恐地瞪大了眼睛,
拼命地摇头,发出“呜呜”的、绝望的悲鸣。我看向我的家人。我的姐姐林静,站在不远处,
脸上依旧挂着那副温柔的、无懈可击的笑容。她的眼神里,没有一丝不忍,反而,
藏着一抹我从未见过的、快意的、冰冷的光。我的妈妈,别过了头,用手帕捂住了脸,
仿佛不忍心看这残忍的一幕。我的爸爸,则依旧板着那张冷硬的脸,眼神躲闪,
不敢与我对视。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了。这不是一场误会。这是一场,由我最亲的家人,
联手为我设下的,温柔的陷阱。他们,要亲手,把我,推入深渊。“放开她!
”江澈的怒吼声,从后面传来。他终于挣脱了我爸的阻拦,像一头愤怒的豹子,冲了过来。
但,一切都晚了。我已经被那两个男人,粗暴地,塞进了车里。车门,“砰”的一声,
被重重地关上,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光线和声音。我最后看到的画面,
是江澈那张充满了震惊、愤怒和担忧的脸,和姐姐林静,
嘴角那抹一闪而过的、胜利的、诡异的微笑。车子,发动了。我被其中一个男人,
死死地按在座位上,动弹不得。我不知道这辆车,要开向哪里。我只知道,从这一刻起,
我的人生,我所熟悉的一切,都将,被彻底地,打败。黑暗中,我停止了挣扎,不再哭喊。
我只是睁大眼睛,将姐姐那抹微笑,将父母那冷漠的侧脸,将江澈那无能为力的怒吼,
像用刻刀一样,一笔一画地,深深地,刻进了我的脑海里,刻进了我的骨血里。
我记住你们了。我对自己说。你们每一个人,我都记住了。如果我还能活着回来,我发誓,
今天你们加诸在我身上所有的痛苦和屈辱,我一定会,千倍百倍地,还给你们。
第三章:地狱的“欢迎仪式”黑车在颠簸的路上,行驶了多久,我不知道。
在那个密不透风的、充满了汗臭和烟草味的狭小空间里,时间失去了意义。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反抗和求救,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我像一个被宣判了死刑的囚犯,被押送往未知的刑场。终于,车子停了下来。车门被拉开,
刺眼的白光射了进来,我下意识地用手挡住眼睛。我被两个黑衣男人,
粗暴地从车上拽了下来。脚下,是坑坑洼洼的水泥地。空气中,
弥漫着一股潮湿的、发霉的味道。我环顾四周,
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荒凉的、被高墙和电网包围的大院里。院子中央,
是一栋灰白色的、看起来像废弃工厂改造的、毫无生气的五层小楼。楼的顶端,
挂着一个巨大的、已经有些生锈的招牌。上面用红色的油漆,
写着几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华新行为矫正中心。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拯救迷途少年,
重塑崭新人生”。行为矫-正中心?我的心,沉到了谷底。这不是什么夏令营,
也不是什么艺术学校。这是一个……一个在网络上,有过无数恐怖传闻的,地方。
我曾在一个深夜新闻里,看到过关于这类学校的报道。电击,虐待,体罚,
精神控制……无数的“叛逆少年”,被绝望的父母送进这里,然后,
被折磨成一个个听话的、眼神空洞的“行尸走肉”。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种只存在于新闻里的地狱,有一天,会降临在我的身上。而亲手把我推下来的,
是我最亲的家人。“欢迎来到华新,新同学。”一个油腻的声音,从我面前传来。我抬起头,
看到一个穿着白大褂、戴着金丝眼镜、挺着啤酒肚的中年男人,正满脸堆笑地看着我。
他的笑容,像一条吐着信子的毒蛇,让我不寒而栗。他就是这所“学校”的主任,杨万里,
后来,我称他为“杨阎王”。“杨主任,人给您带来了。”把我押来的那个黑衣男人,
恭敬地对他说。“辛苦了。”杨主任点了点头,然后,将他那双小眼睛,落在了我的身上,
上下打量着,像是在审视一件货物。“嗯,看起来是个好苗子。就是眼神……太倔了。
不过没关系,到了这里,再硬的骨头,我们也能给她磨平了。”他笑着,向我伸出手:“来,
林未同学,跟杨主任进去吧。以后,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滚开!
”我像一只被激怒的猫,狠狠地打开了他的手,用尽全身的力气,向着大门的方向跑去,
“我不是你们的学生!你们这是非法拘禁!我要报警!”然而,我还没跑出两步,
就被那两个黑衣男人,一左一右,死死地架住了。“报警?”杨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冰冷的、残忍的狞笑,“在这里,我,就是法律。”“看来,
我们的新同学,需要先上一堂‘入学教育课’啊。”他对手下使了个眼色,
“带她去‘治疗室’,给她进行第一次‘醒脑治疗’。电量……开到最大。让她好好地,
清醒清醒。”治疗室?醒脑治疗?我虽然不知道那具体是什么,但从他那残忍的笑容里,
我已经预感到了,那将是何等恐怖的折磨。我开始疯狂地挣扎,尖叫,哭喊。“放开我!
你们这群魔鬼!畜生!我爸妈给了你们多少钱?!我给你们双倍!不!十倍!放我走!”但,
无济于事。我被他们,拖进了一间充满了浓重消毒水味道的、冰冷的白色房间。房间的中央,
摆着一张冰冷的铁床,上面,布满了皮质的束缚带。床的旁边,
是一台看起来像老式心电图仪的、闪烁着诡异绿光的仪器,上面连接着两个金属的电极片。
我被他们粗暴地按在那张床上,手腕、脚腕、额头,都被冰冷的束缚带,死死地捆住。
我看着那个戴着白手套,拿着电极片,一步步向我走来的、面无表情的“医生”,
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入骨髓的恐惧。
“不……不要……求求你们……放过我……”我的声音,因为恐惧而颤抖,带上了哭腔。
但没有人理会我的哀求。杨主任就站在旁边,冷冷地看着,像是在欣赏一场有趣的表演。
“开始吧。”他下令。那个“医生”,将冰冷的、涂满了导电膏的电极片,
贴在了我的太阳穴上。“林未同学,别怕。”杨主任的声音,像来自地狱的魔鬼的低语,
“很快,你就会感谢我们的。我们会帮助你,戒掉网瘾,戒掉那些不该有的、叛逆的思想,
让你……重获新生。”下一秒。一股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毁灭性的剧痛,从我的太阳穴,
瞬间传遍了我的全身!我感觉自己的大脑,像是被几千伏的高压电流,狠狠地击穿了!
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剧烈抽搐,痉挛,牙齿死死地咬在一起,发出了“咯咯”的声响。
我的眼前,一片刺眼的白光,所有的声音,都离我远去。我甚至,连惨叫声,都发不出来。
我只感觉,我的灵魂,正在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强行地,从我的身体里,撕扯出去。
在意识彻底陷入黑暗的前一秒,我的脑海里,只剩下最后一个念头。这不是学校。
这是……地狱。第四章:地狱的规则我不知道自己昏迷了多久。当我再次恢复意识时,
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冰冷的、散发着霉味的木板床上。周围,
是一个狭小的、只有不到十平米的房间。房间里,除了我身下的这张床,
和对面的另一张同样的床之外,再无他物。墙壁是灰色的,上面布满了各种划痕和污渍。
头顶,一扇小小的、被铁栅栏封死的窗户,透进一丝微弱的、病态的光。我的头,
像是要裂开一样疼。太阳穴的位置,还残留着被电击后的、灼烧般的痛感。
我挣扎着想坐起来,却发现自己浑身酸软,没有一丝力气。
我换上了一身灰蓝色的、宽大的、像是囚服一样的统一制服。我那一头及腰的长发,
也被剪成了参差不齐的、可笑的短发。镜子里,映出一张苍白、陌生、眼神空洞的脸。
我几乎认不出,那是我自己。“醒了?”一个冷漠的、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从对面传来。
我抬起头,看到对面床上,坐着一个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她和我穿着同样的“囚服”,
留着同样的短发,瘦得像一根竹竿,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她的眼神,也和我一样,空洞,
死寂,像一潭不会起任何波澜的死水。“这里是哪里?”我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喉咙像是被火烧过一样。“华新行为矫正中心。”女孩淡淡地回答,
仿佛在说一个与自己无关的地方,“或者,你可以叫它……地狱18层。
”她就是后来成为我唯一盟友的,阿九。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名,因为在这里,
名字是没有意义的。所有人,都只有一个代号。而她,是第九个被送进这个房间的。
“我……我要回家……我要离开这里……”我挣扎着,想下床。“别白费力气了。
”阿九看着我,那眼神,像是在看一个初生的、不懂事的婴儿,
“你没看到外面的高墙和电网吗?你没尝过杨阎王的‘醒脑治疗’吗?来了这里,
除非他们认为你已经被‘格式化’成功了,否则,你一辈子也别想出去。
”“不……我没有病!我没有网瘾!是他们骗我来的!是我姐姐!是我爸妈!
他们……”我说着,眼泪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阿九看着我,眼神里,没有同情,
只有一丝麻木的了然。“在这里,每个人都说自己没病。每个人,都说是被家人骗来的。
”她说,“但在这里,你有没有病,不是你说了算,
是杨阎-王和他手下那群穿着白大褂的魔鬼,说了算。”就在这时,房间的铁门,
“哐当”一声,被粗暴地打开了。一个穿着迷彩服、身材高大、满脸横肉的“教官”,
走了进来。他手里,还拿着一根长长的、闪烁着蓝色电弧的电击棍。“73号!起床!
到**时间了!”他用电击棍,不耐烦地敲了敲我的床沿。73号,这是我的新代号。
“我不是73号!我叫林未!”我抬起头,用尽全身的力气,对他吼道,
“你们这是非-法-拘-禁!你们没有权利这么对我!”“哟呵?
”那个教官被我的反抗逗笑了,他走到我面前,用电击棍,抬起我的下巴,脸上,
是猫捉老鼠般的戏谑,“还是个带刺的?我告诉你,在这里,别跟我提什么权利!老子的话,
就是规矩!”“我说了!我没有病!放我出去!”我死死地瞪着他。“看来,
杨主任的‘醒脑治疗’,对你效果还不够啊。”教官的脸色,沉了下来,“没关系,
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学会,什么叫‘规矩’!”说完,他手中的电击棍,
带着“滋滋”的电流声,狠狠地,戳向了我的小腹!“啊——!
”又一阵剧烈的、撕心裂肺的剧痛,传遍了我的全身!我疼得蜷缩成一团,在床上翻滚,
哀嚎。但他没有停手。电击棍,一次又一次地,落在我的身上。我的意识,在剧痛中,
渐渐模糊。我不知道这场折磨,持续了多久。等我再次醒来,
发现自己被关在了一个更小的、伸手不见五指的“禁闭室”里。这里,阴暗,潮湿,
充满了尿骚和腐烂的味道。我浑身是伤,又冷又饿,连动一根手指的力气都没有。
就在我以为自己会就这么死在这里的时候。禁闭室的小铁门,被打开了一条缝。
一张没有表情的脸,出现在了门口。是阿九。她趁着送饭的机会,偷偷地来看我。
她将一个硬邦邦的、已经冷掉的馒头,塞到了我的手里。然后,她蹲下身,
看着蜷缩在角落里,狼狈不堪的我,用她那贯有的、冷漠的声音,说出了我在这里,
学到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带血的生存法则。“在这里,反抗,是没用的。
”“你想报仇吗?”我抬起头,看着她。“想,就先学会伪装。”“想活下去,
就先变成一条……听话的狗。”第五章:阿九的“教导”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禁闭室里,
阿九的话,像一把冰冷的钥匙,捅进了我被仇恨和恐惧堵死的心。“狗?
”我虚弱地靠在墙上,嘴里咀嚼着那个硬得像石头的馒头,自嘲地笑了笑,“我现在,
连狗都不如。”“不。”阿九摇了摇头,她的眼神在黑暗中,像两点微弱的星火,“狗,
至少还知道摇尾乞怜,能换来一口吃的。而你,只会龇牙咧嘴,结果,
换来的只有更狠的毒打。”我沉默了。她说的是事实。我的反抗,除了让我遍体鳞伤,
没有任何意义。“你以为杨阎王和那些教官,是真的想‘治好’我们吗?”阿九的声音,
带着一丝不属于她这个年纪的、深刻的嘲讽,“别傻了。
他们只是在享受这种掌控一切、肆意折磨别人的**。我们越是痛苦,越是反抗,
他们就越是兴奋。”“而我们的父母,”她顿了顿,声音里,
多了一丝连她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悲凉,“他们把我们送进来,花了那么大一笔钱,
他们需要的,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
而是一个‘听话’的、被驯服的、符合他们期望的‘产品’。杨阎王,就是在为他们,
生产这个‘产品’。”我看着她,这个和我年纪相仿,
却仿佛已经看透了世间所有黑暗的女孩,心中,涌起一股巨大的悲哀。“那你呢?”我问,
“你也是……”“我?”她扯了扯嘴角,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我爸妈,
嫌我考不上重点大学,丢了他们的脸。他们觉得我打游戏是‘不求上进’,是‘精神**’。
所以,他们把我送进来,让杨主任,帮我‘戒掉’那些不该有的‘梦想’。”“我进来,
已经一年了。”她说,“我反抗过,绝食过,甚至……自杀过。”她撩起自己的袖子,
借着门缝透进来的微光,我看到,她那瘦骨嶙-峋的手腕上,
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狰狞的伤疤。“但都没用。”她平静地放下袖子,“他们有的是办法,
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直到,你彻底放弃所有的希望和尊严。”“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的声音里,充满了绝望。“想活下去,想出去,想报仇,”阿九看着我的眼睛,
一字一句地说道,“就要先学会,在这里,活下去。”“怎么活?”“第一,学会伪装。
”阿九说,“从明天起,收起你那可笑的、不屈的眼神。他们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让你吃饭,你就大口地吃;让你跑步,你就跑到虚脱;让你在‘忏悔大会’上哭,
你就哭得比谁都伤心。”“第二,学会观察。”她继续说道,“观察这里的每一个教官,
每一个‘医生’,他们的性格,他们的弱点,他们的作息规律。观察这里的每一个角落,
每一个摄像头,每一扇门的开关时间。”“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学会忍耐。”她的声音,
压得更低了,“把所有的恨,所有的不甘,都给我,咽回肚子里。把它们,
变成你活下去的养料。在这里,眼泪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值钱的东西,比我们的命,还贱。
”说完,她站起身,准备离开。“为什么要帮我?”我忍不住问。阿九的脚步顿了一下,
她没有回头,只是淡淡地,留下了一句话。“因为,我从你那双还没被彻底磨灭的眼睛里,
看到了一点……和我当初一样的,不甘心的火。”“我不想,看着它,就这么熄灭了。
”“也因为……”“我一个人,逃不出去。”说完,她消失在了黑暗中。铁门,
“哐当”一声,再次被锁上。禁闭室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在冰冷的墙壁上,
将最后一口馒头,狠狠地,咽了下去。我看着手腕上,
被电击棍烫出的、一个个紫黑色的伤痕,心中,那股被压抑的、名为“仇恨”的火焰,
非但没有熄灭,反而,在阿九那番话的浇灌下,燃烧得,更加疯狂,更加旺盛。阿九说得对。
我要活下去。我要像一条最卑微、最听话的狗一样,在这里,活下去。然后,我要找到机会,
逃出去。最后,我要让所有伤害过我的人,都付出,比我惨烈千倍、万倍的代价!
从这一天起,那个天真、敏感、骄傲的林未,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代号“73”的,
带着复仇火焰的,行尸走肉。第六章:模范生的“忏悔”从禁闭室出来后,我变了。
变得……“听话”了。每天早上五点半,当刺耳的起床哨声响起时,我不再像以前那样赖床,
而是第一个,从床上爬起来,用三分钟的时间,叠好那床像豆腐块一样、棱角分明的被子。
早操时间,我不再消极怠过,而是跟着教官的口令,一遍又一遍地跑着,
喊着那些可笑的口号,直到跑到喉咙沙哑,跑到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吃饭的时候,
我不再挑剔那些闻起来像猪食一样的、黏糊糊的饭菜。我端着饭盆,大口大口地,
将它们全部咽下去。因为阿九说过,只有吃饱了,才有力气,去恨,去谋划。课堂上,
那些所谓的“国学大师”、“心理专家”,讲着那些扭曲的、漏洞百出的“感恩理论”时,
我不再像以前那样,在下面翻白眼,或者用沉默来对抗。我坐得笔直,手里拿着笔和本子,
认真地“记着笔记”,脸上,是恰到好处的、求知若渴的表情。我甚至,开始主动地,
向教官“汇报思想”。“报告教官,我今天学习了《弟子规》,深刻地认识到,
我以前是多么的不孝。我顶撞父母,沉迷网络,辜负了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我站在教官的办公室里,低着头,声音里,充满了“悔恨”。
教官满意地点了点头:“嗯,73号,有进步。继续努力。”我最大的“进步”,
体现在每周一次的“亲情连线”和“忏悔大会”上。“亲情连线”,
是学校用来向家长展示“教育成果”的保留项目。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酝酿已久的情绪,
瞬间爆发。“妈!是我!未未!”我对着听筒,放声大哭,“妈!我好想你!我想回家!
”“未未啊……”电话那头,传来妈妈迟疑的声音。“妈!你别担心!我在这里很好!
杨主任和教官们,都对我很好!他们就像我的再生父母一样,教我做人,教我感恩!
我以前太不懂事了,总是惹你和爸爸生气,我对不起你们!我保证,我以后一定改!
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做人,再也不玩游戏,再也不画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了!
”我哭得声泪俱下,泣不成声,演技之逼真,连我自己都快要信了。电话那头的妈妈,
显然被我的“转变”惊呆了,也跟着哭了起来:“……好……好孩子……未未,
你终于……终于懂事了……”挂了电话,我擦干眼泪,看到站在一旁监听的杨主任,
脸上露出了满意的、赞许的笑容。而“忏悔大会”,则是我的“封神之作”。所有学生,
都要轮流站到台-上,面对着墙上那面巨大的、写着“感恩、孝道、责任”的旗帜,
忏悔自己过去的“罪行”。轮到我时,我走上台,拿着话筒,未语泪先流。“我叫林未,
代号73。今天,我要向我的父母,向我的姐姐,向杨主任和所有的教官,
做一次最深刻的忏悔……”我从我三岁时打碎了邻居家的玻璃,嫁祸给姐姐说起,
一直忏悔到我十七岁时,为了买一块新的数位板,而欺骗父母说是学校要交的资料费。
我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谎话连篇、自私自利、沉迷网络、无可救药的“坏女孩”。
我一边说,一边用尽全力地,扇着自己的耳光。“啪!啪!啪!”清脆的响声,
回荡在整个礼堂里。“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沉迷网络,那都是精神**!
我不该画画,那都是浪费时间!我不该不听父母的话,他们都是为我好!我不该嫉妒我姐姐,
她比我优秀,比我懂事!都是我的错!”“是华新!是杨主任!是各位教官!像一盏明灯,
照亮了我黑暗的人生!是你们,把我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是你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感谢你们!我发誓,我以后,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我哭倒在台上,浑身抽搐,
像一个得到了神明救赎的、最虔诚的信徒。台下,掌声雷动。杨主任亲自走上台,
将我扶了起来,对着所有人说:“大家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华新教育的成果!
这就是一个迷途知返的、成功的案例!73号,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学校的‘模范生’!
”从那天起,我成了杨主任口中,最得意的“作品”。我获得了比别人更多的自由。
我可以在休息时间,不用参加集体活动。我甚至,
被安排去打扫杨主任那间戒备森严的办公室。所有人都以为,73号,
已经被彻底地“格式化”了。只有我自己知道,在那副顺从的、感恩戴德的面具之下,
隐藏着的,是一颗怎样的、被仇恨浸泡得冰冷而坚硬的心。我的表演,才刚刚开始。
而我的猎物们,还对此,一无所知。第七章:秘密的“武器”成为“模范生”,
是我复仇计划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它像一张通行证,
让我在这个处处都是监视和高墙的地狱里,获得了一丝喘息和行动的空间。
杨主任对我的“转变”非常满意,他经常在各种场合,把我当成正面典型来宣传。他觉得,
我已经彻底被他那套扭曲的理论洗脑,变成了一个对他感恩戴德的、最忠实的“信徒”。
因此,他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来悔恨终生的决定——让我负责打扫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
是整个学校的“心脏”,也是罪恶的“中枢”。里面,存放着所有学生的档案,
所有家长的联系方式和“捐赠”记录,
以及……他用来向上级和外界炫耀的、所谓的“教学成果”。第一次走进那间办公室时,
我的心,在狂跳。但我脸上,依旧是那副谦卑而恭敬的表情。我小心翼翼地,擦拭着办公桌,
整理着书架,将每一个角落,都打扫得一尘不染。杨主任偶尔会坐在他的老板椅上,
一边喝着茶,一边用一种审视的、满意的目光看着我。“小林啊,
”他甚至开始用一种亲切的口吻称呼我,“干得不错。你看看,人只要思想端正了,
做什么事,都像模像样。等你出去了,可得好好感谢你的父母和姐姐,是他们,
把你从泥潭里拉出来的。”“是,主任。我一辈子都感谢他们。”我低着头,
声音里充满了“感激”。但我的眼睛,却在利用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瞬间,
飞快地扫视着办公室里的每一个细节。抽屉的位置,文件的分类,
电脑的密码(他输入密码时,我假装在擦地,用眼角的余光,记下了他手指的动作),
保险柜的型号……我像一块干燥的海绵,疯狂地吸收着这里所有可能用得上的信息。终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