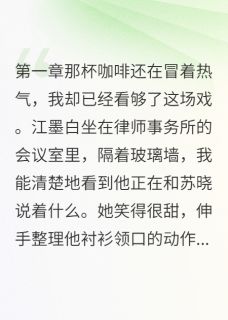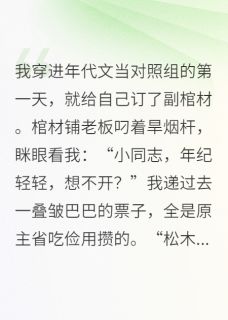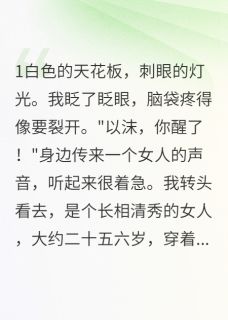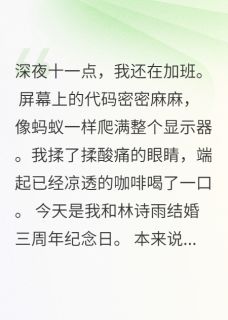夜,像一块巨大的墨蓝色天鹅绒,温柔地覆盖了笃行园。
白日的喧嚣沉淀下来,宿舍里只剩下室友们均匀绵长的呼吸声。
林九九躺在床上,却毫无睡意。
文娱部面试成功的兴奋还未完全褪去,白天苏心然那灿烂的挥手,像一枚投入心湖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一圈圈扩大,最终漫延成一片深邃的梦境。
梦里,她站在灯火辉煌的舞台中央。
追光灯打在她身上,暖得有些灼人。
台下是黑压压的人群,掌声雷动,欢呼声模糊不清。
她穿着洁白的舞裙,身姿轻盈,脸上带着完美的谢幕微笑,目光习惯性地投向观众席前排——那两个本该属于她父母的位置,却空无一人。
梦境瞬间切换。
她看到幼儿园小小的自己,穿着粉色的蓬蓬裙,在简陋的舞台上笨拙地转着圈,台下小朋友的家长笑得前仰后合,她的目光却越过人群,焦急地寻找着熟悉的身影,最终只捕捉到门口匆匆离去的衣角。
小学文艺汇演谢幕时,她捧着优秀表演的奖状,对着台下微笑,即使知道父母不会出现在观众席上。
初中绘画比赛领奖台上,她接过奖杯,闪光灯亮起,她下意识地看向台下,依旧只有陌生的面孔和善意的掌声。
舞蹈表演结束后,汗水浸湿了额发,她站在后台出口,看着其他同学扑进父母怀里,自己则安静地等着,直到最后被老师送回家。
每一次的荣耀时刻,都伴随着一种隐秘的失落。
那些奖状和奖杯,最终都被父母小心翼翼地收进了书柜最上层那个鼓鼓囊囊的文件夹里。
“小九真棒,不过要记得作业写完哦。”记忆中,父母总是这样说着,语气温和,带着不容置疑的关切。那个文件夹,像一个精致的坟墓,埋葬着她童年和少女时代无数个闪闪发光的瞬间,很少被翻开。
苏心然兴奋挥手的身影在梦中再次浮现,林九九猛地从混沌中惊醒,心脏在黑暗中剧烈地跳动。
她意识到,白天苏心然那热情的挥手,竟是这三年来,第一次有人为她的才艺向她表达如此直白的期待和喜悦——而讽刺的是,对方甚至可能根本不知道她具体有什么才艺。
高中三年,画笔尘封在储物盒最底层,上面压着一摞摞沉甸甸的复习资料;心爱的舞鞋被束之高阁,鞋尖上积了一层薄灰,像被遗忘的时光;就连曾经随口就能哼唱的歌也很少再唱,偶尔在洗澡时哼几句,也会被自己陌生的声音惊到——什么时候开始,连表达喜悦和悲伤的本能都变得如此生疏?那些流淌在血液里的旋律和节奏,仿佛被厚厚的尘埃覆盖了。
“等高考完再说。”父母总是这样安慰她,语气里是笃信不疑的规划和对未来的稳妥考量。她也总是乖巧地点头,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玩偶,将那些“不务正业”的渴望深深压进心底。直到那些曾经熟悉的感觉都渐渐模糊,如同被雨水反复冲刷的水彩画,只剩下淡淡的、几不可辨的痕迹,连同那份纯粹的、为艺术本身而雀跃的心。
那张色彩斑斓的文娱部传单在脑海中再次清晰浮现。
她想起了书柜里那些被小心收藏的奖状——市少儿绘画比赛二等奖,校园艺术节表演奖,舞蹈竞赛优秀奖……一张张,一页页,如同褪色的老照片,记录着她曾经的热忱和微光,却又像一个个被强行画上的、未完成的句号,带着无声的遗憾。
记忆的闸门被彻底冲开。
小学五年级那次,她的水彩画《游乐园》色彩奔放,充满了孩童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被班主任极力推荐参加市里比赛。老师特意打电话给妈妈,语气激动:“九九妈妈,九九这幅画真的很有灵气,色彩运用大胆,构图成熟得不像这个年纪的孩子!很有培养前途!”
比赛当天,妈妈把她送到少年宫门口,身上还穿着来不及换下的白大褂,消毒水的味道似乎还萦绕在鼻尖。
“小九乖,妈妈医院还有台手术,不能陪你了。比完赛记得打电话,爸爸来接你。”
妈妈的声音带着疲惫,匆匆摸了摸她的头便转身离去。
那天,她捧回了一个沉甸甸的水晶奖杯,独自坐在空荡荡的等候区冰冷的塑料椅上,等了整整两个小时。
人来人往,喧嚣散去,只有她怀抱着冰冷的奖杯。
爸爸终于来了,在车上,他翻看着奖杯,笑着夸了她一路:
“我们家小九真厉害!画得真好!”
然而,车子驶入小区前,爸爸最后补了一句,像一句轻描淡写的判词:
“不过画画呢,就当个爱好就好,陶冶情操。咱们家小九以后是要考重点大学的,那才是正经出路。”
初二那年,音乐老师发现了她清澈干净的音色和良好的音准,课后特意留下她:“九九,你的声音条件很好,音准特别棒,音色也很干净透亮。如果愿意接受系统一点的声乐训练,说不定……”
她怀着小小的雀跃回家,刚开口提了老师的建议,爸爸便温和地摸了摸她的头,语气带着不容商量的关切:
“小九唱歌真好听,爸爸也爱听。不过呢,咱们还是先把数学成绩提上去,好不好?你最近数学有点退步了,这才是关键。”
高二那年,班主任拿着校园舞蹈大赛的报名表找到她:“林九九,我记得你初中在市里舞蹈比赛拿过奖吧?这次大赛规格挺高的,获奖还能加综合素质分,对升学也有帮助,要不要试试?”
她看着那张色彩鲜艳的报名表,心动了很久,手指在上面摩挲了许久。
最终,那份渴望还是败给了“正途”的压力和那句深入骨髓的“等高考结束吧”。
她把报名表夹进了厚重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里,仿佛夹住了一只扑腾着翅膀想要飞出的蝴蝶。
后来,那张承载过短暂幻想的纸片,和无数张写满公式的草稿纸一起,被当作废纸卖掉了,无声无息。
林九九无意识地摩挲着盖在身上的薄被边缘,粗糙的触感让她指尖微颤。
这触感,奇异地与记忆中第一次握住画笔时,木杆的温润与油彩的粘腻混合的感觉重叠;又像是舞蹈服腰间那圈精致蕾丝花边,轻轻蹭过皮肤时的微痒。
她从来不怪父母。真的。他们只是像千千万万普通的父母一样,怀揣着最朴素的愿望:希望女儿走一条更稳妥、更“有用”的路。那些被搁置的画具,那些错过的比赛,那些无人喝彩的演出……她都能理解。她知道父母是爱她的,只是他们的爱里,总是裹挟着对未来的忧虑,像一层无形的茧,将她那些“无用”却璀璨的梦想温柔地束缚。
只是,在那些独自一人的寂静时刻,当她在自己房间对着镜子,无声地练习着记忆中的舞蹈动作时,总会忍不住去想:如果当时有人,哪怕只是轻轻推她一把呢?如果那次舞蹈比赛她勇敢地站上去了,如果那幅画能继续画下去,如果那首歌能坚持唱完……现在的自己,会是什么样子?会不会更快乐?更鲜活?
三年高中,她以为自己早已习惯了做一个“淡淡的”优等生,将所有的色彩都调成了灰白,将所有的热情都封存于名为“高考”的匣子里。
直到现在,站在大学这片崭新的、充满无限可能的土地上,看着苏心然那双盛满纯粹期待和热情的眼睛,她才猛然惊觉:那个被自己刻意遗忘、深埋心底的、热爱用色彩和肢体表达世界的女孩,她从未真正消失。
白天艺术学院的教学楼里,隐约飘来的断续钢琴声,像一根无形的线,牵动着她的心弦。几个学姐背着画板、提着颜料箱从她身边经过,空气中弥漫开松节油和丙烯颜料特有的、有些刺鼻却又无比熟悉的气味——那一瞬间,她的鼻子猛地一酸,眼眶毫无预兆地发热。
那是她曾经最熟悉、最迷恋的气味,是梦想最初的味道。
她轻轻掀开被子,赤脚走到窗边。夜风带着初秋特有的微凉,拂过她温热的脸颊,带来一丝清醒。她抬起头,望向深邃的夜空。漫天星辰璀璨,如同无数细碎的钻石洒落在墨蓝的天鹅绒上。
她忽然清晰地记起,小时候画过的一幅画:画中的自己穿着闪亮的舞裙,在巨大的舞台上忘情旋转,台下座无虚席,观众们的脸上洋溢着赞叹的笑容。
而现在,仰望着这片无垠的星海,一个念头无比清晰地在她心中升起,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与释然:那个最重要的观众,从来都不在台下熙攘的人群里。那个最该为自己鼓掌、为自己喝彩的人,一直就应该是她自己。
星辉温柔地洒落,仿佛为她披上了一层无声的、却无比璀璨的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