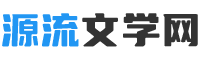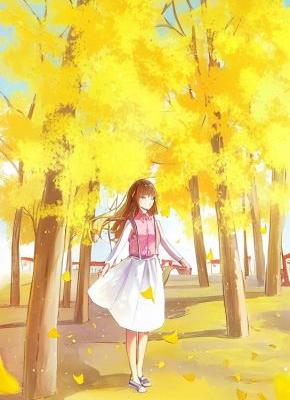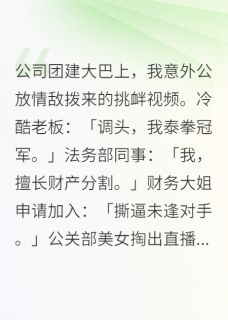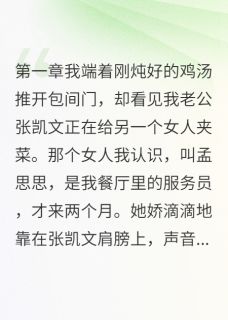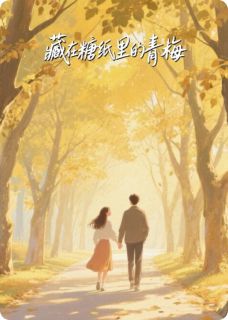
第一章咸涩的海与青石板的河我对F市的记忆,总裹着一层咸湿的海风。
1995年的夏天,我在妇幼保健院的啼哭里第一次呼吸到那股味道,后来才知道,
那是混杂着鱼腥味与码头喧嚣的独特气息。父亲温州民是远洋货轮的轮机长,
母亲杨茗在纺织厂上班,他们的结合像海与岸的相遇,热烈过后只剩无休止的潮涨潮落。
五岁那年深秋,母亲收拾行李时,我正蹲在门槛上数蚂蚁。她的樟木箱锁扣发出咔嗒声,
像敲碎了什么东西。“阿筝,以后跟爸爸过。”她蹲下来摸我的脸,手心有纺织机油的味道,
“要照顾好妹妹。”温琳那时才三岁,扎着两个软乎乎的羊角辫,正抱着我的腿啃。
我把她的脸推开,看见母亲眼里的红血丝,突然就懂了——有些离开,就像退潮的海水,
不会再回来。父亲抱着我和温琳登上开往S市的长途汽车时,
我攥着母亲留下的碎花手帕。舅婆家在老城区深处,青石板路被雨水泡得发乌,
墙根爬满青苔。舅公早逝,舅婆带着两个儿子过活,我们的到来像扔进死水潭的石子。
“丫头片子就是要干活。”舅婆的烟袋锅敲着桌沿,火星溅在我手背上。从那天起,
我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抱着比我还高的木盆去河边洗衣。青石板台阶湿滑,河水是墨绿的,
深不见底,偶尔有死鱼浮上来,肚皮翻白。“姐,我帮你。”温琳的小短腿迈不过门槛,
举着搓衣板要过来。我把她推回去,用石头抵住门:“老实待着,掉下去喂鱼。
”她咧着嘴要哭,我掏出偷偷藏的糖块塞她嘴里——那是父亲临走前给的,我一直省着。
有次河水涨潮,浪头差点把木盆卷走。我死死抓住盆沿,膝盖磕在石头上,渗出血来。
回家时舅婆嫌我洗得慢,抄起竹篾就抽在背上。我咬着牙没哭,夜里给温琳盖被子时,
才摸着背上的红痕掉眼泪。她睡得很沉,小脸红扑扑的,嘴角还沾着糖渣。
2001年开春,外婆杜文沅突然出现在巷口。她穿着藏蓝色斜襟布衫,
银簪子在头发里发亮,看见我冻裂的手背时,眼圈一下子红了。她抱起温琳,“跟外婆走。
”她拉起我就走。坐上去Y市的火车时,外婆给我们煮了鸡蛋。我把蛋黄剥给温琳,
自己啃着蛋白,窗外的风景从灰扑扑的老巷变成绿油油的田野。“到了Y市,
外婆送你们上学。”她摩挲着我的头发,“以后不用再去河边了。”Y市的阳光是暖的,
带着梧桐叶的清香。外婆家在机床厂家属院,两层红砖小楼,院里有棵两人合抱的梧桐树,
枝桠能伸到二楼窗台。“这树比你妈岁数都大。”外婆指着树干上的刻痕,
“以后就住这儿。”我和温琳睡里屋的小床,睡前她总缠着我讲故事。我就编些河边的谎话,
说水里有会唱歌的鱼,其实心里怕得要命。开学前一天,外婆给我们剪头发,
温琳哭得惊天动地,我攥着新做的蓝布书包,手心全是汗。实验小学的校门漆着红漆,
一年级(2)班的教室里,阳光在课桌上跳来跳去。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同桌是个扎羊角辫的女生,叫张和曦。她偷偷塞给我一颗话梅糖:“你就是杜奶奶的外孙女?
”“嗯,我叫温筝。”“我知道,李柊烨奶奶跟你外婆是好朋友!”她朝前排努努嘴,“喏,
那个就是李柊烨。”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心脏突然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男孩坐得笔直,阳光落在他柔软的黑发上,镀着一层金边。他正在看算术本,
侧脸线条干净得像用笔画出来的,睫毛很长,垂下来时在眼睑投下一小片阴影。
他忽然抬起头,目光直直地撞进我眼里——那是双很亮的眼睛,
像Y市春天里融化的溪水,清凌凌的。我慌忙低下头,耳朵烧得厉害,
手心里的话梅糖都快攥化了。放学时,外婆牵着我,杨奶奶牵着他,在梧桐树下碰了面。
“这是阿筝,这是柊烨。”外婆笑得眼角堆起皱纹。他朝我鞠了一躬,
声音温温的:“温筝妹妹好。”“李柊烨哥哥好。”我蚊子似的应了一声,手指绞着衣角。
那天的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我和他并排走在梧桐树下,踩着满地碎金似的阳光。
他的书包带是深蓝色的,比我的新。“你以前没上过学?”他突然问。“嗯。
”“我教你认字吧。”他停下脚步,转身看着我,眼睛弯成月牙,“我认识好多字。
”梧桐树的叶子沙沙响,像在笑我们。我看着他认真的样子,突然就不害怕了,
重重地点了点头。第二章糖纸里的月光李柊烨真的像他说的那样,每天教我认字。
他的铅笔盒是铁皮的,印着孙悟空,打开时总发出咔嗒声。我写字歪歪扭扭,
他就握着我的手,一笔一划地教:“横要平,竖要直,就像做人一样。”他的手心暖暖的,
碰到我手背时,我总忍不住想抽回手。张和曦在旁边起哄:“李柊烨,你是不是喜欢温筝啊?
”他的耳朵一下子红了,却梗着脖子说:“我是她哥哥。
”我们很快就成了院里的“四人组”。除了我和李柊烨,还有张和曦,以及她的邻居冯晟杰。
冯晟杰是个皮猴,总爱爬树掏鸟窝,每次都把张和曦吓得尖叫。三年级那个夏天,
蝉鸣吵得人睡不着。我们四个蹲在梧桐树下玩弹珠,冯晟杰突然拍大腿:“我们玩过家家吧!
”他从兜里掏出块红绸布,是他姐姐的头花,“温筝当新娘,李柊烨当新郎!
”我的脸“腾”地红了,抓起弹珠就要走。“玩嘛玩嘛!”张和曦拉住我,
把红绸布往我头上一盖,“你看你今天穿的红裙子,多配!”那是外婆用旧被面改的裙子,
洗得发白了。我低头绞着裙摆,看见李柊烨站在那里,耳根红得像熟透的樱桃。
冯晟杰把两根柳条塞进我们手里,宣布:“拜堂开始!”梧桐叶在头顶轻轻晃,阳光漏下来,
在他脸上晃成碎金。我们对着树影鞠躬,他的皮鞋尖差点碰到我的布鞋。
冯晟杰喊“夫妻对拜”时,他突然凑近我,热气吹在我耳边:“长大后,我一定娶你。
”我的心像被投进石子的井,咕咚一声,漾起圈圈涟漪。我猛地抬头,撞进他清亮的眼睛里,
那里映着我的影子,小小的,穿着红裙子。“你说啥?”张和曦跑过来,
冯晟杰也伸长了脖子。他慌忙后退一步,背着手说:“没什么!”我攥着柳条的手微微发抖,
红绸布从头上滑下来,落在脚边。从那以后,李柊烨总爱给我带糖。
他的铁盒放在书包最里层,杨奶奶说那是他的“宝贝盒”。每次他都变戏法似的掏出两颗糖,
橘子味的给我,苹果味的留给自己。“为什么不给我苹果味的?”我噘着嘴问。
“因为橘子味的更甜。”他把糖纸剥开,塞到我手里,自己却含着苹果味的糖,
腮帮子鼓鼓的。我舍不得吃糖,把糖纸一张张抚平,放进外婆给的铁皮盒里。
那盒子原本装饼干,现在成了我的宝贝,藏在床底下。温琳总好奇地问:“姐,
你那盒子里装的啥?”我就把她推开:“小孩子别问。”有天夜里,我趁她睡熟,
偷偷打开铁盒。月光从窗棂钻进来,照在五颜六色的糖纸上,像撒了把星星。
橘子味的糖纸是橙黄色的,印着小橘子图案;苹果味的是红色的,画着胖乎乎的苹果。
我一张一张地数,数到第十七张时,听见温琳翻了个身,赶紧把盒子藏回床底。
李柊烨的铁盒我只见过一次。那天去他家写作业,他的盒子敞着放在桌上,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糖,橘子味和苹果味的各占一半。杨奶奶端来桂花糕时,
他慌忙把盒子合上,脸颊红扑扑的。“这孩子,藏什么呢?”杨奶奶笑着打趣,
“是不是给阿筝留的糖?”他没说话,只是往我手里塞了块桂花糕,甜得粘舌头。
四年级的秋天,我得了肺炎,躺在床上发烧。迷迷糊糊中,总觉得有人在摸我的额头。
睁开眼时,看见李柊烨坐在床边,手里攥着颗橘子糖。“我听奶奶说,吃糖病好得快。
”他把糖剥开,小心翼翼地喂到我嘴边。橘子味在舌尖散开,甜丝丝的。温琳趴在床尾,
睡得口水都流出来了。“你怎么来了?”我的声音哑得像砂纸。“我跟老师请假了。
”他从书包里掏出作业本,“我把今天的课记下来了,等你好了教你。
”窗外的梧桐叶被风吹得哗哗响,他的声音温温的,像初秋的阳光。我含着糖,突然觉得,
生病好像也不是那么难受。五年级上学期,学校组织秋游。我们要去郊外的植物园,
李柊烨特意买了两串糖葫芦,用玻璃纸包着。他把大的那串给我,小的留给自己。“小心点,
别粘到衣服上。”他跟在我后面,像个小尾巴。张和曦跑过来抢我的糖葫芦,
李柊烨一把拦住她:“这是给温筝的!”张和曦撇撇嘴:“小气鬼。
”我把糖葫芦举到她嘴边:“你吃一口。”她咬了一大口,酸得直皱眉,逗得我们都笑了。
那天的阳光特别好,透过树叶洒在地上,像铺了层金子。我们坐在草地上吃午饭,
李柊烨把他的鸡蛋给我:“我不爱吃蛋黄。”我知道他骗人,他每次都把蛋黄留给我。
温琳在旁边追蝴蝶,小辫子飞起来,像只快乐的小蜻蜓。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过下去。
早上一起上学,傍晚一起在梧桐树下写作业,他教我做算术,我听他讲课本里的故事。
杨奶奶会喊我们吃晚饭,外婆会留着烤红薯等我们。直到那个周五下午,我推开家门,
看见父亲坐在沙发上。他黑了些,胖了些,穿着崭新的夹克衫,看见我就站起来:“阿筝,
琳琳,收拾东西,跟爸爸回家。
”第三章未说出口的再见父亲说他调到C市的港务局工作了,房子也安顿好了,
以后我们就能安稳过日子。温琳抱着父亲的脖子,笑得咯咯响,她早就不记得在舅婆家的苦,
只知道爸爸回来了。我却像被冻住了,站在原地动弹不得。“什么时候走?
”我的声音抖得厉害。“明天一早的火车。”父亲摸着我的头,掌心粗糙却温暖,
“我知道你舍不得外婆,放假就来看她。”外婆在厨房抹眼泪,锅铲碰着锅沿,
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我回到房间,温琳正兴奋地收拾她的画具——她那时已经喜欢画画,
作业本上全是小人儿。“姐,我们真的能天天跟爸爸在一起了?”“嗯。”我蹲下来,
摸着她的头发,心里像被掏空了一块。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从窗棂照进来,
落在床底下的铁盒上。我悄悄爬起来,打开盒子,糖纸在月光下泛着微光。十七张,
不多不少,都是李柊烨给的。我想去找他,想跟他说我要走了,想问他会不会想我。
可院里的灯都灭了,梧桐树下黑漆漆的,只有蝉鸣在空荡荡的夜里响。我摸着冰冷的铁门,
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凌晨四点,父亲就叫我们起床。温琳还在睡,被父亲轻轻抱起来,
小脑袋靠在他肩上。我背着书包,手里紧紧攥着那个铁盒,
走之前回头看了一眼外婆家的小楼。梧桐树的影子在月光里沉默着,像个巨大的叹息。
火车启动时,我扒着窗户往外看。Y市的轮廓渐渐模糊,
最后连那片熟悉的梧桐绿都看不见了。温琳醒了,揉着眼睛问:“姐,
我们还能见到李柊烨哥哥吗?”我的喉咙像被堵住了,说不出话,只能把她搂在怀里。
铁盒在口袋里硌着心口,疼得厉害。那些没说出口的再见,那些藏在糖纸里的秘密,
都被我带离了那棵梧桐树。C市的冬天来得早,风里带着煤烟味。父亲的房子在老城区,
一楼带个小院子,他在院里种了月季。温琳很快就适应了新学校,她的画在班里得了奖,
贴在墙上,像朵小小的太阳花。我却总是想起Y市。上课时会走神,听见窗外的风声,
就以为是梧桐叶在响;吃到橘子味的糖,眼泪就忍不住在眼眶里打转;做算术题时,
总觉得旁边少了个温温和和教我的人。父亲看我闷闷不乐,就每天晚上陪我做题。
他的手指关节粗大,握笔时总发抖,却还是一笔一划地教我:“别怕,爸爸陪你。
”我看着他鬓角的白发,突然就懂了,我不能再陷在过去里,我要好好读书,要让爸爸放心。
我开始拼命学习,把所有的思念都藏进课本里。早上第一个到教室,晚上最后一个离开。
我的成绩从班级中游,慢慢爬到年级前列。老师说我是“最刻苦的学生”,
同学们说我“冷冰冰的”,只有温琳知道,我枕头底下压着一张梧桐叶,
是离开Y市那天偷偷摘的。初一下学期的那年暑假,外婆来C市看我们。
她带来了杨奶奶做的桂花糕,还有一个布包。“这是柊烨让我带给你的。”外婆打开布包,
里面是个熟悉的铁皮盒——是李柊烨的宝贝盒。我抱着盒子冲进房间,反锁上门。打开一看,
里面整整齐齐码着橘子味和苹果味的糖,还有一张纸条,字迹清秀:“温筝,我等你回来。
”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砸在糖纸上。原来他一直记得我喜欢橘子味,原来他也在等我。
我把那些糖倒出来,数了数,正好三十五颗,是我们分开的月数。我开始给外婆写信,
每次都问起李柊烨。外婆说他还是第一名,说他在作文里写“我的好朋友去了远方”,
说杨奶奶总念叨我。我把这些话翻来覆去地看,像在嚼一块慢慢融化的糖。中考那年,
我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上C市最好的高中。开学那天,父亲送我去学校,
校门口的香樟树郁郁葱葱,像Y市的梧桐树。报到处,一个扎高马尾的女生撞了我一下,
手里的舞蹈鞋掉在地上。“对不起对不起!”她慌忙捡起来,笑容像向日葵,“我叫周软软,
你呢?”“温筝。”“温筝?好名字!”她拉着我的手,“我在高一(20)班,你呢?
”“我也是。”那天的阳光很暖,周软软叽叽喳喳地跟我说着学校的趣事,
旁边站着个戴眼镜的女生,安安静静地笑。“这是慕楠溪,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
”周软软介绍道。慕楠溪朝我点了点头,眼神很温和。我看着她们明亮的笑脸,突然觉得,
或许新生活真的开始了。第四章重逢在人海高中三年,
我和周软软、慕楠溪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周软软是舞蹈特长生,
练功房的镜子里总映着她旋转的身影;慕楠溪是学霸,
总能在我卡壳时递过一张写满解题步骤的草稿纸;我则成了她们的“后勤部长”,
帮周软软记舞蹈动作,替慕楠溪整理笔记。“温筝,你看那个男生!”周软软趴在栏杆上,
朝篮球场努嘴,“他看你好几次了。”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只看到一群奔跑的身影,
慌忙低下头:“别乱说。”“我没乱说!”她拽着我的胳膊晃,“他是校篮球队队长,
好多女生喜欢他呢!”慕楠溪推了推眼镜:“软软,别吓着温筝。”我知道她们是好意,
可我的心里像被那只铁皮糖盒装满了,再也容不下别人。晚自习时,
我会对着窗外的月光发呆,想象李柊烨是不是也在Y市的同一片月光下刷题。
外婆说他考进了Y市最好的高中,还是第一名,我对着信纸笑了很久,
觉得他就该是这样的。高三那年,时间像上了发条的钟,滴滴答答催得人喘不过气。
周软软的舞蹈服磨破了膝盖,慕楠溪的眼镜度数又涨了,我书桌上的习题集堆成了小山。
我们三个挤在学校附近租的小屋里,周软软练舞回来就给我们煮面条,慕楠溪帮我们划重点,
我负责收拾满地的草稿纸。“等考上大学,我要天天睡懒觉。”周软软趴在床上,
有气无力地说。“我要去看海。”慕楠溪推了推眼镜,“听说C市的海没有F市蓝。
”我看着她们,心里默默想:我要回Y市,看看那棵梧桐树。高考结束那天,
我走出考场,看到父亲举着“温筝必胜”的牌子,温琳抱着画板站在旁边,
画纸上是我们一家人的笑脸。她已经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眉眼像极了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