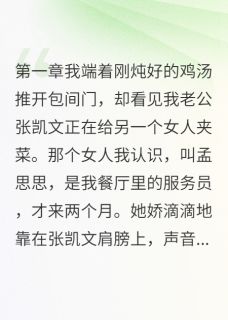1995年,七月的荪田乡像个蒸笼,黏腻的暑气沉甸甸地压在姚小凤的肩头。她躺在床上,
竹席的纹理硌着皮肤,耳边是潘公隔着薄薄一层木板墙传来的咆哮,
粗粝得如同砂纸打磨生锈的铁皮:“猪都比你勤快!懒骨头!
有本事学学城里那些舞厅的**,人家躺着就能吃香喝辣!”最后几个字像淬了毒的针,
狠狠扎进姚小凤的耳膜。她猛地坐起,浑身冰凉,连汗都凝住了。窗纸透进灰白的天光,
映着她脸上未干的泪痕。她受够了,受够了这刻薄如刀的日子,受够了这不见天日的牢笼。
胡乱套上一条洗得发白的碎花裙子,连脸都顾不上擦一把。床头柜上,放着她出嫁前,
嫂子送的一条水红色丝巾,薄如蝉翼,绣着细密的缠枝莲。姚小凤一把抓起,胡乱兜在头上,
遮住红肿的眼和散乱的发,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她赤着脚,推开吱呀作响的房门,
清晨微凉的空气涌进来,带着露水和泥土的气息。她头也不回地冲进了朦胧的曙色里,
朝着镇上唯一的长途汽车站狂奔。镇子刚苏醒,街道空旷。姚小凤跑得气喘吁吁,
心快要跳出喉咙口。车站简陋的雨棚下,稀稀拉拉站着几个等车的乡民,扛着编织袋,
神色木然。她躲在角落里,不敢看人,只焦急地踮脚张望那尘土飞扬的路口。
班车迟迟不见踪影。一辆脏兮兮的白色面包车,“嘎吱”一声,带着刺耳的刹车声,
斜插着停在她面前。车窗摇下,露出一张黝黑油亮的脸,三角眼,
嘴角叼着半截快烧到过滤嘴的烟。是汪老七,镇上出了名的“泥鳅”,专跑黑车,
名声臭得很。“妹子,去哪?”汪老七咧开嘴,露出一口被烟熏得焦黄的牙,
眼神在她裹着丝巾的脸上打了个转,又滑向她单薄的衣衫。“县…县城。
”姚小凤的声音带着哭腔,细若蚊蚋。“哟,巧了!顺路!”汪老七吐掉烟头,热情得过分,
“班车坏半道上了,今儿个等不到!上来吧,马上走,价钱好说!”姚小凤犹豫了。
她认得汪老七,知道他不是好人。可空荡荡的车站,迟迟不来的班车,娘家仿佛远在天边。
婆家那张刻薄的脸在眼前晃动。她心一横,拉开车门钻了进去。
车里的汽油味、汗味、劣质烟草味混合在一起,令人作呕。除了她,还有两个去县城的农妇,
沉默地坐在后面。面包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簸着驶向县城。姚小凤把头抵在冰凉的车窗上,
泪水无声地浸湿了丝巾的一角。她不知道,这辆车正把她拖向一个比潘家更深的泥潭。
县城到了,那两个农妇提着包裹下了车。姚小凤也要起身,
汪老七却“咔哒”一声锁上了车门。“妹子,急啥?”他慢悠悠地点了根新烟,
三角眼闪着算计的光,“去你娘家的班车,下午三点才有呢!这大热天的,等在外头晒脱皮?
走,七哥带你去个地方歇歇脚,喝口水,凉快凉快!就在省城边上,顺道,
下午准点把你送车站!”姚小凤的心猛地一沉:“不…不用了,我就在车站等……”“啧,
跟七哥客气啥!”汪老七不由分说,一脚油门,面包车怪叫着冲出了县城,
朝着省城的方向疾驰而去。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越来越陌生。姚小凤的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缠紧了她的心脏。车子七拐八绕,
最终钻进省城边缘一片迷宫般的城中村。污水横流,私搭乱建的棚屋挤挤挨挨,
空气里弥漫着腐烂的菜叶和劣质煤球的味道。
面包车停在一栋挂着“老七录像厅”破旧灯箱的三层小楼前。汪老七拽着姚小凤的胳膊,
几乎是把她拖了进去。一股浓重的烟味、汗馊味和过期爆米花的甜腻味扑面而来。
一楼昏暗的大厅里,十几排破旧的折叠椅对着一个巨大的彩色电视屏幕,
正放着港片枪战的激烈画面,枪声震耳欲聋。几个头发染得五颜六色的青年窝在椅子里,
眼神空洞。汪老七没停留,拽着姚小凤穿过一条堆满杂物、仅容一人通过的幽暗楼梯,
来到顶楼一个紧闭的房门前。他掏出钥匙打开门,一股混合着霉味和廉价香水的气息涌出。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木板床,一张瘸腿桌子,一个掉了漆的衣柜。
唯一的窗户被厚厚的、脏兮兮的绒布窗帘遮得严严实实。“就在这歇着!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汪老七把她推进去,反手就锁上了门。“开门!放我出去!”姚小凤扑到门上,
拼命拍打、嘶喊。回应她的只有楼下录像厅传来的枪炮轰鸣和男人粗野的哄笑。
绝望像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她。她瘫软在门后,失声痛哭。不知过了多久,
门锁“咔哒”一响。姚小凤惊恐地抬头,汪老七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方便面进来了,
身后还跟着一个五十多岁、穿着艳俗花衬衫、烫着爆炸头的胖女人。
胖女人脸上堆着夸张的笑,厚厚的脂粉也盖不住眼角的皱纹。“哎哟喂,可怜见的!
哭成个泪人儿了!”胖女人扭着腰走过来,一**坐在床边,自来熟地拉起姚小凤冰凉的手,
触感油腻腻的。“我是王姨,这录像厅的老板娘。妹子,快别哭了,跟王姨说说,
谁欺负你了?是不是家里那个老不死的?”姚小凤如同抓住浮木,
抽噎着断断续续诉说了潘家公婆的刻薄和丈夫的冷漠。“杀千刀的!烂心肝的老货!
”王姨拍着大腿,唾沫横飞地咒骂,表情生动得如同在表演,“妹子,你长得这么水灵,
跟朵花儿似的,就该被人捧在手心儿里疼!看看你这手,细皮嫩肉的,哪是干粗活的命?
”她凑近些,压低声音,带着一股浓烈的廉价香水味:“听王姨一句劝,这年头,
笑贫不笑娼!省城这花花世界,有钱的老板海了去了!只要你想开了,
往那‘金色年代’舞厅里一站,扭扭小腰,陪人跳个舞,喝杯酒,那票子啊,
哗哗地往你口袋里钻!穿金戴银,吃香喝辣,不比回那穷山沟里受窝囊气强百倍?
”王姨唾沫横飞地描绘着舞厅的纸醉金迷,汪老七倚在门框上,
三角眼里闪烁着豺狼般贪婪的光,嘴角挂着志在必得的狞笑。“不!我不去!放我走!
”姚小凤猛地甩开王姨的手,像受惊的小鹿般缩到墙角,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她抓起桌上一个空啤酒瓶,“啪”地一声在桌沿敲碎,锋利的玻璃碴直指自己的喉咙,
声音因极度的恐惧和决绝而尖利变调:“再逼我…我就死在这里!
”王姨脸上的假笑瞬间冻结,像一张劣质的面具裂开了缝。她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肥硕的身体撞在瘸腿桌子上,发出难听的吱嘎声。汪老七脸上的狞笑也僵住了,
三角眼里闪过一丝慌乱。他猛地啐了一口:“晦气!”死个值钱货,那可真就鸡飞蛋打了。
“妹子!别!别冲动!”王姨尖着嗓子喊,脸上的粉簌簌往下掉,“放下!快放下!
有话好说!七哥就是吓唬吓唬你!我们哪能真逼你啊!”她一边说着,一边给汪老七使眼色。
汪老七脸色铁青,狠狠瞪了姚小凤一眼,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行!你有种!
给我老实待着!”他“砰”地一声摔上门,落锁的声音格外刺耳。王姨拍着胸口,
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哎哟,吓死我了!妹子你性子也太烈了!行行行,不去就不去,
王姨不逼你。你先歇着,消消气,我去给你弄点正经吃的。”她扭着肥臀,
也慌慌张张地退了出去。房间里只剩下姚小凤粗重的喘息和楼下录像厅隐约传来的枪炮声。
她靠着冰冷的墙壁,慢慢滑坐到地上,破碎的酒瓶还死死抵在颈边,
玻璃的寒气和锐利触感让她稍微清醒。眼泪无声地淌下来,滴在蒙尘的水泥地上,
洇开一小片深色的绝望。日子在恐惧和麻木中一天天捱过。
王姨每天进来送些清汤寡水的饭菜,脸上依旧堆着假笑,
嘴里翻来覆去就是“想开点”、“好日子在后头”。姚小凤像个木头人,不言不语,
只是蜷缩在角落里,眼神空洞地望着那扇永远紧闭的门。汪老七偶尔进来,
用那双黏腻的三角眼上下打量她,目光像冰冷的蛇信子舔过皮肤,留下一阵阵恶寒。
直到一个闷热的傍晚,门又被打开了。这次进来的除了王姨,还有一个矮胖的男人,
穿着紧绷的条纹POLO衫,腆着个啤酒肚,脖子上挂着条粗得晃眼的金链子。他叫吴大郎,
在省城做点建材生意,是汪老七的“老主顾”。吴大郎一进门,
那双被肥肉挤成细缝的小眼睛就黏在了姚小凤身上,肆无忌惮地扫视着,
像在估量一件货物的成色。他摸着下巴,油腻的脸上堆起满意的笑,对汪老七点点头:“嗯,
货色不错,够水灵。就是这眼神…死气沉沉的。”王姨立刻扭着腰上前,
脸上堆满谄媚的笑:“吴老板您放心!刚来,还没开窍呢!养几天,****,
保管让您满意!”她转头对着姚小凤,语气瞬间变得强硬,带着不容置疑的威胁:“小凤!
还不站起来!这位是吴老板,以后就是你的贵人了!跟着吴老板,吃香的喝辣的,
有你享不完的福!别不识抬举!”姚小凤的身体剧烈地颤抖起来,胃里一阵翻江倒海。
她死死咬着下唇,尝到了铁锈般的血腥味。汪老七靠在门边,三角眼冷冷地盯着她,
像在看一只待宰的羔羊。吴大郎不耐烦地挥挥手:“行了,明天晚上,‘金色年代’,
带过去让我瞧瞧。”门再次锁上。姚小凤瘫软在地,指甲深深抠进冰冷的水泥地面,
留下几道惨白的划痕。她看着窗外被窗帘缝隙切割成一条细线的、灰蒙蒙的天空,那点微光,
仿佛是她世界里最后一点活着的证明。第二天傍晚,王姨带着一股廉价的香风进来,
手里拎着一个鼓囊囊的塑料袋。“起来!打扮打扮!吴老板等着呢!”她的语气不容拒绝。
姚小凤被强行拽起来,像一具提线木偶。王姨从袋子里抖出一条廉价的亮片吊带裙,
银色的亮片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刺眼又廉价的光。裙子很短,领口开得很低。
王姨又拿出劣质的粉底和口红,不由分说地往姚小凤脸上涂抹。粉底像刷墙一样糊上去,
掩盖了她苍白的肤色和眼下的青黑,口红涂得过于饱满,像刚吸了血。
当王姨把那件轻飘飘、几乎遮不住什么的亮片裙套在姚小凤身上时,她浑身僵硬,
羞耻感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淹没了头顶。镜子里的人影陌生而妖异,像个待价而沽的商品。
王姨满意地拍手:“瞧瞧!多俊!到了场子里,给我机灵点!把吴老板伺候高兴了,
少不了你的好处!”她拽着浑身僵硬的姚小凤,像拖着一个没有灵魂的包裹,
走出了这个囚禁了她数日的牢笼。下楼,穿过录像厅乌烟瘴气的前厅,
里面几个混混模样的青年吹起了口哨,下流的目光像黏腻的舌头舔舐着姚小凤**的皮肤。
汪老七开着他那辆破面包车,载着她们驶向省城中心最喧嚣的所在,金色年代迪斯科舞厅。
震耳欲聋的鼓点隔着几条街就冲击着耳膜。舞厅巨大的霓虹招牌在夜色中疯狂闪烁,
“金色年代”几个字扭曲变形,散发着一种醉生梦死的蛊惑力。门口停满了摩托车和小汽车,
穿着奇装异服的男男女女进进出出,空气里弥漫着香水、汗水和酒精混合的浓烈气味。
姚小凤被王姨半推半搡地弄进舞厅大门。瞬间,狂暴的音浪像无数只拳头砸在胸口,
让她几乎窒息。旋转的镭射彩灯切割着舞池里疯狂扭动的人群,光怪陆离,人影幢幢。
巨大的低音炮震得脚下的地板都在颤抖。
烟味、酒气、汗臭和各种香水味混杂成一股令人头晕目眩的浊流。
王姨熟门熟路地把她带到角落一个半圆形的卡座。吴大郎已经大马金刀地坐在那里,
面前堆着啤酒瓶和果盘,旁边还坐着两个同样油头粉面的男人。看到姚小凤,
吴大郎眼睛一亮,咧开嘴露出被烟熏黄的牙,拍了拍身边的位置:“来来来!小凤是吧?
坐这儿!”姚小凤像被钉在原地,手脚冰凉。王姨在她后腰狠狠掐了一把,低声威胁:“笑!
给我笑!别给脸不要脸!”剧痛让她一个趔趄,被王姨顺势按在了吴大郎身边。
浓烈的酒气和烟草味熏得她阵阵作呕。“吴老板,您慢慢玩!”王姨谄媚地笑着,
又警告地瞪了姚小凤一眼,扭着腰消失在迷幻的光影和攒动的人头里。
吴大郎油腻的大手立刻揽住了姚小凤僵硬的肩膀,把她往怀里带。“来,小美人儿,
陪吴哥喝一个!”他把一杯浑浊的啤酒硬塞到她手里。姚小凤的手指冰冷,杯子几乎拿不稳。
“别害羞嘛!出来玩,放开点!”旁边一个男人起哄道,
眼神猥琐地在她**的肩膀和大腿上扫视。“就是,吴哥看上你是你的福气!
”另一个也帮腔。吴大郎得意地笑着,那只肥厚的手掌顺着姚小凤光滑的手臂往下滑,
试图去摸她的手。姚小凤猛地一缩手,啤酒泼洒出来,溅湿了吴大郎的裤子。“妈的!
给脸不要脸!”吴大郎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刚才的假笑荡然无存。
他一把攥住姚小凤纤细的手腕,力道大得几乎要捏碎骨头。“装什么清高?
汪老七把你卖给我了!你就是老子花钱买的玩意儿!懂不懂?
”手腕的剧痛和那**裸的羞辱像一把烧红的烙铁烫在心上。
姚小凤的身体抖得像秋风中的落叶,巨大的恐惧几乎将她撕裂。
她看到了吴大郎眼中毫不掩饰的欲望和暴戾,看到了周围那些男人看好戏的、下流的眼神。
舞池中央,领舞台上,一个穿着红色紧身皮裙、身材**的女子正随着激烈的音乐疯狂扭动,
甩动着长发,引来台下阵阵口哨和尖叫。那画面刺痛了姚小凤的眼睛。
“放开我…”她微弱地挣扎,声音淹没在震耳欲聋的音乐里。“放开?”吴大郎狞笑,
另一只手更加放肆地摸向她的大腿,“今晚老子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规矩!
”那只手带着令人作呕的热度和力量,像毒蛇一样贴上了她冰凉的皮肤。
就在那只手即将触及更敏感区域的瞬间,
一股前所未有的、混杂着绝望、愤怒和彻底崩溃的蛮力从姚小凤身体深处爆发出来!
她猛地抓起桌上一个还剩半瓶啤酒的绿色玻璃瓶!“砰!!!
”一声极其刺耳、几乎盖过音乐的爆裂声在卡座响起!
玻璃瓶在吴大郎那颗油光锃亮的脑门上炸开了花!金黄的酒液混合着猩红的血水,
瞬间糊了他满脸!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震耳欲聋的迪斯科音乐还在轰鸣,
镭射灯还在疯狂旋转,但整个卡座区域,以及附近几桌的客人,全都像被施了定身法,
动作和表情都凝固了。无数道目光,惊愕的、好奇的、幸灾乐祸的,齐刷刷地聚焦过来。
吴大郎保持着半张着嘴、眼珠暴凸的姿势,似乎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黏稠的血液混着酒液,顺着他的额头、眉毛、鼻梁蜿蜒而下,流过他惊愕扭曲的脸,
滴落在他名贵的POLO衫上,洇开一片刺目的暗红。“啊!!!”下一秒,
杀猪般的惨嚎才从他喉咙里迸发出来,撕心裂肺。他捂着脸,
肥胖的身体像座肉山般轰然倒向沙发,痛苦地翻滚、咒骂:“臭**!**你妈!
老子弄死你!!”姚小凤手里还死死攥着半截锋利的、沾着血的瓶颈,
玻璃碴在旋转的彩灯下闪着森冷诡异的光。她浑身都在剧烈地颤抖,牙齿咯咯作响,
但那双一直空洞绝望的眼睛里,此刻却燃烧着一种近乎疯狂的火焰,
那是被逼到悬崖尽头、退无可退的孤注一掷!“来人!抓住她!别让这**跑了!
”王姨不知从哪里尖叫着冲了出来,指着姚小凤,声音都变了调。
附近几个汪老七安插在舞厅、穿着花衬衫、流里流气的打手也反应了过来,
凶神恶煞地朝卡座围拢过来。姚小凤像一头被逼入绝境的小兽,
猛地将手里带血的瓶颈朝着扑得最近的一个打手胡乱一划!那人猝不及防,
手臂上被划开一道血口子,痛呼着后退。趁着这瞬间的混乱,姚小凤用尽全身力气,
撞开另一个挡路的混混,赤着脚(她的廉价凉鞋不知何时掉了),
像一道银色的、破碎的闪电,一头扎进了舞池中央那翻滚沸腾的人潮之中!“抓住她!
”“别让她跑了!”王姨尖利的叫声和打手的怒吼在音乐声中显得格外刺耳。
姚小凤在疯狂扭动、汗流浃背的人群中跌跌撞撞地穿行。迷幻的灯光切割着她的视线,
震耳的音乐撞击着她的耳膜,无数晃动的手臂和身体像一道道移动的墙,阻挡着她的去路。
她能感觉到身后那些打手粗暴地推开人群,越来越近的威胁。恐惧攫紧了她的喉咙,
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腥味。她慌不择路,
只想逃离身后那几张狰狞的脸和汪老七、王姨编织的恐怖牢笼。舞池边缘相对空旷些,
那里有一片用红色丝绒绳隔开的区域,灯光也相对柔和,摆着几张宽大的真皮沙发。
那是VIP区,通常只有有头有脸或一掷千金的豪客才能进去。此刻,
一个穿着笔挺藏青色夹克、身形高大的男人正背对着舞池,微微倾身,
和一个西装革履、老板模样的中年人低声交谈着什么。他旁边紧挨着坐着一个年轻女人,
穿着一条价格不菲的宝蓝色连衣裙,化着精致的妆容,卷发优雅地挽起,
正巧笑嫣然地给那个老板倒酒。那侧脸的轮廓,在VIP区相对明亮的灯光下,
竟然与姚小凤有着惊人的相似!姚小凤像溺水的人看到浮木,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朝着那片相对安静的区域冲了过去!她撞开了那象征性的红丝绒绳,
踉跄着扑倒在光洁冰凉的大理石地面上,正好扑在那个穿夹克男人的脚边。
巨大的惯性让她撞翻了旁边一个摆着果盘和酒瓶的小圆几。玻璃器皿碎裂的声音清脆刺耳,
果汁和酒液飞溅,染污了男人锃亮的皮鞋裤脚,
也溅了几滴在那个宝蓝色连衣裙的女人裙摆上。“啊!”女人惊叫一声,
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脸上精致的笑容瞬间被恼怒取代,尖声道:“哪来的疯婆子!
不长眼啊?!”震耳的音乐还在继续,
但VIP区这突如其来的混乱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原本在交谈的夹克男人和老板也停下了话头,皱着眉转头看向脚下。姚小凤挣扎着想爬起来,
破碎的亮片裙狼狈地挂在身上,劣质的妆容被汗水、泪水和刚才的挣扎弄得一塌糊涂,
几缕头发黏在额角。她抬起头,
惊恐绝望的目光正好撞上那个夹克男人俯视下来的、带着明显不悦和疑惑的眼神。时间,
在这一刻,仿佛被彻底冻结了。旋转的彩球灯一道强烈的白光扫过,
清晰地照亮了姚小凤那张惊惶、狼狈、却无比熟悉的脸庞。夹克男人,潘建军,
那双原本带着商场上惯有的精明和此刻被打扰的不悦的眼睛,在看清姚小凤面容的瞬间,
瞳孔骤然收缩!如同被一道高压电流狠狠击中!他脸上的血色“唰”地一下褪得干干净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