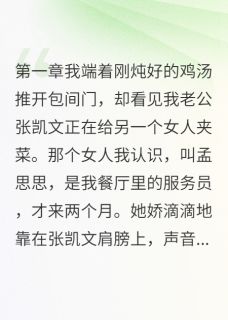暮春的风拂过御花园新绽的芍药,带着暖融的甜香。澄心堂的窗棂半开,阳光斜斜洒入,
在光洁如鉴的墨玉地砖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距离西苑猎场那场惊心动魄的变故,已过去旬日。
楚明昭端坐于宽大的紫檀木书案后,朱笔悬停,
目光落在面前一份关于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出缺的奏议上。玄色常服衬得她面容愈发清冷,
眉间凝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倦意。漕案虽了,余波未平,春狩惊马更像是一记警钟,
提醒着蛰伏的暗影从未远离。轻微的脚步声自身侧响起,带着刻意的放轻。
谢珩捧着一盏新沏的雨前龙井,缓步上前。他今日未着官袍,只一身素雅的月白云纹锦袍,
宽大的袖口随着动作微微摆动,更显身姿颀长。肩胛与肋骨的伤势显然未愈,
行走间动作较平日少了几分行云流水的飘逸,多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凝滞与克制。
御医精心调养的汤药似乎起了作用,他脸上已不见那日的惨白如纸,恢复了些许温润的玉色,
只是唇色依旧偏淡,透着大病初愈的脆弱。阳光透过窗棂,落在他低垂的侧脸上,
勾勒出近乎完美的轮廓。长睫在眼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鼻梁挺直如精心雕琢的玉管,
薄唇微抿,专注地将茶盏轻轻置于楚明昭手边不碍事的位置。动作间,
一缕墨发自他额角滑落,更添几分慵懒的病弱美感。那日浴血护主的疯狂与舔舐伤痕的偏执,
仿佛都被这暖融的春光和素雅的锦袍悄然掩去,
只余下眼前这尊带着微恙却依旧光华内蕴的玉山。“殿下,新茶。
”他的声音也恢复了几分清润,带着恰到好处的恭谨,只是较往日低沉了些许,
如同上好的古琴被轻轻拨动最低沉的弦。楚明昭的目光从奏章上移开,掠过那盏碧色茶汤,
最终落在他脸上。她并未言语,只微微颔首。
视线在他略显苍白的唇色和依旧不能完全舒展的左肩上停留了一瞬,
一丝极淡的、连她自己都未曾深究的波澜掠过眼底。这疯子,倒是恢复得比预想快些。
谢珩并未立刻退下,而是安静地侍立一旁,如同最忠诚的影子。他的目光看似落在虚空,
实则敏锐地捕捉着殿内每一丝气息的流动,以及楚明昭眉宇间细微的变化。他知道,
猎场惊马绝非意外,墨骊臀上那枚淬毒的乌针,如同毒蛇的信子,
指向了深宫与朝堂的某个角落。这份隐忧,如同阴云,笼罩在短暂的平静之上。
殿外传来通禀声,是内阁次辅张阁老求见。张阁老年逾花甲,步履却依旧稳健,
只是眉宇间带着沉重的忧虑。他行礼后,双手奉上一份血迹斑斑、字迹扭曲的帛书,
声音沉痛:“殿下,首辅大人,出大事了!今晨贡院放榜,榜单一出,寒门学子哗然!
落榜者群情激愤,其中一名唤作李慕白的寒门举子,
竟当众……当众撞死在贡院‘为国求贤’的石碑之下!临死前,咬破手指,留下这份**,
控诉今科春闱……有惊天舞弊!”“**”二字,如同惊雷,在安静的澄心堂内炸响!
楚明昭眸光骤然一寒,周身气息瞬间冷冽如冰。她放下朱笔,
接过那卷沾染着暗褐色血迹的帛书。上面的字迹因痛苦和愤怒而扭曲变形,
却字字泣血:“十年寒窗苦,一朝榜无名!朱门酒肉臭,寒士路已穷!座师受贿赂,
考官卖题名!白银十万两,买得金榜登!天理何昭昭,公道在幽冥!我以我血荐,
望君洗冤情!——寒士李慕白绝笔!”“砰!”楚明昭一掌重重拍在紫檀案上,
震得茶盏轻响。她面沉如水,凤眸中寒芒,“好!好一个‘白银十万两,买得金榜登’!
好一个血溅贡院!这是要将本宫与朝廷的脸面,踩在泥地里碾!”科举取士,国之根本,
寒门晋身之阶!若此**控诉为真,不仅是对天下寒窗学子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