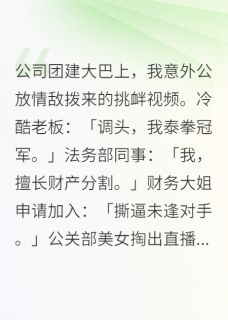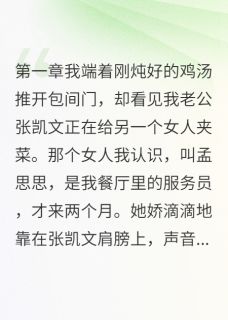1命运错位会议室的水晶灯折射出暖黄的光,落在我摊开的合作协议上。
对面苏氏集团的高管们交换着眼神,语气里满是赞叹:“苏总这版方案真是精妙,
‘晴天’的新媒体资源与我们的线下渠道结合,明年的销售额至少能翻番。
”指尖划过“苏氏”两个鎏金大字,喉间泛起熟悉的暖意。十三年前那个暴雨天,
也是这样的字迹,出现在一张支票上。大**把支票塞进我手里时,
她的校服袖口沾着雨后的草汁,背却挺得笔直,像株迎着晨光舒展的玉兰。
“市一中的重点班,你考上了,我看到了,以后咱们就是校友了。
”她的声音清透得像山涧新泉,没沾半分烟火气。那时我还叫招娣,住在城郊的棚户区。
父亲是附近出了名的赌棍,母亲却总是立不起来,甚至为了给他拿钱,去打三份工,
家里的活儿从早到晚没断过——扫地、做饭、洗衣,我记事起就没闲着。
母亲嘴里总絮絮叨叨:“丫头片子没用”“要是个小子就好了”,听得多了,也就麻木了。
唯一的光亮是课本。趴在灶台边的小板凳上做题时,锅里的玉米糊糊咕嘟冒泡,
蒸汽模糊了字迹,我就用袖子擦一擦,继续算。老师说我是读书的料,劝我考市一中,
说那里的重点班能改变命运。我攥着这句话,熬了无数个夜晚,终于在录取通知书寄来那天,
尝到了一点甜。可那甜很快就被撕碎了。父亲攥着我的录取通知书闯进门,
红着眼把纸团往灶膛里扔:“读什么读!丫头片子认字有屁用,不如嫁给村东头的老光棍,
换点彩礼给我翻本!”那是我熬了无数个夜晚才抓住的指望。我扑过去抢,被他一把推倒,
后脑勺磕在灶台角上,疼得眼冒金星。灶台上的热水壶被撞翻,滚烫的水溅在手腕上,
灼痛感瞬间炸开,我却顾不上,只是死死盯着那团即将被火焰吞噬的纸。
就在我抱着头发抖时,“哐当”一声,破旧的木门被踹开了。大**站在门口,
身后跟着几个高壮的保镖,校服裙沾了灰,头发也乱了,眼神却亮得惊人。
雨丝顺着她的发梢往下滴,混着额角的汗珠,在下巴尖汇成小水珠。她没理跳脚骂人的父亲,
几步冲过来捡起纸团,用指腹轻轻抚平褶皱:“这通知书,谁也不能烧。”“叔叔,
”她的声音比冰棱还冷,“义务教育法规定,不让孩子上学是犯法的。
”身后的律师适时递上文件,“还有,您涉嫌拐卖儿童、堵伯,证据确凿,我已经报案了。
”父亲愣了愣,随即笑出声:“你个小丫头片子唬谁呢?她是我闺女,我卖我自己的人,
犯什么法?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不要胡说八道,不然老子连你一起打”大**没说话,
只是让保镖掀开了里屋的床板。底下藏着的,是父亲这几年偷偷联系买家的书信,
还有他欠赌债的欠条,上面的手印红得刺眼。这些,都是她前几天带着人,
趁父亲出去赌钱时找到的。“拐卖亲生女儿,同样犯法。”律师的声音平静却有分量,
“而且这些欠条的数额,足够判您七年了。”父亲的脸瞬间白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抓着大**的裤脚求饶。母亲在一旁哭哭啼啼,说都是我的错,说我不该惹事。我看着他们,
忽然觉得手腕上的烫伤没那么疼了,心里的某个地方,好像随着他们的丑态,
一点点冷了下去。法庭上父母嘶吼着骂我白眼狼,是大**握住我发抖的手,
在我耳边轻声说:“别怕,以后我护着你。”她的手心很暖,像冬日里的炭火,
驱散了我所有的寒意。判决下来那天,养父因拐卖和堵伯被判七年,养母因包庇罪判了三年。
我站在法院门口,看着囚车呼啸而去,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我哭着对她说:“我没有家了。
”她牵着我的手,眼神坚定:“我就是你的家人,合格的家人。”大**叫苏曼卿,
是苏氏集团的千金。第一次去她家时,我站在别墅门口,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她拉着我跑上二楼,推开一间卧室的门:“以后这就是你的房间了。”房间里有粉色的墙纸,
有大大的落地窗,还有一个摆满了书的书架。书桌上放着一个相框,
里面是她和一对夫妇的合照,笑得眉眼弯弯。“这是我爸妈,”她指着照片,
“他们很和蔼的,你不用怕。”苏伯父和沈阿姨确实很好。沈阿姨总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
说我太瘦了,要多补补;苏伯父会教我下棋,说下棋能让人静下心来。他们从不说我的过去,
也从不让我觉得自己是外人。但我还是有些拘谨。吃饭时总是不敢夹菜,
说话时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大**看出了我的不安,第二天就骑着自行车来接我:“走,
带你去个好地方。”自行车穿过种满梧桐树的街道,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来,落在我们身上,
暖洋洋的。她载着我去了一家冰淇淋店,买了两个最大的甜筒。“吃吧,”她把一个递给我,
“在这里不用客气,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小心翼翼地舔了一口,
甜腻的味道在舌尖蔓延开来,那是我第一次吃冰淇淋。她看着我笑,
眼睛弯成了月牙:“以后想吃,我天天带你来。”车筐里放着本崭新的《牛津词典》,
是她特意给我买的。“以后有不会的单词问我,”她说,“我妈说,知识能让人站得直。
”我确实站得越来越直了。靠着她的资助和奖学金,我从市一中读到了重点大学金融系。
她从不限制我花钱,却总在我想买新款球鞋时敲我额头说:“钱要花在刀刃上。
”她带我去听过苏氏的发布会,也曾拉着我在操场上吃辣条。她说:“真正的底气,
不是家里有多少钱,而是自己能挣多少。”我记住了这句话。大学时,
我利用课余时间做**,发传单、做家教、在餐厅打工,虽然辛苦,但每次拿到工资,
都觉得特别踏实。大**知道了,非但没反对,还帮我介绍了一些翻译的活儿,
说这样既能锻炼能力,又能挣钱。我用那些工资为大**买了一条项链,
虽然比不上他平常戴的,但她还是很喜欢。有一次,我在餐厅打工时,遇到了以前的邻居。
她看着我端盘子的样子,笑着对旁边的人说:“这不是老林家的招娣吗?
听说被有钱人收养了,怎么还在这儿端盘子啊?是不是人家不待见她了?”我心里很不舒服,
却不知道该怎么反驳。这时,大**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接过我手里的盘子:“我让她来体验生活的,怎么了?我苏家的人,想端盘子就端盘子,
想当老板就当老板,轮得到你说三道四?”邻居的脸瞬间红了,讪讪地走了。大**看着我,
皱了皱眉:“怎么不怼回去?”“我……”我低下头,“她说的也是事实。”“什么事实?
”她敲了敲我的脑袋,“你靠自己的双手挣钱,不丢人。那些靠嚼舌根过日子的,才丢人。
”她顿了顿,“以后再有人欺负你,不用忍,有我呢。”大三那年我想创业,做新媒体。
跟她商量时,我心里很忐忑,怕她说我异想天开。没想到她二话不说转来专利奖金,
还把苏氏的供应链总监介绍给我,告诉我:“失败了也没关系,我给你当试用品小白鼠。
”她说到做到。我的“晴天”刚起步时,没什么客户,是她把苏氏的宣传业务交给我做,
还帮我介绍了很多资源。她说:“我相信你的能力,你一定能做好。”有一次,
我们为了一个方案,熬了三个通宵。凌晨五点,看着窗外泛起鱼肚白,我忽然说:“曼卿,
谢谢你。”她打了个哈欠,笑着说:“谢什么?我们是姐妹啊。”“姐妹”两个字,
像一道暖流,瞬间涌遍我的全身。我知道,这两个字,她是认真的。
如今我的“晴天集团”成了新媒体行业的标杆,没人再叫我招娣,都喊我“苏总”。
但只有我知道,每次签合同前,
左手腕那道浅褐色的疤痕总会发烫——那是那天为抢通知书被烫伤的。
大**曾想带我做激光去除,我摇摇头说:“留着吧,提醒我谁把我从火里拉出来的。
”“苏总?”苏氏首席执行官推了推眼镜,“关于联合开发新品牌的事,
您看……”“我觉得可行。”我在协议上签下名字,阳光刚好落在脸上,
“下周让团队对接具体方案。”会议室里响起掌声。大**坐在主位上,
笑着朝我举杯:“早就说过,咱们联手天下无敌。”散会后刚走出旋转门,
就看见苏伯父站在喷泉旁,身边跟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曼卿,星辞,
这位是张总家的公子张明宇,留学回来的高材生。”张明宇伸手想握我的手,
眼神在我身上溜了一圈:“早就听说晴天集团的苏总年轻有为,没想到这么漂亮。
不过女人做生意太辛苦,以后嫁给我,我养你。”我没伸手,
大**已经挽住我的胳膊:“张公子刚回来吧?我和星辞身价数十亿,
这还没算苏氏的财产呢,这该谁养谁还不一定呢。”苏伯父轻咳一声:“曼卿,别胡闹。
明宇是想跟苏氏谈合作,顺便……”“顺便相个亲?”我挑眉,“张公子可能不知道,
我和大**早约好了,这辈子专心搞事业,不结婚。”张明宇脸一僵:“苏总真会开玩笑,
女人最终还是要相夫教子,天天抛头露面的算什么?”大**点开苏氏财报,
“张公子去年在海外亏了三千万吧?我们昨天刚敲定一个亿的合作,您说,
是我们该依附男人,还是某些人该学学怎么赚钱?”张明宇脸色涨成猪肝色。
苏伯父无奈地摆摆手:“你们先忙,我跟他还有事谈。”看着他们走远,
我忍不住笑:“这普信男是从哪个年代穿越来的?”“我爸朋友硬塞的,说什么门当户对。
”大**翻个白眼,“回头让法务部查查他公司的底细,保证他不敢再露面。
”秋日阳光透过梧桐叶隙,在地上织成金色的网。大**忽然停下脚步,
从包里拿出一个档案袋:“给你的,有些事,你也该知道的,我想我欠你一句抱歉。
”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掀开档案袋的瞬间,指尖触到四份亲子鉴定报告。
于99.99%”;第二份的结论像冰碴硌在心上:“排除苏振邦为苏曼卿的生物学父亲”。
第3份和第4份不用看,我大概也能知道是什么——我与沈阿姨的亲权概率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