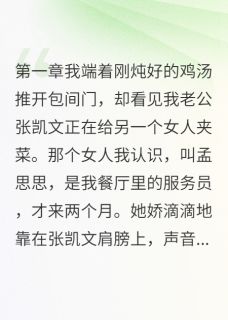暴雨,不是那种诗意的江南烟雨,是城市在倾倒、天空在崩裂般的倾盆。
豆大的雨点砸在苏家别墅光洁的黑铁大门上,砰砰作响,像是无数冰冷的手指在急促地叩击。
雨水顺着精雕细琢的罗马柱疯狂流淌,在门廊昂贵的米白色大理石地面上汇成肮脏的溪流。
林海就站在这片狼藉的中央。他脚边,一个半旧的深蓝色行李箱歪倒在积水中,
泥浆溅满了箱体,也毫不客气地泼洒在他裤管和最后一件勉强算得上整洁的灰色衬衫下摆。
那点灰,在暴雨和泥泞的夹击下,迅速洇开、污浊,像他此刻在这个地方的身份一样,
成了被随意丢弃的垃圾。空气里弥漫着暴雨冲刷泥土的土腥味,
还有别墅深处隐约飘来的昂贵香薰被水汽稀释后的、甜得发腻的余味。
两种气息激烈地冲撞着,如同别墅内外此刻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
别墅厚重的雕花大门敞开着,泄出里面辉煌温暖的金黄色灯光,像一张无声嘲弄的巨口。
门口,站着苏家的人。苏晚,他的前妻,穿着一身剪裁完美的奶油色羊绒连衣裙,
勾勒出养尊处优的曲线。她手里撑着一把巨大的、一看就价值不菲的黑色雨伞,将她自己,
以及她身边精心打扮过的家人,严严实实地笼罩在干燥和体面之中。
雨水顺着伞骨在她脚边砸出一圈细密的水花,却半点沾不到她的鞋尖。她微微抬着下巴,
目光落在林海被雨水打得狼狈不堪的脸上,那眼神里没有一丝一毫的旧情,
只有淬了冰的厌弃和一种终于解脱的快意。她的红唇微微开合,声音不高,却像淬毒的针,
精准地穿透哗啦啦的雨幕,扎进林海的耳膜:“林海,”她顿了顿,
像是在品味这个名字此刻的廉价,“看清楚了吗?这就是你的位置。连苏家的一条看门狗,
都比你干净,比你有用。至少,狗还知道摇尾巴讨口饭吃,你呢?你连当狗的资格,
都没有了。”每一个字,都带着刻骨的寒意。林海的身体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
雨水顺着他紧贴额头的黑发流下,淌过眉骨,滑进眼角,刺得他眼睛生疼,视野有些模糊。
但他没有抬手去擦,只是死死地抿着唇,下颌绷成一道冷硬的线条。
那双曾经温和甚至有些温顺的眼睛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剧烈的痛苦和屈辱中碎裂,
又被雨水冲刷着,一点点沉淀下去,沉入深不见底的冰冷黑暗。他盯着苏晚,或者说,
盯着她身后那片属于苏家的、此刻将他拒之门外的“天堂”。就在这时,
苏晚身边传来一声更加尖锐、更加肆无忌惮的嗤笑。是她妹妹,苏娇。
一个从头到脚都透着被宠坏了的骄纵气息的年轻女人。她穿着当季最新款的亮片小礼服裙,
脚上是闪得刺眼的高跟鞋。她像是看到了什么极其肮脏又极其滑稽的东西,
夸张地捂着嘴笑了两声,然后,她向前一步,高跟鞋尖毫不犹豫地踩了下去。“啪嗒!
”一声轻微又清晰的脆响。她踩中的,是林海行李箱旁边散落出来的一本硬壳册子。
深蓝色的封面,印着烫金的校徽和“毕业纪念”几个字。那是林海大学时代的毕业纪念册,
承载着他曾经以为可以引以为傲的青春、友情和梦想。也是他此刻,除了那几件旧衣服外,
唯一从苏家带出来的、属于自己的东西。泥水瞬间糊脏了那深蓝的封面,
烫金的字迹变得黯淡。苏娇的高跟鞋跟,还恶意地在上面碾了碾,
仿佛在践踏一堆真正的垃圾。“哟,还带着你这堆破烂呢?”苏娇的声音尖利得像划玻璃,
“废物就是废物,连垃圾都当宝贝!赶紧带着你这堆没人要的东西,滚!滚得越远越好,
别脏了我们苏家的地界儿!”她猛地抬脚,将那本就沾满泥泞的纪念册踢飞。
册子在空中划过一个狼狈的弧线,重重摔在台阶下的积水里,溅起更大的泥点。林海的目光,
终于从那片刺目的灯光,移到了那本泡在泥水里的纪念册上。雨水疯狂地冲刷着它的封面,
泥浆模糊了校徽。他看着它,眼神空洞得可怕,
像是灵魂都被这冰冷的雨水和刻毒的言语抽空了。然后,那空洞深处,骤然燃起一点火星,
微弱,却带着焚毁一切的疯狂,只一瞬,又被更深的、冰冷的墨色彻底吞噬、覆盖。
他没有再看苏晚,也没有看苏娇。他弯下腰,动作有些僵硬,却异常稳定。
他伸出同样被雨水泡得发白、指节突出的手,先是抓住了行李箱湿漉漉的拉杆,用力提起。
拉杆上冰冷的金属触感刺入掌心。接着,他趟过浑浊的积水,走到台阶下,俯身,
捡起了那本沉甸甸、湿透了的纪念册。泥水顺着他的指尖滴落。他直起身,
将纪念册紧紧抱在怀里,用胳膊护着,仿佛那是失而复得的稀世珍宝,
又像抱着一块冰冷的墓碑。冰冷的册子隔着湿透的衬衫紧贴着他的胸膛,寒意刺骨。
他拖着行李箱,拉杆发出不堪重负的“嘎吱”声,转过身,一步一步,
艰难地走向别墅大门外那条被暴雨淹没的私家路。身后,苏晚冰冷的声音再次传来,
带着胜利者的宣判:“记住,林海,从今往后,苏家和你,再无瓜葛。你这种垃圾,
就该待在垃圾堆里。”苏娇尖锐的笑声夹杂在雨声中:“滚吧!穷鬼!窝囊废!
”林海的脊背挺得笔直,像一杆被狂风暴雨狠狠抽打却不肯折断的标枪。他没有回头。
每一步踏在积水里,都溅起浑浊的水花。雨水疯狂地抽打在他脸上、身上,模糊了他的视线,
也彻底浇熄了那具躯壳里最后一点名为“林海”的温度。别墅大门在他身后,
带着一种沉重的、象征着彻底隔绝的声响,缓缓合拢。最后一线温暖的光,被无情地切断。
世界,只剩下无边无际的、冰冷的黑暗和喧嚣的暴雨。他抱着那本湿透的纪念册,
拖着唯一的行李箱,走向城市庞大无边的、深不见底的阴影之中。……三年。
时光足以冲刷掉许多痕迹,比如当年那场暴雨带来的狼狈泥泞。但对于另一些东西,
它更像是一块无情的磨刀石,将某些决心磨砺得愈发冰冷锐利。
“世纪新城”项目签约仪式暨市政答谢晚宴,
选在江城最新落成的“云端”国际会议中心顶层。巨大的环形落地玻璃幕墙外,
是璀璨如星河倒悬的城市夜景。宴会厅内,水晶吊灯倾泻下柔和却辉煌的光芒,
空气里浮动着香槟的清冽、高级雪茄的醇厚以及名贵香水的幽雅气息。衣香鬓影,觥筹交错,
每一个动作,每一句低语,都透着属于金字塔尖的从容与距离。今晚,
这里是江城权力与财富最集中的磁场,而磁场的核心,只有一个名字:林海。或者说,
控着“启元资本”、一手主导了震动整个东部沿海的“世纪新城”千亿级项目的——林先生。
他站在靠近落地窗的位置,一身剪裁完美的深黑色定制西装,勾勒出宽肩窄腰的挺拔轮廓。
袖口处,一枚样式极其简约却光华内蕴的铂金袖扣低调地闪烁着。
三年时光洗去了他脸上残余的青涩和温顺,留下的是刀削斧凿般的冷峻线条。眉骨更深,
鼻梁更挺,下颌的线条绷紧如刀锋。那双眼睛,平静地注视着窗外无垠的灯火,
深邃得如同不见底的寒潭,映着城市的流光溢彩,却透不出一丝真正的温度。
周围的空气仿佛都因他的存在而微微凝滞。无论是本地政要,还是商界巨擘,
看向他的目光都充满了毫不掩饰的敬畏、热切与小心翼翼的攀附。但没有人轻易上前打扰。
他身上那股无形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强大气场,像一道透明的屏障。“林先生,
您确认一下明天奠基仪式的流程……”一位穿着干练套裙、气质清冷的年轻女子走到他身侧,
低声说道。她是叶瑾,林海的特别助理,也是他如今最信任的伙伴。她手中拿着平板电脑,
屏幕上显示着复杂的图表。“按既定方案。”林海开口,声音低沉平缓,听不出情绪,
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他的视线甚至没有从窗外收回。“明白。”叶瑾点头,
迅速在平板上记录着什么,动作利落精准。就在这时,
宴会厅入口处传来一阵不易察觉的轻微骚动。林海的目光,
终于从窗外的万家灯火上缓缓移开,落向入口方向。那深邃的眼底,不起一丝波澜,
平静得可怕。苏家的人,来了。
苏晚穿着一身显然是精心挑选过、力图显得优雅又不失奢华的香槟色长裙,但款式和细节,
已经明显落后于今晚真正的顶级名媛。她脸上化了比平时更浓的妆,
试图掩盖眼角的疲惫和眉宇间挥之不去的焦虑。她努力维持着得体的微笑,但那笑容僵硬,
眼神里充满了急切和一种近乎绝望的期待。她的父亲苏建国,
曾经在林海面前颐指气使的岳父,此刻腰背微微佝偻,脸上堆满了近乎谄媚的笑容,
额头冒着细汗。母亲周美娟则紧紧攥着手中的晚宴包,眼神慌乱地四处逡巡,寻找着目标。
苏娇和她那个曾经趾高气扬的丈夫张涛也在其中。
苏娇身上的亮片裙在顶级水晶灯下显得廉价而刺眼,她脸上是毫不掩饰的震惊和贪婪,
死死盯着林海的方向。张涛则显得有些手足无措,眼神躲闪,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曾经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他们就像一群误入顶级盛宴的局促闯入者,
与周围真正的上流人士格格不入。但巨大的诱惑和更巨大的恐惧,驱使他们硬着头皮,
拨开人群,朝着那光芒最盛的核心艰难地移动。周围的低语声更密集了。
不少认出苏家、也知晓当年那场“离婚闹剧”的宾客,
眼中流露出毫不掩饰的玩味、鄙夷和看好戏的神情。苏建国率先挤到了近前。
他脸上那夸张的笑容几乎要咧到耳根,额头的汗珠在灯光下清晰可见。他几乎是半躬着身子,
双手紧张地在身前搓着,声音带着一种刻意拔高的、极不自然的热情:“林…林先生!
哎呀呀,真是…真是好久不见!风采更胜往昔啊!我们苏家…我们苏家一直惦记着您呢!
听说您回来,晚晚她妈高兴得好几天没睡好觉,特意…”他的话戛然而止。因为林海的目光,
终于落在了他的身上。那目光,平静,淡漠,没有一丝温度,像看一件没有生命的摆设。
没有恨意,没有愤怒,甚至没有一丝被打扰的不耐。只是纯粹的、彻底的漠视。
林海甚至没有听完他这番拙劣的套近乎。他微微侧头,对着身旁的叶瑾,声音不高,
却清晰地穿透了周围的低语,
清晰地传入了苏建国以及刚挤过来的苏晚、周美娟等人的耳中:“这里空气不太好。
”他微微蹙了下眉,像是闻到了什么令人不适的气味,“有点脏。”一个“脏”字,
轻飘飘的,却像一记无形的、裹挟着冰碴的重锤,狠狠砸在苏家每个人的脸上。
苏建国脸上的笑容瞬间凝固、碎裂,血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尽,只剩下难堪的死灰。
周美娟身体晃了一下,手里的晚宴包差点掉在地上。苏娇惊愕地张大了嘴,像条离水的鱼。
张涛则猛地低下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周围瞬间安静了一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