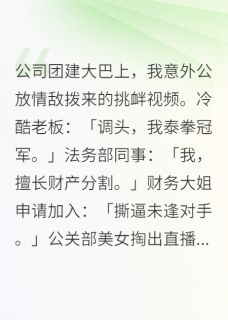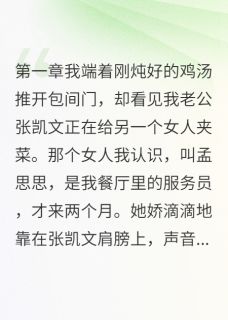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大人,”欧比龙说,“吉德里姆在上,您穿的那是什么?”
“这是一种伪装,亲爱的朋友!”赞德瑞克兴致勃勃地宣布,“我把自己伪装成农民中的一员,这样我到这儿来就不会被打扰了。”
——《孤离》第八章
*********
“停车!例行检查!”一个穿着浆洗得发白、肩章磨损得几乎看不清纹路的军官制服男人,挥舞着手中那根电量不足、光线微弱得如同萤火虫**的信号棒。他的声音带着一种浸透了疲惫和例行公事的懒散,仿佛这句话已经重复了千百遍,早已失去了意义。
他眼看着那辆风尘仆仆、几乎看不出原色、仿佛刚从沙海地狱里爬出来的老旧皮卡,竟异常平稳地停在了路障前。
他不耐烦地朝着旁边那群倚着沙袋、打着哈欠、眼神涣散得如同丢了魂的士兵们打了个响指:“喂!都他妈动起来!磨蹭什么呢?查完这辆就能换岗滚回去睡大觉了!”
然而,士兵们只是懒洋洋地交换了一下眼神,身体像灌了铅一样纹丝不动。
检查这么一辆穷酸得叮当响的破车?
算了吧,榨干它也挤不出半滴油水。这简直是浪费他们宝贵的时间。
军官暗骂一声,肺都快气炸了,于是提高了音量,唾沫星子横飞:“耳朵聋了吗?!这是命令!都给老子爬起来!”他很清楚这个位于德克高利省与邻省交界处的“重要”哨站责任不小——至少在那些糊弄上头的文件报告里是这么写的。
四十来号人,分三班倒守着几条破路,美其名曰“严防不法之徒和感染者流窜入境”。但实际上,他们的目标是那些那些穿梭于两省之间、为富不仁的商队
他们这些“边界守护者”的主要营生,就是从这些“肥羊”身上,替自己、替顶头上司、甚至替远在省会纸醉金迷的“大人们”,薅下足够丰厚的“辛苦费”和“买路钱”。这是心照不宣的规矩,是维系他们这群边缘人生活的潜规则。
至于眼前这辆快散架的皮卡?车斗里塞满了鼓鼓囊囊、散发着廉价肉腥味的肉干、灰扑扑的水囊和磨破边的睡袋,一看就是穷苦人家砸锅卖铁凑出来的远行家当。
检查他们纯粹是浪费时间,连搜刮的兴趣都提不起来。但规矩就是规矩,尤其是对感染者的排查——这可是上面三令五申、不容触碰的“红线”。万一漏掉一个感染者混进去,在哪个富商老爷的地盘上闹出乱子,他们这群小虾米可担待不起。流程,再烦也得走。
“喂!开开车窗,老兄!”一个被军官刀子般目光逼得没办法的年轻士兵,慢吞吞地挪到驾驶室旁,用指关节不情不愿地敲了敲那层积满沙尘、灰蒙蒙几乎不透光的车窗玻璃。
他眯着眼,努力想看清里面的人影,但夜晚的昏暗加上厚厚的污垢,只映出自己模糊而疲惫的倒影。
真他娘的困,我好想睡觉。
“快点儿的!别磨蹭!”他提高音量催促道,语气里充满了被指使干活的不爽和对这辆破车的鄙夷。
真有意思。塞托斯稳稳地坐在驾驶座上,他搓了搓那双原本属于杰佛的毛皮手套,这对于缩小体型的他倒还能穿上——这能有效地避免他的双手沾染上那些污秽。
他能清晰地感知到车外士兵们那几乎凝成实质的怠惰、军官那被烦躁烧灼的神经。
为了更“入乡随俗”地体验这出小小的戏剧,他决定做点微不足道的准备。
他伸手,将原本盖在后座杰佛身上那张厚实、带着汗味和尘土气息的深色粗布扯了过来,随意地披在自己即使缩小后也远比常人高大的金属身躯上。粗布褶皱巧妙地遮掩了绝大部分非人的棱角和金属的反光,只留下一个裹在阴影里、轮廓模糊的“人形”。
同时,他将那张描绘着圣吉列斯悲悯面容、华丽得与这破车格格不入的金色面具,悄无声息地收回了维度口袋。他并非畏惧,只是单纯觉得那些即将喷溅的、成分复杂且气味难闻的有机体液,弄脏面具精美的雕花和沟壑......清理起来会非常不效率。
就在车外那年轻士兵的耐心即将耗尽,手已经摸向腰间的短棍,准备给这不识相的“穷鬼”一点颜色看看的时候——
“咔哒”一声轻响,如同某种精密机关的解锁,驾驶座的车窗终于降下了一道缝隙,随即缓缓滑落到底。
一股混合着陈旧皮革、干燥尘土以及某种难以言喻的、仿佛来自古老墓穴的冰冷气息,瞬间飘散出来。士兵下意识地皱了皱鼻子,后退了小半步,借着哨站那几盏昏黄摇曳、供电不足的灯泡光线,他勉强看清驾驶座上坐着一个披着深色粗布、低着头的高大身影。
那身影仿佛怕冷般蜷缩着,又像是在刻意躲避着光线和视线。
“你们......打哪儿来?要去哪儿?”士兵清了清嗓子,强作镇定地问道,声音里那点不耐烦被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取代了。
“去切尔诺伯格。”一个低沉、平稳得几乎没有起伏,却又带着某种奇异金属质感的声音从粗布下传来。那人影的头似乎埋得更低了,粗布的边缘微微晃动。
士兵的眉头立刻拧成了一个死结。这家伙......居然没叫他“长官”?甚至连个“您”字都没有!这太不合规矩了!简直是对他们这身制服的藐视!
一股被冒犯的恼怒混杂着隐隐的不安,像冰冷的蛇一样爬上他的脊背。他不动声色地朝旁边的同伴使了个眼色。
原本懒散倚靠着的士兵们似乎也嗅到了气氛的异样,眼神锐利了几分,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简陋的钢刀和上了弦的弩,脚步无声地移动,慢慢从两侧围拢上来,隐隐封住了皮卡的退路。
远处,那个军官也停下了走向哨站小屋的脚步,手悄然按在了腰间那把沉重砍刀的刀柄上,眉头紧锁,目光如鹰隼般死死盯住驾驶室。
塞托斯将这一切尽收眼底。这些碳基生命体的群体警戒反应虽然迟钝,但一旦触发,倒也比预想的稍微有那么点协同性?
这是群体本能?还是说他露出了什么破绽?
对于情感并没有过多研究的戴冠将军并不知道引发警戒的,是他那毫无敬意的语言。
“打开后门!我需要检查其他乘客的身体状况!”士兵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口吻,一只手已经牢牢按在了车门把手上,随时准备发力拉开。
塞托斯没有阻止他动作的意图,反而用一种近乎闲聊的、带着一丝古怪探究意味的语气,清晰地问出了那个在乌萨斯哨站堪称禁忌的问题:
“冒昧地问一下......对于感染者,你们通常会怎么处理?”
这句话如同在滚烫的油锅里泼进了一瓢冷水。
“唰啦——!”
围拢的士兵们脸色剧变,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同时举起了手中的武器。冰冷的钢刀反射着昏黄的光,弩箭的箭簇齐刷刷地对准了驾驶室里那个模糊的身影。
在乌萨斯的哨站,问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裸的、近乎自杀式的挑衅!一个正常人怎么会不知道感染者在这里的下场?除非......他就是!或者车上就有!
只有外来的感染者会这样愚昧无知。
塞托斯对那些指向他的、在他眼中脆弱得如同孩童玩具的武器没有任何反应。粗布下的身影甚至连一丝颤抖都没有。他只是用那平稳得可怕的、如同机器读数般的声调,清晰地、一字一顿地重复了一遍:
“对于感染者,你们会怎么处理?”
“怎么处理?!”刚才敲窗的士兵像是被这“明知故问”的愚蠢彻底激怒了,也可能是为了在军官和同伴面前表现自己的“忠诚”和“勇猛”,他踏前一步,咧开嘴,露出一口被劣质烟草熏黄的牙齿,脸上充满了扭曲的恶意和一种面对“贱民”的优越感,声音因为激动而变得尖利:
“当然是像处理垃圾一样!关进滞留区那些臭气熏天的铁笼子里!等凑够一车皮,就把这些瘟神、这些行走的污染源,统统塞进闷罐车,丢到最黑最深、不见天日的矿坑里去!让他们在源石矿脉旁边烂掉!化成灰!这就是感染者的下场!懂了吗?!贱骨头!”
他几乎是吼出来的,唾沫星子飞溅,有几滴甚至落在了摇下的车窗框上。
这真的,真的,很肮脏。
塞托斯沉默了一瞬,记录下了这个充满仇恨和恐惧的答案。然后,一只覆盖着同样粗糙皮革手套的手,从粗布下伸了出来。
这只手的手指间,稳稳地夹着一沓崭新、挺括、散发着诱人油墨清香的钞票——那是湛蓝色的龙门币。即使在昏暗摇曳的光线下,那独特的、象征着财富的颜色,以及上面清晰的、令人心跳加速的大面额数字,瞬间像磁石一样吸住了所有士兵的目光。
贪婪的火焰瞬间在他们眼中点燃,熊熊燃烧,瞬间压过了之前的恶意和警惕。
很好,还是一群贪婪的家伙。
有机体总是贪婪的。
“收好它。”那个低沉的声音说道,平稳地将那沓足以让这些穷苦士兵眼红的钞票,递向那个唾沫横飞的士兵。
士兵整个人都僵住了。
脸上的恶意和扭曲的优越感如同冰雪般消融,被难以置信的狂喜和更加炽热、几乎要烧穿理智的贪婪取代。
这么多龙门币!崭新的!在黑市上能换多少东西足够他离开这个鬼地方,逍遥快活好一阵子了!这破车上果然藏着大鱼!说不定这“怪人”身上还有更多宝贝!
“哈!算**识相!”士兵咧开一个更加夸张、几乎要裂到耳根的笑容,露出满口肮脏的黄牙。
他迫不及待地、像饿狼扑食般伸手就去抓那沓诱人的蓝色财富。“你是做什么大买卖的?嗯?能随手拿出这么多龙门币?”他一边急切地试图将那厚厚的钞票从对方纹丝不动的手指间抽出来,一边贪婪地盘问着,脑中已经开始盘算着拿到钱后的美妙生活。
然而,他猛地一抽!那沓钞票却如同焊在了对方手上,纹丝不动!
士兵愕然,脸上贪婪的笑容凝固了一瞬,随即不信邪地使出吃奶的力气,双手并用,身体后仰,脸都憋成了猪肝色。但那覆盖着皮革的手,如同钢铁浇铸的山峦,任凭他如何用力拉扯,那诱人的蓝色钞票依旧牢牢地嵌在对方指间,连一丝褶皱都没产生。
就在这时,那个低沉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平稳的询问,而是变成了一种充满了戏剧性、带着无尽嘲弄和戏谑的语调,如同在舞台上向所有观众揭露一个惊天秘密:
“这是一种伪装,亲爱的朋友!”声音高声说道,带着一种非人的穿透力和冰冷的金属质感,清晰地回荡在寂静的夜空中。
在士兵错愕到极点、大脑一片空白的目光注视下,在周围所有弩箭和钢刀紧张的对准下,那只抓钱的手——松开了。
崭新的、湛蓝色的龙门币,如同被风吹散的落叶,纷纷扬扬地飘落向肮脏的沙土地面。
与此同时,那只松开钞票的手,闪电般反手扣住了士兵那只还按在车门把手上、因用力而青筋暴起的手腕。
力道之大,让士兵听到了自己腕骨不堪重负的**。
脆弱的有机体。
“呃啊——!”剧痛让士兵下意识地惨叫出声。
但这还没完。
驾驶座上的人影猛地一抬手,将头上披着的深色粗布狠狠扯了下来,随意地甩在一旁。
一张冰冷、光滑、毫无生气、完全由奇异金属构成的骷髅面孔,暴露在昏暗摇曳的灯光下。
没有皮肤,没有血肉,只有闪烁着冰冷、恒定幽绿光芒的光学目镜,如同深不见底的寒潭中燃烧的鬼火,死死地瞪着眼前这个渺小、贪婪、此刻被无与伦比的恐惧彻底攫住、连惨叫都卡在喉咙里的士兵。
“我把自己伪装成农民中的一员,”塞托斯发出刺耳的、如同金属摩擦扭曲般的非人声音,每一个字都浸满了冰冷的嘲讽,“这样我到这儿来就不会被打扰了,但很显然,你们这群嗡嗡叫的苍蝇,打扰了我的宁静。”
他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失去理智的、优秀仁慈的人。
嗯,我的所作所为,倒很像是赞德瑞克会做出来的......他总是那么幽默。只可惜我身边没有一个王卫,不然我简直就是赞德瑞克本人了。
赞德瑞克,你是否醒了呢?
“怪......怪物......老......老天......”士兵脸上的贪婪狂喜彻底僵死,化作一片死灰般的绝望和无法言喻的恐怖。
他的瞳孔放大到极限,几乎占据了整个眼眶,喉咙里只能发出咯咯的、如同破风箱般的怪响,身体因为极度的恐惧而彻底石化、僵硬,连一丝逃跑的力气都消失了。
塞托斯没有给他任何忏悔或求饶的机会。那只覆盖着廉价皮革手套的金属手掌,扼住了士兵脆弱的脖颈。
“咔嚓!”
一声清脆得令人头皮发麻、如同枯枝被踩断的骨骼碎裂声,在死寂的夜晚清晰地响起。
士兵脸上那狂喜、错愕、剧痛和极致恐惧交织的复杂表情,永远凝固在了脸上。他眼中的光芒熄灭了,身体像被抽空了骨头一般,软软地瘫倒下去,砸起一小片尘土。
塞托斯从容不迫地推开车门,动作优雅得如同赴宴的贵族,从那辆破旧的皮卡里跨步走了出来。
他高大、闪烁着冰冷金属光泽的身躯完全暴露在哨站昏黄摇曳的灯光下,幽绿的目光如同探照灯般,缓缓扫过周围那一张张因极度震惊、恐惧和难以置信而彻底扭曲、惨白如纸的脸庞。
那块深色粗布如同落幕的戏服,委顿在他脚边的沙地上。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了哨站。只有风穿过树林的呜咽,和远处不知名虫豸的嘶鸣。
军官的手还按在刀柄上,但他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冻结了,手指僵硬得无法动弹。他看着那个从破车里走出来的金属怪物,看着地上士兵那扭曲的尸体,大脑一片空白。恐惧像冰冷的潮水,淹没了他所有的勇气和算计。
“怪......怪物!开火!开火啊!”军官终于从喉咙深处挤出一声变了调的、如同被掐住脖子的公鸡般的尖叫,打破了死寂。他猛地拔出砍刀,却因为手抖得太厉害,刀差点脱手飞出。
围拢的士兵们如梦初醒,恐惧压倒了理智,他们嘶吼着,颤抖着扣动了扳机,射出了弩箭,挥舞着钢刀,疯狂地扑向那个非人的存在!一时间,弩箭破空声、刀刃挥舞的呼啸、士兵绝望的呐喊响成一片!
他们从未!从未见过这样的非人之物!
塞托斯站在原地,甚至没有移动脚步。他的骷髅面孔上看不出任何表情,只有那对幽绿的光学目镜捕捉着每一个扑来的身影,计算着每一条攻击轨迹。
他放缓了自己的时间感知,仔细品味着每一个人的恐惧和慌张。
多么有趣啊。
真正的戏剧才刚刚拉开序幕。幽绿的光芒在混乱的刀光箭影中,稳定地闪烁着。
“取悦我吧!”征服者欣喜地宣告着。
他像人类一样弯曲着自己的嘴,像人类一样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