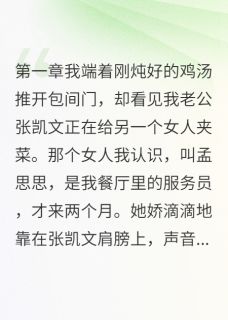永和十二年冬,北疆朔风卷着细雪扑打在青石城墙上。
七岁的姜云昭踮脚趴在将军府最高的阁楼窗边,鼻尖冻得通红,却不肯挪开盯着城门的眼睛。
“姑娘快下来,要是让将军知道您又爬窗,一定不会饶了老奴的!
”乳母张嬷嬷在底下急得直搓手。“爹爹今日巡营归来,说好给我带白狐皮的!
”小女孩声音清亮如檐下风铃,两条用红绳扎起的小辫在风中晃动。她突然眼睛一亮,
“来了!”府门处传来马蹄声,姜云昭像只灵巧的猫儿从窗棂翻下,提着棉裙就往楼下冲。
刚跑到庭院,却见父亲姜震霆身后还跟着辆青布马车。“昭昭,这是程家公子。
”姜震霆将女儿抱起,指着从马车里钻出来的小男孩。“他父亲是南边来的丝绸商人,
要在咱们这儿住段时日。”那男孩裹着月白色狐裘,像团雪球似的从车上滚下来。抬头时,
姜云昭看见双清凌灵的眼睛,像是把天山雪都盛在了里头。“我叫程砚舟。
”他规规矩矩行礼,声音比城里的教书先生还斯文。姜云昭从父亲怀里挣下来,
沾着泥雪的鹿皮靴"啪"地踩在程砚舟跟前:“我是姜云昭,以后我罩着你!
”说着就把自己腰间的小木剑塞进他手里。五年光阴如门前溪水流过。
十二岁的姜云昭蹲在程家商行后院的老梅树上,嘴里叼着根草茎,
看底下少年捧着账本愁眉苦脸。“喂,书呆子!说好今天去听周先生说书的!
”程砚舟额间还沾着墨迹,闻言抬头。阳光透过梅枝在他脸上投下细碎光斑,
衬得那对眉眼愈发温润。他无奈地合上账册:“昨日南边来的货船出了差错,
爹爹要我......”话未说完,姜云昭已经猴子似的荡下树枝,拽起他就跑:“管他呢!
周先生半月才来一次!”两个孩子穿过熙攘的街市。姜云昭跑在前头,
石榴红的裙裾扫过青石板,像簇跳动的火苗。程砚舟被她拽着衣袖,腰间玉佩叮当作响。
路过糖画摊子时,他悄悄摸出铜板,换来只蝴蝶形状的糖画。“给你的。”他气息还不稳,
耳尖却先红了。“上次你说蝴蝶比凤凰好看。”姜云昭眼睛弯成月牙,正要接过,
突然街角窜出条恶犬。那畜生足有半人高,獠牙上还挂着血丝,直扑姜云昭而来。
电光火石间,程砚舟猛地将她推到身后。恶犬的利齿"嗤"地撕开他后背衣衫,
鲜血顿时浸透长衫。“砚舟!”姜云昭的尖叫惊动了整条街。程家厢房里飘着苦涩药香。
姜云昭趴在程砚舟榻边,眼睛肿得像核桃。程砚舟后背缠着厚厚纱布,
却还笑着安慰她:“不过皮肉伤,过几日就好。”“你傻呀!”姜云昭抹着眼泪。
窗外暮色渐沉,程砚舟忽然望向窗外:“你看,北斗七星出来了。”他声音轻得像片羽毛。
“我娘说过,对着星星许愿最灵验,我刚才许愿,希望云昭永远平安喜乐。
”姜云昭鼻子一酸,抓过程砚舟的手紧紧握住:“那我也许愿,要永远和砚舟在一起!
”月光漫过窗棂,将两个孩子交握的手映在墙上,像株并蒂莲的影子。永和二十年春,
朝廷急令调姜震霆镇守北疆。消息传来时,姜云昭正在程家后院练剑。听到父亲召唤,
她手中木剑"当啷"落地。“三日后启程?”她声音发颤,
“那砚舟......”姜震霆沉默片刻,终究硬起心肠:“程家商路在南边,
你们......”话未说完,姜云昭已经冲出门去。
她在城郊枫林找到正在核对货单的程砚舟。少年听罢消息,手中毛笔"啪"地折断,
墨汁溅了满袖。当夜暴雨倾盆。姜云昭在闺房收拾行装,忽听窗棂轻响。推开窗,
程砚舟浑身湿透站在雨里,掌心躺着枚羊脂玉佩。“我请匠人赶制的。”他声音沙哑。
“你带半块,我留半块。上面刻着我们的名字。”玉佩在闪电中泛着温润的光。
姜云昭突然翻出窗台,扑进程砚舟怀里。雨水混着泪水滚落,她咬着他肩头呜咽:“三年,
最多三年,我一定回来!”程砚舟抚着她湿透的长发,在雷声中一字一顿:“我等你,
哪怕十年,二十年。”北疆的风沙磨糙了姜云昭的皮肤,却让她的剑术愈发凌厉。每月初一,
总有商队带来盖着程家印鉴的信笺。她将那些信贴身收着,在营帐烛火下反复品读。
域语言......”“砚舟接手了三支商队......”“砚舟......”在江南,
程砚舟的书房抽屉里锁着厚厚一叠回信。每封开头都是力透纸背的“砚舟亲启”,
结尾处总画着柄小剑——那是他们儿时的暗号。三年将满时,姜云昭收到封不同往常的信。
程砚舟的字迹难得潦草:“边关恐有变故,商队三日后抵北疆,万万谨慎!”她摩挲着信纸,
心跳如擂鼓。北疆的夜风裹挟着细沙拍打在帐篷上,发出细碎的声响。
姜云昭摩挲着腰间半块玉佩,指尖感受着上面"砚"字的每一笔划。三年了,
当初刻骨铭心的约定,如今只剩三天就能实现。“姜校尉!”帐外传来亲兵急促的呼唤,
“斥候在三十里外发现商队踪迹,但...似乎有马匪尾随!”姜云昭眼神一凛,
佩剑已握在手中:“备马!点二十轻骑随我出营!”马蹄掀起滚滚黄沙。
三年军旅生涯已将当年那个爬树摘梅的小姑娘,打磨成令敌人闻风丧胆的"赤焰校尉"。
她伏在马背上,红缨盔下的双眸如鹰隼般锐利。远处山谷传来兵刃相接之声。
姜云昭抬手示意队伍分散包抄,自己则纵马直冲声源处。转过山隘,
眼前景象让她呼吸一滞——十余辆马车围成防御圈,
三十多名商队护卫正与数量近乎两倍的马匪厮杀。而最引人注目的,
是站在最高那辆马车顶部的修长身影。那人一袭靛青长衫,手中长弓如满月,
箭矢破空之声不绝。每一箭射出,必有一名马匪应声落马。那背影陌生又熟悉,
姜云昭心头猛地一跳。“杀!”她压下纷乱思绪,长剑出鞘如龙吟。
二十铁骑如尖刀插入战局,马匪阵型顿时大乱。混战中,一支冷箭直取姜云昭后心。
电光火石间,马车顶上那人飞身扑来,竟以手臂硬生生挡下这一箭!
“云昭...”熟悉的气息笼罩下来,姜云昭抬眼对上一双梦中出现过千百次的眼睛。
程砚舟脸色苍白,却笑得如当年那个递给她糖画的少年,“三年零三天,我来赴约了。
”战后营地篝火噼啪作响。姜云昭小心翼翼为程砚舟包扎手臂伤口。“怎么认出我的?
”她低声问。三年军旅磨去了她所有女儿娇态,铠甲下的身姿比许多男子还要挺拔。
程砚舟从怀中取出封信,边角已磨得发毛:“每月都收到这样的笔迹,怎会认不出?
”他指向信尾小剑图案。“只是没想到,当年画在沙地上的剑,如今真能取人性命。
”火光映着他轮廓分明的侧脸。当初温润如玉的少年,如今眉宇间多了几分坚毅。
姜云昭突然发现,他腰间悬着的半块玉佩上,“昭”字旁边新刻了朵小小的梅花。
“商队运的什么?值得“程少主”亲自押送?”她故意用上军中同僚的调侃语气。
程砚舟笑容微敛,从袖中取出个青铜零件。“这批货里混进了这个,北狄军械上的机括,
本该只有朝廷督造的兵器才有。”姜云昭瞳孔骤缩。上月边关冲突中,
北狄人使用的弩箭确实与朝廷最新研制的高度相似。“还有...”程砚舟欲言又止,
“你父亲为你定了亲事。对方是赵副将的公子。”篝火“啪”地爆出个火星。
姜云昭猛地站起,佩剑撞在地上发出清脆声响:“不可能!
父亲知道我们......”“他知道。”程砚舟苦笑,“正因知道,
才急着把你许给将门之子。”北疆大营中军帐内,姜震霆一掌拍裂了案几:“胡闹!
你可知那程砚舟是什么身份?商贾之子!
”姜云昭跪得笔直:“女儿只知他十二岁为救我挡恶犬,十五岁冒雨送玉佩,
如今又为查军械案亲涉险境...”“住口!”姜震霆须发皆张,
“你当为父不知你们书信往来?纵容至今已是仁慈!"帐外突然传来喧哗。
亲兵慌张来报:“将军,程家商队送来百车粮草说是...说是聘礼!
”姜震霆怒极反笑:“好个程砚舟!传令,让他滚进来!”程砚舟入帐时依然行晚辈礼,
背脊却挺得笔直。“晚辈自知门第低微,但有三事相禀。其一,已通过考核,
得圣上亲赐七品冠带;其二,发现军械走私线索;其三...”他看向姜云昭,眼神灼灼。
“愿参加今秋武举。”姜震霆冷笑:“商贾能参加科举?”“晚辈自有贵人赏识!”“父亲!
”姜云昭突然解下佩剑,“女儿愿以军功换一个机会。若程砚舟秋闱不入三甲,
女儿即刻嫁入赵家!”帐内死寂。良久,姜震霆抓起案上令箭一折为二:“记住你说的话。
”边城最隐蔽的酒馆地窖里,程砚舟与姜云昭对坐灯下。
桌上摊开着从商队货物中查获的异常单据。“所有线索都指向兵部左侍郎。
”程砚舟指尖划过一串数字,“三年来,经他手报废的军械足够武装万人。
”姜云昭眉头紧锁:“但北疆近期冲突规模不大,他们要这么多兵器...”“不是北狄。
”程砚舟突然压低声音。“西南藩王。”若藩王勾结朝臣私运军械,那就是谋反之罪!
“是赵家!”“必须拿到确凿证据。”姜云昭指尖无意识摩挲着玉佩,
“三日后父亲要去巡检军械库...”话音未落,窗外传来破空之声。姜云昭快速闪身,
一支弩箭已钉入她方才所在的位置,窗外黑影一闪而过。“是冲我来的。”姜云昭脸色突变。
夜晚,姜云昭潜行至赵家别院。透过窗缝,她看到赵小将军正与一个黑衣人密谈。
“...侍郎大人放心,姜家丫头活不过武举前夜...”姜云昭浑身血液冻结。
她正要退走,却听黑衣人冷笑道:“那个程家小子倒聪明,查到西南去了。
可惜明日商队过鹰愁涧时...”后面的话被雷声淹没。姜云昭冒雨狂奔回营,
却发现程砚舟已带商队连夜出发!“去鹰愁涧!”她扯过亲兵怒吼,“点我亲卫三十人,不,
五十人!立刻!”暴雨中的山道如同鬼门关。姜云昭不断催促战马,心中悔恨如潮。
若早知查案会将他置于险境...前方突然传来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火光中,
她看到商队马车正成排坠入深渊。“砚舟——!”爆炸的余震还在山涧回荡,
姜云昭已经纵马冲入烟尘。雨水混合着火药味刺入鼻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