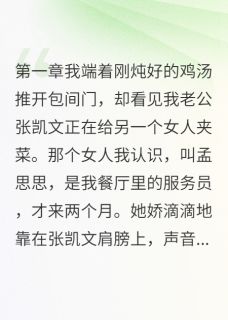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你亲手杀了我最后一个还想当你妻子的理由。”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病房。
身后,传来林佩雯尖利的咒骂和顾淮安彻底崩溃的哭嚎。
那些声音,被厚重的门隔绝,越来越远,直至消失。
新的病房,干净,明亮,窗外是郁郁葱葱的树木。
没有呛人的香水味,也没有绝望的空气。
沈言替我办好了一切,临走前,他将一份文件递给我。
“你的嫁妆,当初你父亲是以信托基金的方式给你的。顾淮安没有动用权,他只是想骗你签字,把监管权转给他。”
我愣住了。
“你的律师团队会帮你处理后续,把所有属于你的东西,一分不少地拿回来。”
我的眼眶有些发热。
原来,我所以为的“我们共渡难关”,从头到尾,都只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骗局。
离婚官司打得异常顺利。
沈言的律师团,是业内最顶尖的。
顾淮安那边请的律师,在他们面前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他想拖,想用舆论压我,想把我塑造成一个水性杨花、贪得无厌的女人。
可沈言的团队,只甩出了一份份证据。
顾淮安带姜思思回婚房的监控录像。
他对我动手的验伤报告。
以及,他亲口承认踢掉我孩子时,在病房里被沈言助理录下的音频。
每一条,都让他无力反驳。
法院最终判决我们离婚,婚内财产按照嫁妆协议分割,我带走所有属于我的东西,顾淮安需要额外支付我一笔巨额精神损失费。
拿到判决书那天,我在新公寓里,给自己开了一瓶香槟。
自由的滋味,真好。
关于姜思思的那条疤,她当然不肯善罢甘休。
法院的传票很快就拍在了我的脸上。
她告我故意伤害,索赔八百万。
附上的照片里,她脸上那道从眉骨蜿蜒到嘴角的疤,像一条狰狞的蜈蚣,趴在一张毁掉的脸上。
她要我用后半生来偿还。
开庭那天,我看见了她。
她坐在原告席,墨镜和口罩遮住了那条疤,却遮不住从骨子里渗出的怨毒。
她的律师口若悬河,把她塑造成一个为爱退让、却被嫉妒的疯女人残忍伤害的无辜者。
而我,就是那个面目可憎的毒妇。
法庭里,旁听席的窃窃私语像针一样扎过来。
我能感觉到那些视线,鄙夷,猎奇,幸灾乐祸。
轮到我方证人出庭时,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是顾家的管家,还有那几个平日里对我视若无睹的佣人。
我攥紧了手。
顾淮安发的薪水,顾家给的饭碗,他们会说什么,我早已料到。
不过是另一场,墙倒众人推的戏码。
管家第一个站上证人席,表情严肃。
我甚至已经准备好,听他如何颠倒黑白。
法官问话。他的回答却字字惊雷。
“那天,是姜**自己情绪激动,冲向太太。”
“她脚下没站稳,脸撞在了茶几上,是意外。”
“我们当时都在场,都看到了。”
我猛地抬起头,他身后,那几个佣人,竟然齐齐点头。
“是的,我们都看到了。”
“是她自己摔的。”
整个法庭,一片死寂。
连我的律师,都露出了错愕的表情。
姜思思在原告席上猛地弹了起来,口罩下的声音尖利扭曲。
“你们胡说!”
“顾淮安给了你们多少钱!那个贱女人给了你们多少钱!”
“你们都在撒谎!”
“肃静!”法官的法槌重重落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