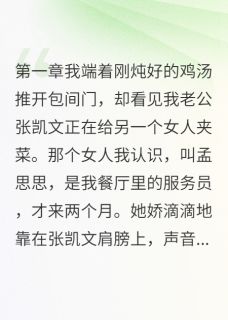沈耀很快便恢复了一丝生机。
他凛冽地瞪着我。
“沈清越,你真的是疯了,居然敢这么对我!”
“赶紧把我们放下来,手要断掉了啊。”
我冷冷地看着他们脸上的痛苦。
“为什么会痛呀弟弟,你不记得了吗?阿越可是经常这样被你吊起来呢。”
“那时候你是怎么说的来着?哦,对了,你说我天生贱种,就应该这样吊起来冷静冷静。”
“我还记得那一次,阿越过生日,好不容易攒够了钱买了一个生日蛋糕,可是蜡烛刚刚插上去,沈清冉就哭着跑了过来,她说她从来没有过过生日,很羡慕。”
“于是你反手就把阿越的蛋糕摔到了地上,还说阿越是天生贱种,根本不配吃这么好的蛋糕。”
“后来为了讨好沈清冉,你更是把阿越吊起来整整两天。”
“不吃不喝的两天,阿越被放下来的时候,手臂关节落下了永久性损伤,你知道吗?”
沈耀听着我的话,脸色骤然变白。
他的眼里罕见地闪过一丝慌乱。
他愧疚开口:“之前是我太冲动了,姐姐,你先冷静一点,先把我放下来好吗?”
“以后我会把你也当作姐姐好好对待的。”
我歪着头看他,眼里满是冷静。
“我不要了,迟来的深情比草贱。”
阿越已经没有了。
你早就失去了弥补的机会。
“弟弟啊,你知道阿越有多想得到你们的喜欢,你们的每一句恶毒话语,都会狠狠地剜她一刀,我以前真的不明白,为什么阿越就这么让你们讨厌?”
“现在我明白了,真假千金只是一个噱头,归根到底,你们从来没把她当作家人,你们只认沈清冉为家人。”
“阿越只是帮你们拉拢客户的东西,只是养大你的保姆,只是你们看不起的野种。”
“既然这样的话,阿越也不要你们的喜欢了,阿越要让自己开心。”
说着,我低下头便开始四处翻找起来。
最后,我找到放在一旁的牛肉干。
撕开包装袋,我抓出一根放进嘴里。
边嚼边说:“牛肉干还是太硬了,我看你们细皮嫩肉的,做成肉干应该挺不错的吧?”
听到我的话,沈耀害怕地大叫。
“沈清越,你到底想要做什么?你疯了?!”
我愣了一下,随后笑了起来。
“对啊,我早就疯了的,原本我早就要去死的,是阿越,是她把我拉回来的。”
“原本一切都在变好,但是,是你们亲手毁了这一切!”
“我就是个疯子啊,疯子就是要做一些常人无法忍受的事情,我就觉得,你们吊在这里,很适合晒成人干呢。”
说完,我拿起一块牛肉干放到沈清冉他们面前。
“看看,多么完美的纹路啊,可惜就是太小了一些。”
“不把你们切块,直接风干,那是多么大一块肉干啊。”
我认真地解说着。
沈清冉的身体控制不住颤抖起来。
“不要,不可以,你不能这么对我,你会坐牢的!”
我不为所动,斜眼看着她。
“我怎么会坐牢呢?”
“还得多谢你啊沈清冉,从绑匪手里死里逃生的少女患上精神病,多么名正言顺啊。”
说着,我手里的刀狠狠地划破了沈清冉的脸颊。
当初,沈清冉可是让那些绑匪一刀一刀剜下了阿越脸颊的肉。
看着阿越的面容彻底毁掉,他们才心满意足地大笑。
那现在,我也要让沈清冉的脸毁掉。
“晒成肉干皮肤都会皱,你这么漂亮的脸皮,还是不要晒皱吧。”
“放心,脸上的肉割了不会死的。”
沈清冉再也忍不住了,她号啕大哭起来。
身体剧烈挣扎着想逃。
却被我一拳打中了肚子。
她尖叫出声,拼命呼喊着沈耀救她。
可是一向对她言听计从的沈耀却咽了咽口水。
他讨好地看向我说:“姐姐,你到底在绑匪那里经历了什么?”
“你先冷静一下好不好?你到底经历了什么,都可以告诉我,我一定会给你出气的。”
“你为什么要割破沈清冉的脸?她对你做了什么?”
我笑着摇头。
“阿越跟你们说过很多次了,很多次,可是你们都不相信不是吗?”
“阿越说累了,不想再说了。”
“至于沈清冉的脸,她自己手脚不干净不要脸,我就成全她。”
说着,我不耐烦地皱眉。
“你们真的好吵啊,我现在就把你们的血放干好做成肉干。”
沈清冉一听,彻底绷不住了。
她猛烈的挣扎倒真的让绳子变松。
她摔倒在地,随后跪在我的脚边拼命磕头。
“清越是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求求你放过我,放我离开好不好,我保证,再也不出现在你面前。”
沈清冉满脸是泪,鼻涕也流了出来。
“是吗?那你说说你都做了哪些错事?”
沈清冉哭着说:
“我在你刚回来的时候,就把你推下楼梯,还假装是你推我。”
“我舞蹈夺不了冠,就故意扭伤脚踝,陷害你说是你不让我去跳舞。”
“我还故意撕掉沈耀的作业,说是你为了赶走我做的。”
“还有认亲宴上的绑匪绑架,也是我找人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羞辱你,但我没想到他们真的会完全不顾你的死活。”
“我还交代绑匪虐待你,挑断你的手筋脚筋,戳瞎你的眼睛,还把你的脸划烂。”
“我知道我很恶毒,我知道错了,求你不要把做成肉干。”
沈清冉浑身颤抖,泪流满面。
而沈耀在一旁瞪大了眼睛。
亲耳听到这些,他才终于明白。
自己一直尊敬喜爱的亲姐姐才是天生的坏种。
沈清冉眼睛都哭肿了,看起来无比可怜。
可是她一点都不值得人同情。
因为阿越之前,眼睛都快哭瞎了。
但她依旧没有放过她。
反而把她的指甲一个个拔了出来。
将她的衣服全部剪烂。
如明月高悬的阿越啊。
就这样残缺地失去了生命。
谁又曾可怜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