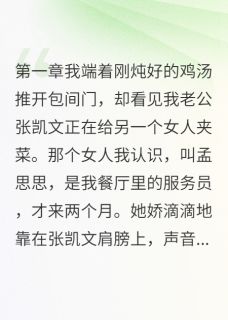1重生奶娃破大阵我渡劫失败重生为四岁女童,被家族弃子从死人堆里捡到。
他给我喂馊掉的米汤,我嫌难喝吐了他一身。“小祖宗,我只有这个了。
”少年擦着脏兮兮的袖子苦笑。家族大难临头时,他抱着我杀回主家求救。
长老指着我们怒骂:“沈厌你这小畜生,还带个拖油瓶回来?
”我奶声奶气回怼:“老畜生骂谁?”弹指间破了护族大阵,全场鸦雀无声。“都跪下!
”我啃着灵果含糊下令,“本座饿了。
”---2乱葬岗的生机死亡的味道浓郁得几乎凝结成块,沉沉压在荒芜的乱葬岗上,
挥之不去。
凝固发黑的血块、还有某种内脏被粗暴翻搅后散逸的腥甜……所有气息混杂在污浊的空气里,
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粘稠。几只铁灰色的乌鸦立在枯死扭曲的枝桠上,
血红的眼珠冷漠地俯视着下方,偶尔发出一两声粗嘎难听的鸣叫,
像是在为这片被遗忘之地唱着挽歌。沈厌就在这片死寂的泥泞里,
机械地翻动着那些僵硬冰冷的躯体。他身上的粗布麻衣早已被血污和泥浆浸透,
辨不出原本的颜色,紧贴在少年单薄的身架上,勾勒出嶙峋的骨形轮廓。
那张脸埋在乱糟糟垂下的黑发里,只露出一个紧绷的下颌线,嘴唇干裂发白,
沾着不知是自己还是别人的血迹。每一次俯身,每一次拉扯那些沉重的死物,
都牵扯着他背上那道尚未结痂、皮肉狰狞翻卷的鞭伤,尖锐的痛楚沿着脊椎窜上头顶,
让他眼前阵阵发黑。汗水混着泥污,沿着他沾满污垢的脖颈滑下,
在他粗重的喘息声中砸进身下暗红的泥地里。他在找食物,找任何一点能让他活下去的东西。
一个干瘪的馍馍,半块发硬的饼,甚至一块还算干净的布头……只要能塞进肚子里,
或者换到一点微末的希望。指尖在冰冷僵硬的肢体间摸索,触感滑腻而令人心底发毛,
但他已经麻木了。活下去,这个念头像烧红的烙铁,烫得他灵魂都在嘶鸣,
压倒了胃里翻江倒海的恶心。就在他掀开一具穿着破烂皮甲的壮硕尸体,
手指探向对方腰间那个干瘪的皮囊时——“饿……”一个极其微弱的声音,
带着刚睡醒般的含糊和奶气,突兀地钻进他的耳朵。沈厌的动作猛地僵住,
像被无形的冰锥刺穿了脊背。他保持着半蹲的姿势,手指还捏着那冰冷的皮囊,
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冻结。错觉?在这除了乌鸦和死人就只有他自己的鬼地方?他屏住呼吸,
侧耳倾听。风呜咽着穿过枯枝,乌鸦又发出一声沙哑的啼鸣。死寂重新笼罩。他垂下眼,
自嘲地扯了扯嘴角,一丝近乎冷酷的弧度。果然是饿得幻听了。他摇摇头,手上用力,
试图扯下那个皮囊。“饿……饿……”那声音又来了!比刚才清晰了一点,
带着孩子特有的执拗和委屈,细弱得像风中一缕随时会断的游丝,却无比清晰地再次响起。
这一次,沈厌听得分明。声音的来源,就在他脚边,被这具壮硕尸体压着的地方!
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又猛地松开,剧烈地撞击着胸腔。他几乎是凭着本能,
丢开那具沉重的尸体,双手发疯似的扒拉着尸体下方的烂泥和破碎的布片。
腐臭的气息扑面而来,但他什么都顾不上了。污泥和腐叶被慌乱地拨开。终于,
一抹极其微弱的、与周围死气沉沉截然不同的粉色,刺入了他被绝望浸染的眼帘。
那是一个小小的襁褓,用上好的、如今却沾满泥污和暗红血渍的锦缎包裹着。襁褓里,
露出一张脸。沈厌的动作骤然停住,呼吸也停滞了。那是个小得不可思议的女娃娃。
看上去顶多三四岁的样子,脸蛋粉雕玉琢,在这污秽之地显得异常突兀和干净。
长长的睫毛像两把小扇子,此刻正微微颤动着,在眼睑下投下一小片阴影。
小巧的鼻尖轻轻皱着,**的嘴唇微微噘起,发出无意识的、细弱的哼哼声,
小眉头还难受地蹙着。她还活着!这个认知像一道微弱的电流,
瞬间击穿了沈厌被疲惫和麻木包裹的心房,带来一丝微弱却尖锐的刺痛。他见过太多死亡,
从战场到流放路,再到这乱葬岗。死亡是常态,是冰冷的终结。可眼前这个小东西,
这抹脆弱到极致的生机,像一根细针,精准地刺破了他用冷漠筑起的壳。
一种难以言喻的酸涩猛地冲上鼻尖。他下意识地伸出手,指尖带着污泥和血痂,
却在触碰到那孩子温热柔软脸颊的前一瞬,猛地顿住,像被烫到一样缩了回来。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肮脏污秽的手,又看了看那张在污泥中依然纯净得不像话的小脸,
一种从未有过的、名为“自惭形秽”的情绪,笨拙而尖锐地攫住了他。他深吸一口气,
那腐臭的空气几乎让他窒息。他小心翼翼地,用尽可能干净的袖子内侧,
笨拙地、一点点地擦掉小娃娃脸上沾着的污泥。动作生涩得像个刚学步的孩子,
生怕自己粗糙的触碰会弄碎这易碎的珍宝。“饿……”小娃娃似乎感觉到动静,
小嘴又瘪了瘪,发出更清晰的**,带着浓浓的委屈。沈厌的心像是被一只小手揪了一下。
他手忙脚乱地在身上摸索,翻遍了每一个破口袋,每一个可能藏东西的角落。最终,
只掏出一个同样脏污不堪、瘪瘪的皮质水囊。拔开塞子,一股淡淡的馊味弥漫开来。
里面是昨天他在一个废弃的土灶旁找到的一点米汤,早已冷透,微微发酸。他犹豫了。
这玩意儿……连他自己喝下去都觉得喉咙发紧。他看看水囊,
又看看怀里那粉雕玉琢、一看就娇贵无比的小娃娃。这馊米汤……她怎么喝?
可那细弱的“饿”字,像小锤子一样敲打着他。他咬咬牙,用破烂的衣角使劲擦了擦囊口,
然后小心翼翼地凑近小娃娃的嘴唇,试图倾倒一点点进去。微凉、带着明显馊味的浑浊液体,
沾湿了玄璃的唇瓣。几乎是立刻,玄璃那原本还迷迷糊糊蹙着的眉头猛地拧成了结,
小脸皱得像只刚出笼的包子。一种源自灵魂深处、对污秽之物的极度厌恶感,
排山倒海般冲垮了她残余的睡意和混沌。“噗——!”她毫不客气地、用尽全身力气,
猛地将嘴里那点馊水吐了出来。不偏不倚,
全喷在了沈厌那张凑得极近、写满紧张和忐忑的脸上!
一股难以形容的、混杂着食物腐败和胃酸的气息瞬间糊了他一脸。沈厌整个人都僵住了。
冰冷的馊米汤顺着他脏污的脸颊往下淌,滑进脖颈,带来黏腻湿冷的触感。
他保持着那个俯身喂水的姿势,一动不动,像尊被雷劈中的泥塑。
那双总是带着戒备和阴郁的眼里,此刻只剩下纯粹的呆滞和错愕。他甚至忘了去擦。
玄璃吐完,似乎舒服了一点,但那股馊味还萦绕在鼻尖,让她极其不爽。
她费力地掀开沉重的眼皮,乌溜溜的大眼睛里还蒙着一层水汽,
带着刚睡醒的迷蒙和被打扰后的巨大不满。她努力聚焦,
终于看清了眼前这个“胆敢”用馊水“毒害”自己的家伙。一个……脏兮兮的少年?
头发像乱草,脸上糊满泥和不知道是什么的污迹,还有自己刚才喷上去的馊米汤,
正顺着他的下巴往下滴。衣服破破烂烂,露出的皮肤上带着伤。
整个人狼狈得像刚从泥坑里滚出来的流浪狗。玄璃嫌弃地撇了撇小嘴,
小奶音带着浓浓的起床气和被冒犯的愤怒,又软又冲:“难喝!臭臭!”这脆生生的控诉,
终于把石化的沈厌砸醒了。他猛地回过神,脸上瞬间涨得通红,连耳根都烧了起来。
不是羞涩,而是巨大的窘迫和一种……被当面戳破所有不堪的狼狈。
他手忙脚乱地抬起自己同样脏污不堪的袖子,胡乱地在脸上抹着,试图擦掉那些馊水和泥污。
袖子粗糙的布料蹭过皮肤,反而把脏污抹得更开,糊成了一片滑稽的地图。
他不敢再看那双清澈得能映出自己狼狈倒影的眼睛,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
声音干涩沙哑得厉害,
带着一种近乎卑微的局促和苦涩:“小……小祖宗……”他胡乱抹着脸,
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对…对不住……我……我只有这个了……”玄璃没吭声,
只是用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毫不避讳地、直勾勾地盯着他,小眉头依然蹙着,
**的小嘴抿得紧紧的,一副“我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小模样。那眼神,
仿佛在无声地审判他:你就给我吃这个?沈厌被她看得头皮发麻,手足无措。
他慌乱地移开视线,目光扫过周围堆积如山的腐尸,掠过枯枝上虎视眈眈的乌鸦,
最后落回自己空空如也的破口袋和手里那个散发着馊味的水囊上。一股冰冷的绝望,
混合着被这小小生命嫌弃的难堪,像毒藤一样再次缠绕上来,勒得他几乎窒息。他张了张嘴,
想说点什么,或许解释,或许道歉,但最终只挤出几个破碎的音节,便彻底哑了。
他颓然地垂下头,肩膀垮了下去,仿佛瞬间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在这片无边的死亡之海里,
他连一点干净的食物都找不到,又拿什么去养活这个娇气的小祖宗?
刚才那一瞬间生出的、想要护住这点微光的冲动,此刻被冰冷的现实砸得粉碎。
玄璃看着他瞬间黯淡下去的眼神,看着那少年身上几乎要溢出来的绝望和卑微,
嫌弃的小表情微微顿了一下。她虽然现在身体缩水了,脑子也因为强行涅槃而混沌不清,
但属于老祖的阅历和识人之能并未完全消失。眼前这个少年,虽然脏得像块抹布,
但那眼神深处,除了绝望,似乎还有一点点……别的什么东西?算了。
玄璃在心里嫌弃地哼了一声,小脑袋费力地转了转,打量着这片尸山血海,
感受着空气中稀薄到几近于无的灵气。啧,这环境,比魔修的粪坑还糟心。她堂堂……算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眼下这具脆弱的小身板,饿得前胸贴后背,再不吃点东西,
怕是真的要再死一次了。她极其不情愿地、勉为其难地,
把视线又挪回到沈厌那张糊得五彩斑斓的脸上,以及他手里那个散发着“毒气”的破水囊上。
小嘴瘪了又瘪,内心天人交战。最终,
生存的本能(以及这具身体强烈的饥饿感)压倒了灵魂深处的高贵(和洁癖)。
她极其嫌弃地、用一种“本座屈尊降贵”的眼神瞥了沈厌一眼,
然后伸出白**嫩、肉乎乎的小手指,极其勉强地,指了指那个水囊。
小奶音带着十二万分的不情愿,哼唧道:“那……再、再试试……”说完,
立刻紧紧闭上了眼睛,小眉头皱得死紧,一副准备英勇就义、喝毒药的悲壮表情。
沈厌猛地抬起头,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双原本黯淡的眼睛里,
瞬间炸开一丝微弱的、难以置信的光。
他看着怀里闭着眼、小脸绷得紧紧、仿佛不是要喝米汤而是要上刑场的小娃娃,
一股难以言喻的酸热猛地冲上眼眶。他手忙脚乱地再次把水囊凑过去,
这一次动作轻得不能再轻,屏住呼吸,小心翼翼地倾倒了一点点。
浑浊微凉的液体再次沾湿了玄璃的唇。“唔……”玄璃的小脸再次痛苦地皱成一团,
本能地想吐,但强大的意志力(主要是饿)让她硬生生忍住了。她闭着眼,
小嘴巴极其艰难地、小口小口地抿着那味道极其糟糕的液体,每咽下一口,
小小的身体都控制不住地轻微颤抖一下,仿佛在承受巨大的酷刑。
沈厌的心也跟着她的每一次吞咽而揪紧。他看着她痛苦的小表情,
看着她强忍着不适吞咽的样子,一种陌生的、滚烫的情绪在冰冷的胸腔里野蛮生长,
冲撞得他鼻尖发酸,喉咙发堵。他笨拙地用还算干净的袖子一角,
轻轻擦掉她嘴角溢出的馊水。动作依旧生硬,却带上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专注和……温柔?
终于,玄璃喝了几小口,再也无法忍受那可怕的味道和胃里的翻腾,小脑袋一偏,
坚决地避开了水囊口。她紧闭着眼,小胸脯微微起伏,显然在努力平复那股恶心感。
沈厌立刻收回水囊,不敢再勉强。他抱着怀里这轻飘飘、却又重逾千斤的小身体,
看着她苍白的小脸因为不适而微微泛起的红晕,一种强烈的冲动攫住了他。他深吸一口气,
那腐臭的空气似乎也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他用一种近乎发誓的语气,声音嘶哑却异常清晰,
一字一顿地说道:“别怕。”他顿了顿,像是在给自己,也给她一个承诺,“我……养你。
”玄璃没睁眼,只是在他怀里极其轻微地、嫌弃地哼唧了一声,
小脑袋往他那同样不算干净的衣襟里蹭了蹭,找了个稍微舒服点的姿势,
仿佛在无声地表示:哼,本座先信你一回,要是再敢给馊水……后果自负!
沈厌看着她依赖的小动作,感受着怀里那点微弱却真实的暖意和重量,
那颗在冰冷绝望中沉浮了太久的心,像是终于抓住了一块浮木。他收紧手臂,
小心翼翼地将这捡来的小祖宗护在怀中,仿佛护住了这死寂世界里唯一的光。他站起身,
背上的鞭伤因为动作牵拉而传来尖锐的疼痛,但他只是皱了皱眉,
目光扫过这片埋葬了无数尸骸的乱葬岗,最终投向远方阴霾笼罩的地平线。眼神里,
褪去了些许麻木,多了一种沉甸甸的东西。活下去。带着她,活下去。他迈开脚步,
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污浊的泥泞里,抱着怀里沉沉睡去的小娃娃,一步一步,
艰难地朝着未知的前方走去。身后,是死亡堆积的荒丘;前方,
是浓雾弥漫、危机四伏的未知。只有怀中这点微弱的呼吸和暖意,
成了支撑他走下去的全部力量。
---3逃亡黑云城日子在泥泞、饥饿和沈厌笨拙的求生中滑过,像钝刀子割肉,
缓慢而煎熬。沈厌用从死人堆里扒拉出来的破布,勉强给玄璃改了一件能裹身的小褂子,
又用还算干净的布条做了个简陋的襁褓背带,把她牢牢捆在自己胸前。
他像一头沉默而警惕的幼兽,带着他捡来的“小包袱”,在荒凉的流放之地边缘挣扎求生。
渴了,寻山涧里浑浊的水;饿了,挖苦涩难咽的草根,偶尔运气好,能掏到鸟窝里的蛋,
或是设陷阱捉到一只瘦得皮包骨的野鼠。每一次,
沈厌总是把能找到的最干净、最好的一点点东西,小心翼翼地喂给胸前的小祖宗。
玄璃的嫌弃是显而易见的。喂她喝浑浊的涧水,她小眉头能拧成麻花,小嘴紧闭,
非得沈厌笨拙地用破碗沉淀半天,把最上面那层勉强看得过去的“清水”喂给她,
她才肯赏脸抿几口。喂她烤得半生不熟、带着焦糊味的鸟蛋,她小嘴一撇,
能把头扭到脖子酸,直到沈厌手忙脚乱地把烤焦的部分一点点抠掉,
露出里面还算嫩滑的蛋黄,她才勉为其难地张开小嘴。
至于那些草根和偶尔能捉到的、烤得黑乎乎的老鼠肉?玄璃看都不会看一眼,小鼻子一耸,
直接表达最高级别的嫌弃。每当这时,沈厌只能默默地把那些难以下咽的东西塞进自己嘴里,
强忍着胃里的翻腾吞下去,然后更加拼命地去寻找下一顿可能好一点的食物。沈厌话很少,
大多数时候只是沉默地赶路,沉默地寻找食物,
沉默地应付着背上鞭伤反复发作的疼痛和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流放之地边缘,
从不缺少觊觎落单者的豺狼。只有对着玄璃时,他那双总是带着阴郁戒备的眼睛里,
才会流露出一丝笨拙的柔软。他会一边笨手笨脚地给她整理蹭乱的头发,
一边用干涩的嗓子低声哼着不成调的、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乡野小曲,试图哄她入睡。
他会指着天上飞过的一只怪模怪样的大鸟,或是路边一株颜色诡异的花朵,
用沙哑的声音告诉她:“看……鸟……花……”词汇匮乏得可怜。
玄璃大多数时候都只是懒洋洋地窝在他胸前,要么闭目养神,
努力运转着体内那丝微弱得几乎感觉不到的涅槃之力修复根基,
要么就用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没什么情绪地看着少年忙碌、战斗、挣扎。
偶尔被他的笨拙逗得烦了,或是实在受不了食物的粗劣,才会从鼻子里哼唧一声,
表达自己的不满。沈厌从不生气,只是更加手忙脚乱,
眼神里的歉意和笨拙的讨好几乎要溢出来。玄璃嘴上嫌弃着,心里却门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