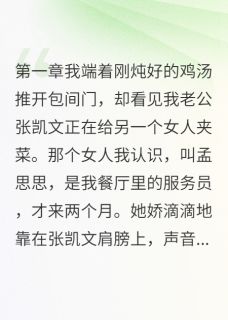我们像两棵并生的树,根缠了十年。直到他亲手劈开纠缠的根须,
我才看清树心的年轮早已腐朽。和许昭冷战第五十二天。
他带了隔壁艺校的姑娘参加毕业旅行。篝火边有人起哄:「昭哥,这才配得上你啊!
话说你当初怎么就看上陈禾了?」许昭拨弄着火星,笑得漫不经心:「从小吃惯了清粥小菜,
总得见识下大餐不是?」我站在帐篷的阴影里,没哭没闹,也没冲出去质问。
只是清楚地知道,我和许昭,十年的路,走到这儿,散了。1许昭晾了我快两个月。
巷子口那盏声控灯,亮了又灭,再也没等来他踢着石子喊禾苗的脚步声。那盏灯,
还是他小学时够不着,踩着我的肩膀才换好的灯泡。其实这半年,裂缝早已无声蔓延。
他打完球不再把汗湿的、带着阳光和青草味的球衣塞给我。放学也不再刻意绕远路,
踢着我家的门喊:“禾苗,开门!饿死了!”。巷子口那家他最爱吃的馄饨摊,
我们曾经共享过无数个冒着热气的傍晚。可每次他爸酒瓶砸碎的声音响起,
他妈压抑的哭声传来,他又会像只受伤归巢的兽,熟练地翻过我那扇吱呀作响的木窗,
带着一身低气压滚进我房间。他会扯着我洗得发白的睡衣袖子,声音闷在被子里,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脆弱:「禾苗,别走…就一会儿。」这扇窗,他翻越了十年,
窗棂上那道被他无数次借力踩出的凹痕,是我和他共享的秘密。一个月前那晚,
窗外炸雷滚过,雨点砸在瓦片上噼啪作响。他又带着一身湿漉漉的寒气翻进来,
头发上的水珠蹭着我脖颈,冰得我一颤。空气粘稠得像化不开的劣质糖浆,甜得发齁,
又带着雨水的腥气。我像小时候无数次那样,笨拙地哼着外婆哄我的摇篮曲,
试图驱散他眼底的阴霾。“别唱了陈禾!吵死了!”他烦躁地低吼,手却紧紧捂在我嘴上,
掌心滚烫。那只手,曾无数次牵着我跑过雨巷,替我挡过飞来的石子。可下一秒,
那手又猛地滑下,死死攥住我的手腕,力道大得骨头都在叫嚣。黑暗中,
他的呼吸粗重地喷在我颈侧,带着酒气和一种陌生的、令人心悸的侵略性。
月光从窗帘缝隙漏进来,在斑驳的墙上投下我们扭曲交叠的影子。最后,他喉结剧烈滚动,
哑着嗓子骂了句脏话,额头抵着我的,滚烫的皮肤相贴,像要灼烧起来。「…禾苗,别唱了。
」外婆缝的、装着干茉莉花瓣的旧香囊,不知何时掉落在枕边。那熟悉的、令人心安的甜香,
在黑暗中被蒸腾得又苦又涩。天蒙蒙亮,他就走了,像每一次仓促的逃离。
窗棂上那块他常借力翻越的木框,被晨露洇湿了一块深色,像未干的泪痕,
也像一道新鲜的伤口。再后来,我的信息石沉大海,红色的感叹号刺得眼疼。
电话永远是忙音,冰冷的电子女声重复着“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连巷子里的野猫都不再在他家门口等我喂食了。直到班花李薇无意间在课间闲聊,
声音不大不小,刚好飘进我耳朵。「哎,你们看见没?许昭最近可拉风了,
载着个艺校的姑娘,骑着摩托飙得飞快,后座那姑娘搂着他的腰,笑得那叫一个开心!」
她斜睨我一眼,嘴角挂着意味深长的笑。我对着洗漱间那块模糊的水银镜。
镜子里还是那个头发有点毛躁、穿着洗得发白校服的陈禾。
和许昭身边那个画报里走出来的、会发光似的姑娘比,我就像颗蒙尘的玻璃珠子,黯淡无光。
可心底那点扎根了十年的、名为习惯的藤蔓,还在不甘地缠绕,试图抓住最后一点微光。
那微光,是十年前他把我从欺负我的大孩子手里拉出来时,
擦破的胳膊;是他偷摘隔壁阿婆的枇杷,把最黄最甜的那颗塞给我时,
亮晶晶的眼睛;是无数个雷雨夜,他翻窗进来,缩在我床脚地铺上,呼吸均匀后,
那点让人心安的依赖。毕业旅行这晚,
很久钱才买下的那条碎花裙——是许昭曾指着橱窗说“这裙子挺适合你这种小土包”的那条。
我笨拙地拧开李薇送的樱桃色唇彩,对着小镜子涂了又擦,擦了又涂,笨拙得像第一次学步。
挤上大巴时,许昭正戴着无线耳机靠窗假寐,侧脸线条在晨光里依旧好看得让人心头发酸。
他旁边的座位空着,却放着一个与这破旧大巴格格不入的、亮闪闪的铆钉包,
像一道无声的宣告。我默默走到最后一排,缩进角落。裙摆下的帆布鞋边缘,磨得起毛,
硌着脚踝的旧伤疤隐隐作痛。2营地篝火烧得噼啪作响,火星四溅。啤酒罐滚了一地,
空气里弥漫着烤肉焦糊、廉价啤酒和年轻汗液混合的躁动气息。我像误入盛宴的局外人,
到得晚,只能缩在人群最外围帐篷投下的浓重阴影里。这里离温暖的光源很远,
离喧嚣的笑闹声也很远。没人注意我。或者说,没人想注意我。所有的目光都像被磁石吸引,
牢牢黏在许昭和他身边那个叫林璐的姑娘身上。火焰在她明艳的脸上跳跃,她仰起脸笑,
眼波流转间像盛满了揉碎的星光。
**在吊带外的皮肤在跳动的火光下泛着蜜釉般诱人的光泽,每一个动作都充满自信的张力。
起哄的声浪一波高过一波,带着酒精催化下的放肆:「昭哥!介绍介绍啊!
藏着掖着算怎么回事?」「就是!这颜值!这才叫天生丽质!甩咱们班那些庸脂俗粉十条街!
」有人意有所指地高声附和。「哎,话说回来,」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男生拔高声音,
带着毫不掩饰的恶意调侃,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阴暗角落,最终定格在我身上。「昭哥,
兄弟一直想不通,你当初怎么看上陈禾的?眼瘸了?那会儿食堂打饭大妈都比她水灵吧?
哈哈哈哈!」空气瞬间凝滞成冰。哄笑声卡在半空,有人尴尬地清清嗓子,
更多看好戏的目光聚焦过来,像无数细小的针。许昭像是被这直白的挑衅逗乐了,
又像是急于融入这份狂欢。他懒洋洋地笑起来,那笑容我曾经无比熟悉,此刻却陌生得刺眼。
他随手抓起一根柴火棍,漫不经心地拨弄火堆,溅起一片灼热的火星,
有几颗差点落到我脚边。他挑眉,语气混不吝,目光轻飘飘地掠过跳跃的火苗,扫过人群,
没有一丝一毫落向我所在的阴影,「从小吃惯了清粥小菜,」他顿了顿,
嘴角勾起一抹无谓的笑,声音清晰地穿透喧闹,「总得见识下大餐不是?」「靠!精辟!」
「昭哥威武!早该开开荤了!清粥小菜吃多了也腻歪!」刺耳的哄笑声再次炸开,
比之前更响,更肆无忌惮。像无数把钝刀子反复切割着那根名为十年的神经。
那些曾经一起长大的伙伴,此刻都成了这凌迟的帮凶。我站在冰冷刺骨的阴影里,浑身冰凉,
血液仿佛都凝固了。指甲深深陷进掌心,掐破皮肤,渗出血珠,却感觉不到一丝疼痛。
只有心脏被狠狠攥紧,又被那冰冷的嘲笑声撕扯成碎片的钝响。
看着许昭接过林璐笑意盈盈递来的、烤得焦香的肉串,
指尖状似无意地擦过她白皙光滑的手背。林璐娇笑着轻捶他肩膀,他不但不躲,
反而顺势揽了一下。火光勾勒出他们亲昵依偎的剪影,美好得像一幅精心构图的海报。
这幅画面,彻底覆盖了记忆中那个为我打架、擦着鼻血说「别怕,有我。」的男孩。
那些一起爬过的枇杷树,一起淋过的大雨,一起挨过的骂,
一起埋下的时光胶囊……在这一刻,被那轻飘飘的清粥小菜四个字,彻底碾碎成齑粉,
混着篝火的灰烬,被风吹散,再也拼凑不回来。原来,十年的相伴,在他口中,
不过是一段吃腻了的寡淡经历。原来,我视若珍宝的羁绊,不过是他用来垫脚,
去够向所谓大餐的、可以随时丢弃的旧台阶。3我没有冲出去质问。不是懦弱,
是那巨大的、冰冷的失望,像深海的水压,瞬间抽干了肺里所有的空气,
也冻结了所有激烈反应的能力。心口那块地方,空得只剩下木然的回响,
连一滴泪都榨不出来。只是在看到林璐被突如其来的夜风吹得缩了缩肩膀,
许昭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带着一种熟稔,一把脱下他身上那件外套,
无比自然地披在了林璐的肩上。林璐回眸一笑,火光映着她精致的侧脸,满是依赖和甜蜜。
4回程的大巴像个巨大的、摇摇晃晃的金属罐头,载着一车青春的狼藉和沉甸甸的疲惫。
手机屏幕在黑暗中突兀地亮起,微弱的光映着我麻木的脸。是许昭的信息。「晚上跑哪去了?
没见你人。」语气平淡得像在询问一个走失的物件。
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模糊的、被速度拉成光带的灯火,手指冰凉得几乎失去知觉,
僵硬地打字:「帐篷里,有点累。」每一个字都像在心上刻。那边沉默了很久,
久到屏幕暗下去,又被我按亮,再暗下去。就在我以为他不会再回时,
屏幕才终于吝啬地再次亮起。「哦。」一个单薄、冰冷、毫无意义的音节,
像一枚生锈的图钉,精准地钉在我心口那片早已空茫的废墟上。我关掉屏幕,
额头重重抵在冰凉的车窗上。玻璃的寒意透过皮肤,直刺骨髓。
窗外是飞驰而过的、模糊的灯火,像被拉长、扭曲、最终消逝的时光胶片。
车窗上映着我模糊的轮廓,还有那片被远远抛在身后的、燃烧着虚假欢笑的营地。莫名地,
清晰地想起小学毕业那个暴雨倾盆的傍晚。天空像被撕裂了口子。
他爸砸东西的巨响混着他妈绝望的哭喊,穿透雨幕。他像只被逼到绝境的、愤怒的小兽,
一脚踹开我家吱呀作响、不堪一击的木门。雨水顺着他倔强的短发、棱角初显的下颌往下淌,
在地板上洇开一片狼狈的水痕。那时,我蹲在他面前,笨拙地拿着干毛巾想帮他擦头发,
他猛地抬头,眼睛红得像兔子,哑着嗓子说:“禾苗,以后哥罩你一辈子。谁也不能欺负你。
”雨点砸在瓦片上,像密集的鼓点,敲打着那个关于“一辈子”的、稚嫩而郑重的承诺。
十年后的今天,那场雨仿佛从未停歇,冰冷刺骨,彻底浇熄了心底最后一点火星。我闭上眼,
在颠簸的黑暗里,在十年青梅竹马的光影碎片和今夜的冰冷嘲笑声中,
尝到了迟来的、咸涩的、名为清醒的味道。5那晚之后,许昭彻底淡出了我的视野。
我在外婆的老屋住了几天。对着院里那棵我们一起栽的枇杷树,发了很久的呆。
然后收拾了简单的行李,锁上了吱呀作响的木门。我申请了邻省的医学院,五年制。
录取通知静静躺在邮箱里。最后一次回学校拿档案。远远看见许昭的摩托停在巷口。
林璐穿着他的宽大球衣,光腿坐在后座,晃着脚丫。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是春末的下午,
暖风带着槐花的甜腻。抱着厚厚一摞复习资料的学生们嬉笑着走过。我穿着洗旧的校服,
帆布鞋边磨得起毛。站在爬满藤蔓的旧墙下。看着那个说要罩我一辈子的人。轻而易举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