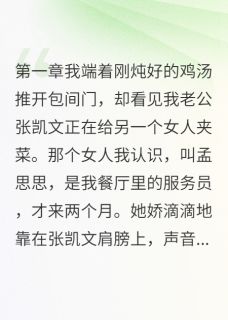荒年萤火永和七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陆沉蜷缩在破庙的角落里,
听着北风从残缺的窗棂间灌进来,发出呜呜的哀鸣。少年小心地护着怀里的半个炊饼,
那是他和宛儿在市集打零工赚来的口粮。半个炊饼,两人,能吃三天。很残酷的事实。
乱世的百姓若能好好活着,其余的便不敢奢求。怀中的炊饼早已冷硬得像块石头,
表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但,少年仍然能闻到一丝若有若无的麦香。"沉哥哥,你听。
"苏宛儿突然抓住他的手臂。十六岁的少女衣衫褴褛,单薄的粗布衣上虽然打满了补丁,
但依旧掩不住眼中灵动的光彩。她指着庙顶破洞外飘落的雪花,
冻得发青的嘴唇微微上扬:"像不像那年元宵,药铺张掌柜撒的糖霜?"陆沉喉头发紧。
他当然记得那个元宵夜。那时,父母尚在,宛儿娘为元宵夜新蒸的枣花馍,
甜香好似还萦绕在唇齿间。那时,他们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看花灯,张掌柜站在二楼,
将雪白的糖霜一把把撒向空中,为今年讨着红彩头。细碎的糖粒落在宛儿的发间,
而他总是偷偷伸手捻着一粒含在嘴里,现在想想,依旧甜得让人心尖发颤。在那年,
他第一次学了木雕,笨拙的为心上人雕刻了一根桃木簪。一根桃木簪,半朵旧荷花。"砰!
"一声巨响突然打断了回忆。破庙摇摇欲坠的门板被整个踹开,寒风卷着雪花呼啸而入。
三个披坚执锐的士兵提着灯笼闯进来,铁甲在火光下泛着冷光。为首者腰间缠着玉带,
莹润透亮,一看就知不是凡品。"就是她!"满脸横肉的士兵指着宛儿,
眼中闪着令人不适的光,"梁王殿下要的童女,带走!"陆沉脑袋嗡的一声,
但还是几乎本能地抄起地上的烧火棍,挡在宛儿身前。他不该带她去市集的。棍子刚举起来,
就听"锵"的一声,对方腰刀出鞘,寒光闪过,烧火棍应声断成两截,
断裂处露出新鲜的木茬。"沉哥哥不要!"宛儿在身后死死拽住他的衣角。陆沉充耳不闻,
像只护崽的狼般扑上去,一口咬住那人持刀的手腕。铁锈味的血立刻灌满口腔,
他发狠地磨着牙,直到听见对方吃痛的咒骂。下一秒,少年只觉得肋下一凉,
接着是火烧般的剧痛。在剧痛之下,他硬生生被扯倒在地。"倒是个硬骨头。
"军汉甩着手上的血,冷笑地看着蜷缩在地的陆沉,
"可惜了这身硬骨头..."明晃晃的刀尖在他眼前晃了晃,接着便高高举起。
刺目的白光迎面而来,凌厉的刀风仿佛割在他脸上。宛儿突然扑到陆沉身上。
透过朦胧的视线,陆沉看到她后颈细小的绒毛被的刀尖卷起的气流肆意拂动。
她颤抖的声音带着哭腔:"我跟你走!别杀他!求你...""早这么识相不就好了?
"军汉一把拽起宛儿,粗鲁地扯开她的衣领检查,
"梁王殿下就喜欢这样嫩生生的..."陆沉挣扎着要爬起来,却被一脚踹回墙角。
他眼睁睁看着宛儿被拖向门外,少女回头望来的那一眼,像是要把他的模样刻进灵魂。
发间那根桃木簪在挣扎中掉落在地,"啪"的断成两截。"沉哥哥,
..."风雪吞没了她最后的呼喊。破庙重归寂静,只剩下陆沉粗重的喘息。
肋下的伤口汩汩流血,在冰冷的地面上汇成一汪小小的血潭。他艰难地爬向门口,
在雪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血痕。经过断成两截的桃木簪时,陆沉突然停下。
簪头那半朵歪歪扭扭的荷花居然完好无损,
花瓣上的刻痕还是少年心动时涨红着脸一笔一笔的勾勒。他颤抖着将断簪咬在嘴里,
桃木的苦涩混着血腥味在口腔中蔓延。远处城门上,"梁"字大旗在风雪中猎猎作响,
像只张牙舞爪的怪兽。陆沉死死盯着那面旗帜,直到视线被泪水模糊。庙门破碎,风雪愈大,
渐渐掩盖了地上的血迹,也掩盖了少女离去的足迹。陆沉的意识开始模糊。恍惚间,
他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元宵夜。宛儿穿着新裁的粉色袄子,发间别着新削的桃木簪,
踮起脚把一颗糖霜喂进他嘴里。"甜吗?"少女笑眼弯弯。"甜。"他听见自己说。
雪花落在睫毛上,融化成冰冷的水滴。陆沉艰难地眨着眼,看见远处的城墙上,
几点灯火在风雪中明灭不定,像是随时会被黑暗吞噬的萤火。
————血淬锋芒陆沉在雪地里爬了半夜。肋下的伤口已经冻得麻木,
血凝结成暗红色的冰碴,每一次呼吸都像有刀子刮着肺腑。他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只是本能地朝着远离城池的方向爬行,仿佛离那座挂着"梁"字大旗的城门越远,
就越能逃离这场噩梦。风雪渐猛,他的手指早已失去知觉,却仍死死攥着那半截桃木簪。
簪头的荷花沾了血,在苍白的雪地上拖出一道浅浅的红痕。
"再爬三步……就三步……"他咬牙往前挪动,却在下一刻彻底脱力,整张脸埋进雪里。
刺骨的寒意渗入骨髓,意识开始涣散。恍惚间,他似乎又听见宛儿的声音——"沉哥哥,
……""……在呢!"他扯了扯嘴角,喉咙里滚出一声嘶哑的笑,"一直在呢!
"可就在这时,头顶传来一声轻叹。"这伤再拖半天,华佗再世也救不了。"清冷的女声,
带着几分慵懒,却又隐含锐利。陆沉艰难地抬头,模糊的视线里,一袭红衣立在风雪中。
女子约莫二十出头,腰间缠着条银光闪闪的软鞭,靴底踩碎积雪的声音格外清脆。她蹲下身,
伸手拨开他额前结冰的发丝,露出一双审视的眼睛。"赤眉军,楚红绡。
"她简短地报上名号,随即掰开他的眼皮看了看,啧了一声:"想报仇就憋住这口气。
"话音未落,她一把将他扛上肩头。陆沉闷哼一声,肋下伤口撕裂,鲜血再次涌出,
滴落在雪地上,像绽开的红梅。他最后看到的,是远处城池上飘着的梁字大旗,
在风雪中猎猎作响。————赤眉军的营地藏在深山老林里,四周峭壁环绕,易守难攻。
陆沉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一张简陋的木床上,肋下的伤口已经被包扎好,但稍微一动,
便是钻心的疼。他打量着四周,下意识去摸腰间的断簪。"找这个?
"楚红绡的声音从门口传来。她斜倚在门框上,指尖转着那半截桃木簪,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陆沉伸手去抓,她却轻轻一抛,簪子落进他掌心。"女人的东西?"她挑眉。"……还我。
"他嗓音嘶哑。楚红绡嗤笑一声,没再追问,只是丢给他一套粗布衣裳:"给你上的好药,
能动了就换上,大当家要见你。"————赤眉军的刑台设在山崖边,四周围满了人。
陆沉被带到一座木台上,台下站着几十个赤眉军汉子,眼神或冷漠或戏谑,
像是在看一场好戏。"新来的?"一个满脸横肉的大汉走上前,手里捏着一块烧红的烙铁,
"赤眉军的规矩,入伙先留个记号。"陆沉还没反应过来,烙铁已经按在他的左肩上。
"嗤—嗤—"皮肉烧焦的气味瞬间弥漫开来,剧痛让他浑身痉挛,牙齿几乎咬碎,
却硬是没叫出声。"哟,骨头挺硬。"大汉咧嘴一笑,随手丢开烙铁,"行,算你过关。
"赤眉军的大当家是个独眼男人,身形瘦削,却透着股狠劲。他走上前,
扔给陆沉一把卷刃的破刀,指着刑台旁的一棵老榆树:"砍断它,你才算个人。
"他临走时回眸,轻瞥少年身侧不断滴落的血,不耐烦的翻着白眼。“先养好伤!”三天后。
陆沉握紧刀柄,喘着粗气,踉跄着走向那棵树。等伤好,他觉得自己等不了那么久。刀很钝,
树皮粗粝,他每一次挥砍都震得虎口发麻,更是震的肋下与左肩钻心的疼。不知过了多久,
少年的掌心早已血肉模糊,可树干上只留下几道浅痕。一天过去,树纹丝不动。两天过去,
树皮剥落了一小块。第三天深夜,陆沉瘫坐在树下,浑身脱力。"刀不是这么用的。
"楚红绡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陆沉回头,见她抱臂而立,月光勾勒出她英气的轮廓。
"力从地起,经腰过肩——"她抽出腰间的软鞭,缠住他的手腕,
带着他的胳膊划出一道弧线,"刀要走弧,不是蛮力。"鞭梢"啪"地抽在树干上,
震落几片枯叶。陆沉学着她的姿势挥刀,破风声惊起夜枭。"那丫头是你什么人?
"楚红绡突然问。"……邻家妹妹。"他嗓音低沉,"她爹……教过我认草药。""认草药?
"她冷笑,"现在要认的是杀人术。"说罢,她甩鞭卷走他手中的刀,寒光闪烁。"咔嚓!
"老榆树轰然倒地。————三个月后,陆沉已经能一刀劈断碗口粗的树。
赤眉军的训练残酷至极,每日天不亮就要负重攀崖,晌午对练刀法,傍晚学习潜行暗杀。
楚红绡偶尔会指点他,但大多数时候,她只是冷眼旁观。"你学得很快。"某天夜里,
她靠在树下,丢给他一壶酒。陆沉接过,仰头灌了一口,辛辣的液体烧过喉咙,
让他微微皱眉。"为什么救我?"他问。楚红绡眯起眼,月光映在她的眸子里,
像淬了冰的刀锋。"你眼里有火。"她淡淡道,"和我当年一样。"陆沉沉默片刻,
从怀里摸出那半截桃木簪。簪头的荷花已经被摩挲得发亮,花瓣上的刻痕依旧清晰。
"我要杀回去。"他说。楚红绡笑了:"赤眉军不缺送死的疯子。""我不是去送死。
"他抬头,眼神冷厉,"我要让梁王府——鸡犬不留。"夜风掠过山林,树影婆娑。
楚红绡盯着他看了许久,忽然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行,我教你。"她站起身,
红裙在风中翻飞,像一团燃烧的火。"但记住,赤眉军的刀,只斩该斩之人。
"陆沉握紧断簪,缓缓点头。远处,赤眉军的篝火仍在燃烧,映红了半边夜空。
——宫墙柳永和九年春,皇宫·掖庭苏宛儿跪在青石板上,指尖浸泡在刺骨的凉水里,
搓洗着一件件华贵的宫装。入宫三年,她的掌心早已磨出厚茧,指节在寒冬里冻得红肿发亮。
同批入宫的宫女死了六个——两个病死的,一个投井的,还有三个被嬷嬷活活打死的。
"动作快点!贵妃娘娘的衣裳若是耽搁了,仔细你的皮!"管事嬷嬷的藤条抽在她背上,
**辣的疼。宛儿咬牙加快动作,腕间的淤青隐隐作痛。三年前,
她被梁王的人强行带入王府,本以为会沦为玩物,却因容貌出众,被当作"贺礼"送进了宫。
可皇宫,不过是更大的牢笼。"听说没?皇上又罢朝了……""嘘!慎言!
前几日有个宫女议论朝政,直接被掌嘴五十,牙都打掉了……"身旁的宫女窃窃私语,
宛儿低头不语。她对这些毫无兴趣,只想活着——活着,或许还能再见到那个人。
她摸了摸耳垂上的小痣,嘴角微微翘起,那是陆沉曾经笑她将娘亲做的“米粒”粘错的地方。
三更,宫女居所宛儿蜷缩在通铺最角落,借着窗缝漏进的月光,悄悄展开一块素帕。
帕子上绣着半朵荷花——和当年那支桃木簪上的一模一样。
"沉哥哥……"她无声地动了动唇,指尖轻抚绣线。突然,门外传来脚步声。
她迅速将帕子塞入袖中,闭眼假寐。门被推开,烛火晃动。"看看这个吧,瞧着模样周正。
"一个尖细的嗓音说道。“这个是新来的,还没教会,怕冲撞了皇上。
”老嬷嬷小心翼翼的说着。“右房宫女……”“嗯--”之后便没了声音。突然,
宛儿感到有人掀开她的被子,粗鲁地捏住她的下巴。她被迫睁眼,
对上一张布满褶子的老脸——是内务府总管太监刘福。刘福眯眼打量她,
目光最终落在了少女耳边的那颗痣。"带走。"刘福压着嗓子尖叫道。
"椒房殿缺个奉茶宫女。"————翌日·御书房外宛儿捧着茶盘,指尖微微发抖。
这是她第一次近身伺候,稍有不慎便是死罪。"进去吧,皇上批折子时不喜吵闹。
"大宫女低声叮嘱,"放下茶就走,别抬头。"宛儿深吸一口气,推门而入。
御书房内龙涎香缭绕,年轻的帝王正伏案疾书,朱笔在奏折上勾画,眉头紧锁。
她轻手轻脚地放下茶盏,正要退下——"青州又闹蝗灾了。"皇帝突然开口,
声音清冷如玉磬。宛儿浑身一僵,指尖颤抖间不慎碰翻茶盏。滚烫的茶水泼在案角,
浸湿了一摞奏折。"奴婢该死!"她慌忙跪下,额头抵地。宛儿脑子一片空白,只是想着,
此生大抵见不到沉哥哥了。预想中的责罚并未降临。一只手伸来,抬起她的下巴。
宛儿被迫仰头,第一次看清天子的面容——萧景琰不过二十七八岁,眉眼如刀削般锋利,
眼下却泛着青黑,显然久未安眠。最让她心惊的是,皇帝案头竟摆着个褪色的荷包,
上面歪歪扭扭绣着半朵荷花。那个荷包,眼熟的让她心惊。
那是她七岁时学着绣的第一个荷包,送给了一个饿晕在豆腐坊门口的小书生。
"你家乡在青州?"皇帝松开手,语气莫名柔和了些。"……是。""梁王上月暴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