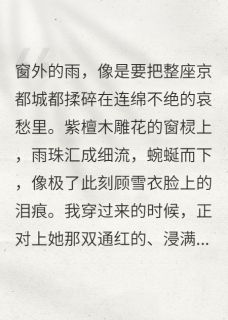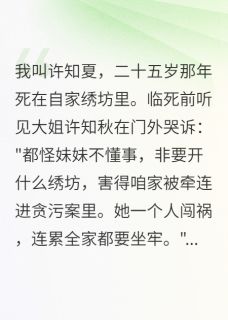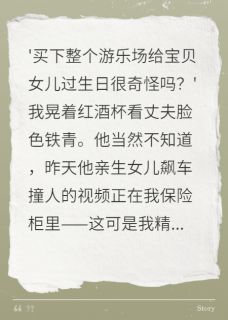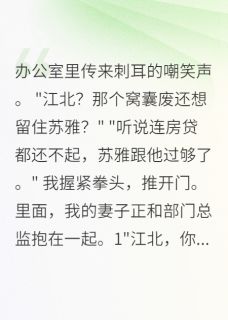第一章:圣谕降临江南的六月,蝉鸣裹着荷香漫过青瓦白墙。裴家云锦坊坐落在秦淮河畔,
三丈高的朱漆牌坊上,“天工云锦”四个鎏金大字被日头照得耀眼,坊内机杼声此起彼伏,
像春蚕啃食桑叶般细密。坊主裴明远负手立于绣楼回廊,看着底下忙碌的匠人。
染坊里蒸腾着五彩水汽,靛蓝、茜红、鹅黄的丝线在木架上晾晒,
风一吹便如流云倾泻;绣娘指尖银针穿梭,孔雀羽线在缎面上织出牡丹纹样,栩栩如生。
“承宇,这批素缎要赶在酉时前浸完苏芳染液。”他唤来长子,
目光扫过库房新到的雪蚕丝,“太后寿礼要用的料子,容不得半点差错。”裴承宇应声上前,
月白长衫袖口还沾着靛青颜料。他今年刚满二十,生得剑眉星目,自幼泡在工坊里,
连说话都带着织锦特有的韵律:“父亲放心,昨日已让匠人将金线重新过筛,
云锦的缠枝纹也按您的意思改了三稿。”话音未落,忽听得坊外马蹄声急,
八匹健马载着宫中侍卫疾驰而来,
领头的太监挥着明黄幡旗高声宣旨:“裴氏云锦坊接旨——”裴家上下顿时跪了满地。
裴明远膝盖重重磕在青石板上,掌心沁出薄汗。太监尖细的嗓音划破暑气:“太后万寿将至,
着裴氏三月内进献云锦十匹,纹样需含‘福、禄、寿、喜’,钦此!”圣旨展开的刹那,
裴明远瞥见末尾朱批的“御用监造”四字,
心脏猛地一跳——这意味着若得太后青睐,裴家便能成为皇家贡品的世袭工坊。
“谢主隆恩!”裴家众人齐叩首,额角在滚烫的石板上烙出红痕。
裴明姝从绣楼二楼探出身子,杏眼亮晶晶的。她是裴家唯一的女儿,
十三岁起便为坊里设计纹样,此刻裙摆扫过案头未干的《百寿图》,
胭脂红的颜料在宣纸上晕开,恰似她雀跃的心。倒是裴承轩懒洋洋倚在廊柱上,
腰间的玉坠随着动作轻晃。他向来不喜被工坊琐事缠身,前日还偷溜出去听戏,
此刻却被父亲严厉的目光钉在原地:“老二,即刻去码头接应波斯商人,
此次进贡要用的捻金线,可全指望着这批货。”裴承轩撇撇嘴,踢开脚边滚来的绣绷,
“知道了。”暮色初临时,云锦坊灯火通明。裴明远将圣旨供在祠堂,
香案前摆着刚织好的样布。烛火摇曳中,祥云中的寿星捧着仙桃,
金线勾勒的轮廓泛着温润的光。“家主,工坊清点完毕,现有金线只够织五匹。
”账房先生擦着汗进来,“波斯商队若晚到半月……”裴明远捏着茶盏的手青筋暴起,
茶汤在杯里晃出细密涟漪。他望着祖宗牌位,想起祖父临终前的话:“裴家云锦,成也金线,
败也金线。”窗外忽然传来乌鸦啼叫,惊得他打翻茶盏,滚烫的茶水在青砖上蜿蜒,
宛如一道不祥的血痕。第二章:忙碌工坊晨光熹微,云锦坊的铜铃便被推的匠人唤醒。
裴承宇披着星子就到了工坊,墨色长发随意束在脑后,发带还沾着昨夜试染的茜草汁。
他站在染缸前,用长木勺搅动翻滚的靛蓝染液,缸底沉淀的蓝草渣滓被搅起,
在晨曦中泛着幽光。“时辰到了,起布!”随着他一声令下,四名壮汉合力扯动绳索,
浸透染液的素缎缓缓升起,如同一道流动的暗夜星河。绣楼里,裴明姝正对着窗棂调配颜料。
案头摊开的《营造法式》里夹着半干的花瓣,她用狼毫蘸取石绿,在宣纸上轻点,
笔下的蝙蝠翅膀便泛起玉石般的光泽。“三妹,父亲让你去库房选金线。
”裴承宇的声音从楼下传来。裴明姝应了一声,裙摆扫过绣架,
惊起几只停在绣品上的粉蝶。工坊中央的织机旁站满了人,
老匠人王伯眯着眼调试花楼织机的花本。这架高过人头的木质织机是裴家的传家宝,
需两人配合——楼上拽花工根据花本提起经线,楼下织工投梭打纬。“承宇少爷,
这‘寿’字纹样的经线密度,还得再紧三分。”王伯布满老茧的手指抚过织机,
“否则金线织上去会打滑。”裴承宇蹲下身,仔细查看样布。
金线在缎面上勾勒的寿字虽已初见雏形,却略显松散。他解下腰间玉佩,将其压在纹样处,
“用这个当镇纸,织的时候每两寸停一停,让金线吃进纬线里。”正说着,
裴承轩大踏步走来,锦缎披风扫过染缸,溅起几点水花。“波斯商队明日酉时到。
”裴承轩随手抓起一块绣帕擦汗,帕子上未绣完的鸳鸯被他扯得变形,“不过他们要的货,
咱们库里怕是凑不齐。”此言一出,工坊里的机杼声都弱了几分。裴承宇直起身子,
目光如炬:“你这话什么意思?”裴承轩耸耸肩,
从袖中掏出羊皮卷:“他们点名要三年陈的苏芳木,可咱们库房里只剩去年的存货。
”羊皮卷展开,上面密密麻麻写着波斯文,末尾还画着狰狞的狮子图腾。裴明姝恰好赶来,
闻言脸色一白:“苏芳木陈化不足,染出的赤色会发暗,根本达不到贡品标准!
”裴承宇捏着羊皮卷的手微微发抖。他知道,波斯商人素来刁钻,若不能满足要求,
不仅拿不到捻金线,还可能坏了裴家的名声。“父亲呢?”他望向祠堂方向,
却见裴明远正扶着门框,脸色比往日更显苍白。“用矾水固色。
”裴明远的声音在寂静的工坊里回荡,惊飞了梁上的燕子,“把去年的苏芳木磨成粉,
兑三倍矾水熬煮,兴许能解燃眉之急。”他拄着拐杖走下台阶,每一步都似踩在众人心上,
“承宇,你带着王伯即刻试验;承轩,去码头盯着,务必让波斯人多宽限两日;明姝,
纹样再改,尽量减少赤色面积。”暮色四合时,工坊的灯火依旧通明。
裴承宇守在新架起的灶台旁,看着染缸里翻滚的矾水与苏芳木粉末。蒸汽模糊了他的眉眼,
刺鼻的气味呛得人咳嗽,可没人敢离开半步。
当第一匹用新方法染出的赤色缎面在灯下展开时,
众人都屏住了呼吸——那颜色虽不及陈年苏芳木染出的醇厚,却也红得夺目,
像极了天边的火烧云。裴明远伸手抚摸缎面,苍老的手指微微颤抖。他知道,这只是开始。
太后寿礼的十匹云锦,每一匹都如同一座山,压在裴家每个人肩头。而暗处,
不知还有多少双眼睛,正盯着云锦坊的一举一动。第三章:金线失窃天色破晓,
晨雾还未散尽,云锦坊内便响起一声尖锐的惊呼:“不好啦,金线没啦!
”这声呼喊像一道惊雷,瞬间震碎了工坊往日的宁静。裴承宇刚踏入工坊,
手中的账簿“啪”地掉落在地。他冲向存放金线的库房,
只见原本摆满金丝锭子的架子如今空空如也,地上只散落着几缕断金的丝线,
在晨光下泛着冰冷的光。“怎么回事?守夜的人呢?”裴承宇揪住一旁吓白了脸的小厮,
双眼通红,声音都因愤怒而发颤。小厮哆哆嗦嗦,话都说不利索:“昨、昨夜守夜的赵叔,
今早就不见人影了……”工坊里瞬间乱成一锅粥,匠人们交头接耳,
恐惧与猜疑在人群中蔓延。“这可如何是好,没了金线,拿什么织云锦?”“难道是遭了贼?
可咱们坊里安保向来严密啊!”裴明远被搀扶着赶来,看到空荡荡的库房,身子一晃,
险些栽倒。“彻查,给我把云锦坊翻个底朝天,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他声音沙哑,
带着从未有过的狠厉。裴承宇迅速冷静下来,指挥着家丁封锁工坊各个出入口,
“所有人不得随意走动,无关人等都集中到前院!”此时,裴明姝也匆匆赶来,
她身着素锦襦裙,发丝有些凌乱,显然是匆忙间赶来。“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
”她焦急地问道。裴承宇眉头紧锁,“三妹,我也正一头雾水。”裴明姝蹲下身子,
捡起地上那缕断金的丝线,仔细端详,“这切口平整,不像是被扯断,
倒像是被利刃割断……”裴承轩不知何时也出现在库房门口,他一改往日的不羁,神色凝重。
“我昨日在码头瞧见赵叔和一个形迹可疑的人交谈,当时没在意,
难不成……”他话还未说完,裴承宇猛地转身,目光如炬:“你为何不早说?
”裴承轩撇了撇嘴:“我哪能想到会出这档子事。”裴明远目光在两个儿子身上扫过,
重重地叹了口气,“当务之急,是找回金线,别在这相互指责。”搜查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
家丁们将工坊的每一个角落都翻了个遍,却一无所获。
裴承宇在工坊的后巷发现了一串奇怪的脚印,脚印较小,步伐间距不大,不像是成年男子。
顺着脚印的方向寻去,在墙角处发现了一小片染着靛蓝的碎布,
和工坊里匠人们的工作服布料一致。“这或许是个线索。
”裴承宇将碎布递给赶来的裴明姝。裴明姝接过,仔细嗅了嗅,“这上面除了靛蓝,
还有股淡淡的檀香味,不像是咱们工坊里的气味。”正说着,前院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
原来是几个家丁在柴房里发现了昏迷不醒的赵叔。众人急忙围过去,
裴明远命人将赵叔抬到工坊的偏房。赵叔悠悠转醒,眼神慌乱,看到裴家人,嘴唇哆嗦着,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赵叔,金线到底去哪儿了?”裴承宇急切地问道。赵叔张了张嘴,
声音微弱:“我……我也不知道,昨夜有人敲晕了我……”裴明远看着赵叔,
目光锐利如鹰:“你最好说实话,否则裴家上下不会轻饶你。”赵叔脸色煞白,
额头上豆大的汗珠滚落,刚要开口,突然双眼一翻,又昏了过去。此时,
工坊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众人的心瞬间又悬了起来,不知这又将带来怎样的变故。
第四章:兄妹生隙工坊里乱成一团,裴明远强撑着病体,在众人搀扶下回到主厅。
裴承宇和裴明姝一左一右跟在身后,裴承轩则远远落在后面,脸色阴沉得能拧出水来。
“承宇,工坊搜查得如何了?”裴明远靠在太师椅上,声音虚弱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裴承宇向前一步,拱手道:“回父亲,除了在后巷发现一些可疑脚印和染着靛蓝的碎布,
目前还未有其他重大线索。”说着,他将碎布呈到裴明远面前。裴明远接过碎布,
摩挲着布料,眉头紧锁:“这碎布看着眼熟,像是工坊匠人工作服上的。
”裴明姝也凑上前,“父亲,我闻着这布上有股陌生的檀香味,绝非咱们工坊里的。
”正说着,裴承轩冷哼一声:“哼,现在找这些有什么用,关键是得把金线找回来,
否则太后寿礼可就泡汤了。”裴承宇闻言,猛地转身,
目光如炬地盯着裴承轩:“你还有脸说!你不是瞧见赵叔和可疑之人交谈吗?若你早点告知,
说不定金线也不会丢!”裴承轩一听这话,瞬间炸了毛:“我怎么知道会出这种事?
再说了,你凭什么一口咬定跟我有关?”“就凭你平日里对家族生意不上心,整日在外闲逛,
结交些不三不四的人!”裴承宇越说越激动,手指几乎戳到裴承轩脸上。裴明姝见状,
急忙上前拉住裴承宇:“大哥,先别着急,咱们当务之急是找回金线,不是在这里争吵。
”裴明远重重地咳嗽几声,打断了兄弟俩的争吵:“够了!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窝里斗!
承轩,你且详细说说,那日在码头到底瞧见了什么。”裴承轩深吸一口气,
努力平复情绪:“那日我去码头等波斯商队,瞧见赵叔和一个身形瘦小的男子在角落里交谈,
那男子面色阴沉,看着不像好人。我当时以为赵叔在谈生意,没多想。”裴承宇皱着眉,
思索片刻:“身形瘦小……这倒与后巷脚印能对上。只是他们为何要偷金线,
又是如何避开工坊重重守卫的?”裴明姝咬着下唇,
眼神闪烁:“会不会是……咱们得罪了什么人,对方故意来捣乱?”裴明远长叹一声,
靠在椅背上,目光望向窗外摇曳的槐树:“树大招风,咱们裴家在这织造行里树敌不少。
可究竟是谁,竟如此大胆,敢动宫里钦点的贡品材料。”此时,一名家丁匆匆跑进来,
禀报道:“家主,官府的人来了,说是听闻金线失窃,前来协助调查。
”裴明远微微点头:“快请进来。”待官差走进主厅,为首的捕头抱拳道:“裴家主,
此事关乎皇家贡品,上头极为重视,我们定会全力以赴。只是,还望裴家能全力配合。
”裴明远拱手回礼:“有劳官爷,裴家上下自当全力配合。”官差们在工坊里四处查看,
询问匠人。裴承宇和裴明姝也跟着忙前忙后,回答问题。裴承轩则独自站在一旁,
看着众人忙碌,心中却五味杂陈。他望着库房方向,暗自思忖:“若真因我一时疏忽,
害了裴家,我该如何是好……”日头渐渐西斜,余晖洒在云锦坊的青瓦上,
却驱不散众人心中的阴霾。金线依旧下落不明,裴家笼罩在一片愁云惨雾之中,
而兄弟间的嫌隙,也在这紧张的氛围中悄然滋生,像一颗埋在心底的种子,
不知何时便会破土而出,带来更大的危机。第五章:家主病倒官差离去时,
暮色已悄然爬上云锦坊的飞檐。裴明远着太师椅扶手起身,忽觉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喉间涌上腥甜,“噗”地吐出一口鲜血,染红了月白色的衣襟。“父亲!
”裴明姝一声尖叫,裙摆扫翻了案上的茶盏。滚烫的茶水混着碎瓷在青砖上蔓延,
映出裴承宇苍白如纸的脸。他冲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父亲,触手之处,
老人的身子竟轻得像片枯叶。裴明远颤抖着抓住儿子的手腕,
气若游丝:“承宇……守住……”话未说完,便瘫软在他怀中。工坊内顿时炸开了锅。
绣娘们举着未完工的云锦,慌得连银针都掉在地上;染匠打翻了靛蓝染缸,
深蓝色的汁液在石板上蜿蜒,如同泣血的河流。裴承轩挤开人群冲进来,见父亲昏迷不醒,
脸上血色尽褪。他想起白天与兄长的争吵,指甲深深掐进掌心,
“都怪我……若我早说……”“别哭哭啼啼!”裴承宇猛地回头,
平日里温润的面容此刻布满寒霜,“快去请大夫!三妹,你即刻清点工坊存料,
看能否撑过这几日!”他的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却掩不住微微的发颤。
裴明姝咬着下唇,抹了把眼泪,转身奔向绣楼。大夫诊治后,摇着头开了几剂汤药。
“家主这是急火攻心,又积劳成疾,需好生将养。”大夫的话像重锤砸在众人心里。
裴承宇守在父亲床前,握着父亲布满老茧的手,想起儿时父亲手把手教他辨认丝线的场景。
如今这双手,却如此冰凉。深夜,云锦坊的灯火依旧通明。裴承宇站在工坊中央,
看着匠人们慌乱的身影,心中涌起一阵无力感。金线失窃,父亲病倒,
宫里的寿礼期限却不会等人。“王伯,以现有材料,能织出几匹云锦?
”他问向身旁白发苍苍的老匠人。王伯叹了口气,浑浊的眼睛里满是忧虑:“撑死三匹,
而且纹样得大幅简化,金线更是……”老人话音未落,工坊外突然传来一阵喧哗。
几个波斯商人怒气冲冲闯进来,为首的大胡子挥舞着羊皮卷:“裴家主呢?说好的苏芳木,
为何迟迟不交货?”裴承宇强压下心头的慌乱,上前拱手:“各位贵客,家父突染重病,
还望宽限几日……”“宽限?”大胡子冷笑一声,“我们的船队可不会等人!
若明日拿不到货,这捻金线,你们裴家也别想要了!”说罢,甩袖而去。
看着波斯商人远去的背影,裴承宇只觉双腿发软。他扶着织机,
指腹触到未完成的“寿”字纹样,金线空缺处的纬线显得如此刺眼。
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裴承轩递来一盏热茶:“哥,我……我去码头再求求他们。
”裴承宇盯着茶汤里自己扭曲的倒影,许久才道:“不必了,我自有办法。
”月光透过雕花窗棂洒进祠堂,裴承宇跪在祖宗牌位前,额头重重磕在青砖上。
“列祖列宗在上,承宇不肖,让裴家陷入如此绝境。但请放心,我就算拼尽性命,
也定会守住云锦坊!”祠堂里,只有烛火在风中摇曳,似在无声地回应着他的誓言。
而此时的裴家,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飘摇的船,不知能否等到黎明的曙光。
第六章:临危受命寅时的梆子声划破寂静,裴承宇在父亲的药碗,看着老人苍白的面容,
心中五味杂陈。昨夜跪在祠堂的誓言犹在耳畔,可现实的困境却如千斤重担,
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推开房门,夜色未散,云锦坊内却已亮起零星灯火。裴承宇紧了紧披风,
快步走向工坊。染坊里,几个匠人正围着染缸发愁,见到他,纷纷围上来:“少东家,
苏芳木不够,这赤色缎子怕是染不出来了。”裴承宇看着染缸里浑浊的液体,
沉思片刻道:“用茜草混朱砂试试,虽不及苏芳木正宗,但或许能应急。”话音未落,
账房先生急匆匆跑来,手里攥着账本:“少东家,波斯商人放话,若今日拿不到苏芳木,
不仅断了金线,还要我们赔偿双倍违约金!”裴承宇的太阳穴突突直跳,
强压下心中的慌乱,“你去准备些金银细软,我亲自去码头一趟。”转身欲走时,
裴明姝抱着一摞设计图拦住他:“大哥,我将纹样又改了一遍,尽量减少金线用量,
可……”她咬着嘴唇,眼中满是担忧。裴承宇伸手拍了拍妹妹的肩膀:“辛苦你了,
先去休息,一切有我。”来到码头,晨雾弥漫。波斯商队的大船如巨兽般停泊在岸边,
大胡子商人正指挥着仆从搬运货物。裴承宇深吸一口气,上前作揖:“还望您再通融几日,
家父病重,裴家实在……”“少废话!”大胡子打断他,“生意场上,只认契约!
”裴承宇从怀中掏出准备好的金锭,“这些先作为定金,五日后定将苏芳木送到。若违约,
裴某愿以云锦坊半数产业作赔!”大胡子盯着金锭,眼中闪过一丝犹豫,
最终一把夺过:“好,就再给你五日!若食言,就别怪我不客气!”回到云锦坊,
裴承宇还未喘口气,又传来噩耗——负责织机的老匠人突发急病,无法工作。
工坊里人心惶惶,不少人开始私下议论,担心裴家撑不过这次危机。裴承宇站在织机前,
看着空荡荡的花楼,突然想起儿时父亲教他的话:“织云锦,讲究的是心定、手稳、眼明。
”他撸起袖子,对众人道:“我来拽花!”说罢,登上花楼。
楼下的织工看着少东家生疏却坚定的动作,渐渐安静下来。机杼声再次响起,
虽然节奏不如老匠人那般流畅,但却带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夜幕降临时,裴承轩回来了,
身后跟着几个陌生汉子,肩上扛着几捆木料。“哥,我在码头结识了几个船商,
他们答应帮忙寻找苏芳木。这些木料,是用来加固织机的。”裴承轩低着头,
声音里带着愧疚。裴承宇看着弟弟,心中一暖,“回来就好,一起干!”深夜,
云锦坊依旧灯火通明。裴承宇站在染坊前,看着新染出的赤色缎子,
虽不如苏芳木染出的鲜艳,但也勉强能用。他揉了揉酸痛的肩膀,望向父亲的房间,
默默道:“父亲,您放心,裴家不会倒下。”而此时,在云锦坊的暗处,
一双眼睛正盯着忙碌的众人,嘴角勾起一抹阴冷的笑意。第七章:秘记初现雨丝如愁,
斜斜地掠过云锦坊的飞檐。裴明姝绣楼的窗前,手中的画笔悬在半空,迟迟落不下去。
案头摊开的设计图上,修改过无数次的纹样依旧差强人意,少了金线勾勒,总显得黯然失色。
她望着窗外被雨水打落的槐花,心中满是焦虑。“三**,该去给老爷送药了。
”丫鬟的声音从门外传来。裴明姝放下画笔,起身时衣角勾住了一旁的木匣,
“啪嗒”一声,木匣掉在地上,里面泛黄的纸张散落开来。她弯腰去捡,
一张字迹斑驳的纸引起了她的注意——上面画着奇怪的染线图谱,
落款处写着“裴氏先祖讳文远手记”。裴明姝心头一颤。裴文远是裴家百年前的先祖,
据说曾以一手出神入化的染金技艺名震江南,后因意外失传。她迫不及待地翻开纸张,
只见上面密密麻麻记载着用特殊矿石与植物混合,将普通丝线染成金光璀璨金线的方法。
“难道这就是失传已久的染金秘术?”她的手微微颤抖,心跳如擂鼓。顾不上给父亲送药,
裴明姝抓起纸张就往染坊跑。雨水打湿了她的鬓发,裙摆沾满泥泞,她却浑然不觉。染坊里,
裴承宇正盯着新染出的赤色缎子眉头紧皱,见妹妹这般模样,吓了一跳:“三妹,发生何事?
”裴明姝喘着粗气,将手记递到他面前:“大哥,你看这个!先祖的染金秘术,
或许能解决金线的难题!”裴承宇接过纸张,目光在上面快速扫过,
眼中渐渐燃起希望的光芒:“若真能成功,裴家就有救了!
只是这材料……”他的目光落在“需用上等辰砂、孔雀石”的记载上,又黯淡下来。
“我记得父亲书房的暗格里,似乎藏着些珍稀矿石。”裴明姝突然说道。两人对视一眼,
立刻奔向父亲的书房。书房里弥漫着浓浓的药香,裴明远仍在昏睡。
裴承宇轻手轻脚地移开墙上的画轴,露出暗格机关。随着“咔嗒”一声轻响,暗格打开,
里面整齐摆放着几个檀木匣子。打开其中一个匣子,
裴明姝惊喜地轻呼出声——里面正是所需的辰砂与孔雀石。
“父亲一定早就知道这些东西的用处。”裴承宇抚摸着匣子,眼眶微微发红。
他小心翼翼地取出矿石,转头对妹妹说:“走,去染坊试验,此事重大,切莫声张。
”回到染坊,他们支开众人,按照手记上的方法,将辰砂研磨成粉,
与孔雀石、明矾等按比例调配。当混合好的染料倒入锅中,
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原本灰扑扑的粉末,在火焰的炙烤下,渐渐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裴明姝屏住呼吸,将普通丝线浸入锅中,只见丝线缓缓染上一层璀璨的金色,
在烛火下流转着温润的光晕。“成功了!”裴承宇激动地握住妹妹的手,眼中闪烁着泪光。
这不仅是染金技艺的重现,更是裴家绝境中的一线生机。然而,喜悦过后,
一丝忧虑爬上裴明姝的心头:“大哥,这染金秘术如此珍贵,
若是被有心人知晓……”裴承宇神色一凛,握紧了拳头:“先瞒着所有人,加紧赶制云锦。
等度过此次危机,再从长计议。”此时,窗外的雨不知何时停了,一缕阳光穿透云层,
洒在染坊中染好的金丝线上,宛如预示着裴家即将迎来的转机。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在暗处,
一双眼睛早已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第八章:艰难尝试晨曦初破,
微光艰难地穿过厚重的云层,洒落在云锦坊的屋脊上。
裴承宇与裴明姝怀揣着那本承载着家族希望的手记,匆匆踏入染坊。
坊内弥漫着刺鼻的染料气味,混合着清晨的潮湿,让人无端生出几分不安。
裴承宇将辰砂、孔雀石等矿石仔细研磨,粉末在石钵中闪烁着细碎的光,宛如细碎的星辰。
裴明姝则在一旁,按照手记上的比例,小心翼翼地调配着明矾、草木灰等辅料,
额头沁出细密的汗珠。“大哥,这配比真的没问题吗?”她声音微微发颤,
眼神中满是忧虑。裴承宇紧抿双唇,目光坚定:“先祖既能记下这技艺,必有其道理,
咱们只管用心尝试。”一切准备就绪,裴承宇将调配好的染料缓缓倒入锅中,
火焰舔舐着锅底,锅中渐渐泛起奇异的光泽。裴明姝深吸一口气,拿起一缕普通丝线,
轻轻浸入锅中。一时间,两人屏气敛息,眼睛死死地盯着丝线,
仿佛那是裴家命运的全部寄托。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锅里的丝线并未如他们期望的那般,
染上璀璨的金色。反而,在高温的作用下,丝线开始变得焦黑,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焦糊味。
“怎么会这样?”裴明姝惊呼出声,眼中的希望瞬间破碎。
裴承宇眉头拧成一个“川”字,他迅速翻看手记,试图找出问题所在。
“难道是火候不对?还是说,这矿石的纯度不够?”他喃喃自语,声音中透着几分挫败。
两人并未气馁,他们重新调整配比,加大了辰砂的用量,又调整了火焰的大小。一次又一次,
锅中的丝线或是色泽暗淡,或是直接断裂,始终无法达到他们心中理想的效果。
日头渐渐升高,日光透过窗户,洒在他们疲惫的脸上。裴承宇的衣衫早已被汗水湿透,
贴在后背,发丝也凌乱地散落在额前;裴明姝的眼眶泛红,双手因长时间接触染料,
变得粗糙不堪。“不行,不能就这么放弃!”裴承宇猛地站起身,眼中重新燃起斗志,
“咱们再试试,把每种材料的用量精确到分毫,肯定能找到问题。”裴明姝用力点头,
眼中闪过一丝决然。他们再次投入到紧张的试验中,反复对比每一次的结果,
对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就在他们焦头烂额之际,工坊外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
裴承轩急匆匆地跑进来,神色慌张:“大哥、三妹,波斯商人又派人来催了,
说若今日拿不出苏芳木,明日就带着船队离开!”裴承宇手中的石钵险些掉落,
他稳住身形,深吸一口气:“你先去稳住他们,就说我们正在全力筹备,明日定能交货!
”裴承轩犹豫了一下,还是转身跑了出去。裴明姝望着哥哥,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大哥,
这可如何是好?染金技艺还未成功,苏芳木又……”裴承宇伸手轻轻拭去妹妹眼角的泪,
强装镇定:“别急,天无绝人之路。咱们先集中精力攻克染金难题,苏芳木的事,
我再想办法。”此时,染坊的门突然被一阵风吹开,一张破旧的纸张被卷了进来,
落在裴承宇脚下。他俯身捡起,发现竟是手记中的一页,
上面记载着一段被他们忽略的小字:“染金之术,需心无旁骛,以虔诚之心感应天地灵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