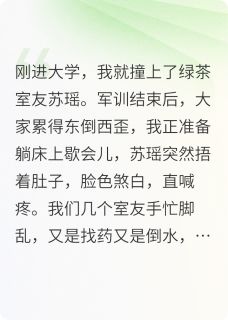>太子病逝那夜,我被塞进国子监顶替堂兄。>为掩盖女儿身,我日日偷吃缓解压力。
>某天撞翻谢珩的糖蒸酥酪,他咳着血轻笑:“苏公子胃口不错。
”>后来他教我伪造四皇子笔迹,替我挡下致命毒酒。>金銮殿上四皇子逼宫,
我高举伪造的退位诏书。>“诏书是假,龙袍为证!”谢珩掀开龙椅暗格。
>众人哗然中他攥住我发抖的手:“现在可以嫁我了?”>“你何时知道我是女子?
”>“从你偷吃第一块玫瑰酥开始。”---国子监后厨那条逼仄的巷子,
成了我苏明远(或者该说,苏霓)在这座庞大牢笼里唯一的喘息之地。
霉味、陈年油垢和阴沟的酸腐气混在一起,本该令人作呕,可于我而言,
却奇异地盖过了身上那股子挥之不去的、属于男人衣袍的浆洗气息。仿佛这污浊,
反倒成了一层遮羞的壳。我缩在最暗的墙角,背脊紧贴着冰冷湿滑的砖石,
几乎能感觉到青苔的凉意透过薄薄的春衫渗进来。心跳得又急又重,擂鼓似的撞击着胸腔,
震得指尖都在发麻。袖袋里那包用油纸裹得严严实实的玫瑰酥,成了此刻唯一的暖源,
也是唯一的救命稻草。指尖探进去,摸索着,终于触到那熟悉的、带着温热酥皮触感的边缘。
就在这时,一道影子,无声无息地落在我面前的地上。像一滴浓墨,
骤然滴入了这方昏暗的浊水。我浑身的血,瞬间冻住。
指尖正捏着那块好不容易掏出来的玫瑰酥,酥皮簌簌地往下掉着渣。影子动了动,
极其缓慢地向前延伸了一寸。我猛地抬头。逆着巷口那点惨淡的天光,一个人影立在那里。
身形颀长,却瘦削得像是随时会被风吹折的竹。宽大的月白澜衫空荡荡地罩在身上,风一过,
便勾勒出底下过于嶙峋的骨架轮廓。他站得不直,微微佝偻着肩背,
仿佛承受着某种无形的重压。是谢珩。那个名字无声地在舌尖滚过,带着冰碴子似的寒意。
太子殿下身边最得力的幕僚,也是这国子监里最令人捉摸不透的存在。清冷,寡言,
一张脸生得是极好,眼睫浓长,鼻梁挺直,唇色却是常年不见血色的淡,
衬得肤色愈发有种冰雪般的冷白。此刻,他那双深潭似的眼睛,正静静地看着我,或者说,
看着我那只僵在半空、捏着点心的手。目光里没什么情绪,却又像带着无形的钩子,
能轻易穿透我拙劣的伪装,直刺心底最深的惊惶。死寂。只有巷子深处不知何处滴落的水声,
嗒,嗒,嗒,敲在我绷紧的神经上。喉头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死死扼住,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甚至能听到自己牙齿细微打颤的咯咯声。谢珩的目光,终于从我手中的玫瑰酥,
缓缓移到了我惨白一片的脸上。他薄唇微启,似乎想说什么,然而话音未出,
却先被一阵剧烈的咳嗽截断。“咳…咳咳咳……”那咳声撕心裂肺,
像是要把整个胸腔都掏空。他猛地侧过身,一手死死抵住冰冷的砖墙,
一手迅速从袖中抽出一方素白的帕子,紧紧捂住口唇。
瘦削的肩胛骨在单薄的衣衫下剧烈地耸动着,每一次咳嗽都让他整个人痛苦地蜷缩,
几乎站立不稳。那压抑的、带着胸腔深处沉闷回音的声响,在狭窄的巷子里回荡,
听得人揪心。咳声终于暂歇,他喘息着,慢慢直起些腰。捂着唇的帕子缓缓放下,
那方素白上,赫然洇开一抹刺目的、如同新绽红梅般的血迹。我的呼吸彻底停滞了。
不是因为那血,而是因为恐惧——太子的人,病弱的谢珩,撞破了我的秘密!
这念头像冰冷的毒蛇,瞬间缠紧了我的心脏。谢珩却仿佛毫不在意那帕子上的血,
只随意地将其拢回袖中。他重新转向我,气息还有些不稳,带着微微的喘。
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眸里,竟浮起一丝极淡、几乎难以察觉的笑意。他看着我,
唇边勾起一个极浅的弧度,声音因为方才的咳嗽而显得更加低哑,
却清晰地送入我耳中:“苏公子……”他顿了顿,
目光若有似无地扫过我手中那块可怜的、酥皮掉了一半的玫瑰酥,
唇角那抹淡笑似乎深了一分,带着某种洞悉一切的了然,“……胃口不错。”轻飘飘五个字,
却像五把淬了冰的匕首,狠狠扎进我的四肢百骸。我脑中轰然一响,眼前发黑。完了。
---谢珩那句轻飘飘的“胃口不错”,像一道无形的枷锁,沉沉地套在了我的脖子上。
自那日后,我彻底成了他案头一件沉默的器物。国子监藏书楼顶层,
一间只容得下两人对坐的小室,成了我新的囚笼。这里远离尘嚣,
只有窗外偶尔掠过的飞鸟和书页翻动的沙沙声。
空气里常年弥漫着旧纸、墨锭和一丝若有若无的、属于谢珩身上清苦药香混合的气息。
他坐在我对面,隔着一张堆满卷宗和舆图的宽大书案。案上一角,
那只雨过天青色的秘色瓷碟里,每日都会准时出现几样精致的糕点。
有时是晶莹剔透的水晶桂花糕,有时是撒着雪白糖霜的豌豆黄,更多时候,
是当日撞破我秘密时、我曾失手打翻的那种糖蒸酥酪——细腻如凝脂,
上面缀着几粒饱满的酒酿桂花,散发出诱人的甜香。糕点无声地摆在那里,
像一种心照不宣的提醒,又像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看这里。
”谢珩的声音总是低而平缓,带着病气特有的微哑,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力量。
他苍白修长的手指,此刻正点在一页泛黄的古籍上。指尖微凉,指甲修剪得极为整洁,
透着一种玉石的质感。我的目光,却不由自主地,粘在了那碟糖蒸酥酪上。
那甜香丝丝缕缕钻入鼻腔,勾动着肠胃深处最原始的渴望。饥饿感,混杂着巨大的压力,
几乎让我坐立难安。“苏公子。”谢珩的声音微微抬高了一度,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冷意,
像一根细针,瞬间刺破了我对点心的迷思。我猛地回神,对上他深潭般的眼眸。
那里面没有责备,只有一种洞悉的平静,平静得令人心头发毛。他指尖并未移动,
依旧点在那行墨迹上。“前朝吏部侍郎王珣,因贪墨案下狱。其门生故旧营救,所用之法,
”他顿了顿,目光锐利地锁住我,“便是仿其政敌笔迹,伪造构陷书信,反将其政敌拖下水。
关键,在于形神兼备,更在于……抓住对手行文布局中那点细微的、自以为是的习惯。
”他移开手指,从旁边厚厚一沓信笺中抽出一张,推到我面前。纸张上墨迹淋漓,
是四皇子府中一位颇为倚重的幕僚,赵乾的手笔。字迹刚硬,转折处带着一股狠厉的锋芒。
“看他的‘之’字,”谢珩的声音又低了下去,带着一种引导的意味,“捺笔末端,
习惯性回勾,力道极重,几乎要戳破纸背。这是他早年习武留下的烙印,改不了。
再看句读转折处,从不留空,喜用浓墨一点,显其急躁专断。”他的讲解条分缕析,
冷静得如同在剖析一件死物。而我,则像一块干涸的海绵,
被迫吸收着这些冰冷而危险的技艺。模仿字迹,伪造文书,
窥探人心深处那些自以为隐藏得天衣无缝的弱点……这与我过去在闺阁中习练的簪花小楷,
与我被硬塞进这身男子衣袍前所认知的世界,隔着天堑。压力如同实质的巨石,
沉甸甸压在心口,每一次呼吸都带着滞涩的痛感。每当这种窒息感涌上来,
我的目光总会不受控制地飘向那碟糕点。仿佛只有那点甜腻的慰藉,
才能短暂地麻痹紧绷到极致的神经。有一次,我对着赵乾一幅狂草的临摹绞尽脑汁,
越写越糟,额角渗出细密的汗珠。那股熟悉的、混杂着焦虑的饥饿感又凶猛地袭来。
趁着谢珩低头翻阅另一份卷宗,我几乎是鬼使神差地,飞快地伸出手指,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那碟糖蒸酥酪的边缘,小心翼翼地刮下了一小点凝乳。
指尖触到冰凉滑腻的瞬间,一丝微弱的甜意弥漫开来。然而,
还未等我那颗悬到嗓子眼的心落回原处,一声极轻的叹息便在我头顶响起。“心神不宁,
何以运笔?”我触电般缩回手,指尖还残留着那点甜腻的冰凉。猛地抬头,
正对上谢珩俯视的目光。他不知何时已放下了卷宗,正静静地看着我,脸上依旧没什么表情,
只是那双深眸里,似乎掠过一丝极淡的、难以言喻的无奈。他伸出手,并非责备,
而是直接端起了那碟糖蒸酥酪,稳稳地放在了我面前的书案上,
紧挨着我临摹失败的那张废纸。细腻的乳酪在碟中轻轻晃了晃,
几粒金黄的酒酿桂花微微颤动。“既如此,”他淡淡开口,声音听不出情绪,
目光却重新落回我临摹的那幅狂草上,手指点了点一处明显失力的转折,“此处,
笔锋当再利三分。赵乾此人,外粗内细,字里行间的狠厉,是他刻意示人的铠甲,
亦是破甲之锥。”我盯着那碟近在咫尺的酥酪,脸颊滚烫,羞愧与那点可怜的食欲交织翻腾,
几乎要将我撕裂。他洞悉一切,却从不点破,只是用这种无声的方式,
将我的弱点连同那点渴望,一起**裸地摊开在这张书案上,逼着我直视,
逼着我在这份难堪中,继续去描摹那些足以致命的笔锋。---暮春的空气里,
花香甜得发腻。四皇子萧玦在府中设下赏花宴,遍邀京中才俊,帖子自然也送到了国子监。
明眼人都知,太子新丧,储位空悬,这场风雅不过是另一场不见硝烟的试探。
我被裹挟在人群里,穿着属于“苏明远”的襕衫,只觉得那布料粗糙地摩擦着皮肤,
带来一阵阵刺痒的不适。谢珩在我斜前方几步之遥,月白的澜衫在姹紫嫣红中显得格外清寂。
他走得慢,背影单薄,偶尔传来一两声压抑的低咳,很快又被他强行咽下,
只余下肩头微微的颤动。四皇子府邸华美非常,亭台楼阁,曲水流觞。然而空气里浮动的,
除了花香,更有一种紧绷的、粘稠的暗流。投向谢珩的目光,有忌惮,有窥探,
更多的是毫不掩饰的冰冷审视。他就像行走在狼群中的病鹤,每一步都踩在悬崖边缘。
席设在水榭,四面环水,唯有两条曲折的回廊相连。丝竹声起,觥筹交错。我食不知味,
目光始终无法从谢珩身上移开。他坐在下首,位置并不显眼,却仿佛是整个漩涡的中心。
他吃得极少,面前精致的菜肴几乎未动,只偶尔端起清茶啜饮一口,
苍白的唇色在碧绿茶汤的映衬下,更显脆弱。四皇子萧玦坐在主位,一身绛紫蟒袍,
面容英挺,嘴角噙着温和的笑意,眼神却锐利如鹰隼。他谈笑风生,目光却不时掠过谢珩,
带着一种猫捉老鼠般的玩味。席间话题渐渐从诗词歌赋,不动声色地引向朝局,
引向太子旧事。“谢先生,”萧玦的声音带着笑意,却像淬了冰,“听闻太子在时,
对先生言听计从,倚为臂膀。可惜……天不假年啊。”他端起金樽,遥遥一敬,话锋陡转,
“不知先生日后,有何高就?”满座瞬间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谢珩身上。
气氛凝滞得如同冻结的湖面。谢珩缓缓放下茶盏,动作从容。他抬眸,迎向萧玦审视的目光,
唇边甚至浮起一丝极淡的、近乎于无的笑意。“殿下谬赞。”他的声音不高,
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带着惯有的微哑,“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太子殿下知遇之恩,
珩不敢忘。至于将来……唯愿潜心学问,不负圣贤教诲。”滴水不漏。
将“忠君”二字顶在前面,既表明了对旧主的立场,又将萧玦隐含的招揽之意轻巧拨开,
最后归隐于学问,姿态谦卑却带着疏离的拒绝。萧玦脸上的笑意淡了几分,
眼底的阴鸷一闪而逝。他放下酒杯,指节在案几上轻轻敲击,发出笃笃的轻响,
每一下都敲在人心上。席间的暗流陡然变得汹涌,无形的压力沉甸甸地压下。就在这时,
变故突生!一名捧着热汤上菜的侍婢,不知怎地脚下一个趔趄,惊呼声中,
手中那滚烫的汤盆竟直直朝着谢珩的方向倾覆过去!滚热的汤汁飞溅!“小心!
”席间有人失声惊呼。电光石火间,我离得最近,身体先于意识做出了反应。几乎是本能地,
我猛地起身,伸手狠狠推了谢珩一把!他本就病弱,猝不及防之下被我推得向旁边踉跄扑倒。
“哗啦——!”滚烫的汤汁尽数泼洒在我方才所坐的矮几和蒲团上,热气蒸腾,
溅起的油星有几滴落在我手背上,瞬间灼起一片刺痛的麻。水榭里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的目光,惊愕、探究、审视,齐刷刷地钉在我身上,如同芒刺。我僵在原地,
手背上的刺痛远不及心头那瞬间涌上的恐惧——我暴露了!在众目睽睽之下,
对一个“男子”做出了如此逾矩的、近乎护卫的动作!萧玦的目光如同冰冷的蛇信,
瞬间锁定了我。那眼神里充满了玩味和一丝了然的锐利,仿佛终于撕开了猎物最后一层伪装。
“苏公子……”萧玦慢悠悠地开口,打破了令人窒息的沉默,每一个字都带着千斤的重量,
“好敏捷的身手,好快的心意。”他顿了顿,嘴角勾起一个意味深长的弧度,“对谢先生,
倒是……关切得很呐。”我脸色煞白,喉咙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死死扼住,发不出半点声音。
完了。彻底完了。巨大的恐惧如同冰冷的潮水,瞬间将我淹没。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当口,
身后传来一阵压抑不住的、撕心裂肺的咳嗽声。是谢珩。他被人搀扶着,艰难地坐直了身体。
方才的推搡和惊吓似乎彻底引爆了他体内的沉疴。他咳得整个身体都在剧烈颤抖,
脸色由白转青,额角青筋暴起,仿佛下一刻就要将心肺都咳出来。他用一方素帕死死捂住嘴,
那帕子很快被染上刺目的深红。剧烈的咳嗽声暂时转移了所有人的注意,
也替我挡下了萧玦那迫人的审视。终于,咳声渐歇,谢珩喘息着,气息微弱得如同风中残烛。
他抬起眼,那双深潭般的眸子此刻布满血丝,带着一种病态的浑浊和疲惫。他看向萧玦,
声音破碎不堪,
每一个字都带着沉重的喘息和压抑不住的咳嗽余音:“殿下……咳咳……苏公子年少莽撞,
受惊之下……咳咳咳……举止失措……惊扰了殿下……还望……恕罪……”他艰难地说完,
又猛地低头,又是一阵剧烈的呛咳,帕子上的血色更深了。
萧玦看着谢珩那副随时可能断气的模样,
眼底的审视和怀疑似乎被一丝不易察觉的嫌恶和一丝“果然如此”的笃定取代。
一个病得快死的谋士,一个被吓破了胆、举止失当的毛头小子……似乎不值得他再多费心思。
他挥了挥手,脸上重新挂上那副温和的假面,语气带着施舍般的宽容:“罢了,一场意外。
谢先生保重身体要紧。来人,扶谢先生和苏公子下去更衣歇息。”危机暂时解除。
我浑身冰凉,指尖还在不受控制地颤抖。被人引着退下时,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谢珩。
他正被人搀扶着起身,步履蹒跚,身形佝偻得厉害。就在他经过我身边时,
那宽大的袖袍极其轻微地、几乎难以察觉地拂过我的手腕。袖袍之下,
一个冰冷、坚硬、细小的东西,悄然塞进了我汗湿的掌心。我的心脏猛地一缩。
借着转身的遮掩,我用指尖飞快地捻了一下那物——是一个小小的、蜡封的圆丸。
---那场惊心动魄的赏花宴,如同一场混乱而漫长的噩梦。回到国子监那间狭小的号舍,
冷汗才后知后觉地浸透了里衣。窗外是沉沉的夜,远处偶尔传来几声梆子响,
更衬得屋内死寂。我摊开掌心,借着窗外透进的微弱月光,凝视着那颗小小的蜡丸。
指尖因为用力而微微发白。轻轻一捻,脆硬的蜡壳碎裂,
露出里面卷得极紧的一小片薄如蝉翼的素绢。心提到了嗓子眼。小心翼翼地展开,
借着月光艰难辨认。绢上只有寥寥数行,墨色极淡,
是谢珩那特有的、带着一丝病骨嶙峋却力透纸背的字迹:“两日后,申时三刻,
城南‘忘忧’书肆。”“赵乾常购前朝野史,阅后批注于扉页,字迹潦草,然习惯未改。
留意其‘捺’笔末梢回勾之角度,及句读浓墨点之位置。”“阅毕即焚,勿留片纸。
”指令清晰,目标明确,甚至精确到了对方难以察觉的书写陋习。
一股寒意顺着脊椎悄然爬升。他早就在布局,甚至算准了四皇子府上的这场“意外”,
算准了我会被卷入漩涡中心,算准了……我需要一个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
一个深入虎穴的投名状。两日后的申时三刻,城南“忘忧”书肆。
我穿着最不起眼的青布直裰,混在寥寥无几的顾客中。书肆里弥漫着旧纸和灰尘的气息。
掌柜是个须发皆白的老者,眼皮耷拉着,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角落的书架旁,
一个穿着藏青绸衫、身形微胖的中年人,正背对着门口,低头翻看着一册书。背影很熟悉,
正是四皇子府上的幕僚,赵乾。时间仿佛被拉长。我佯装挑选书籍,
目光却死死锁住赵乾的动作。他拿起一册书,翻了几页,眉头紧锁,似乎颇为不满。
他掏出随身的炭笔,在书的扉页空白处飞快地写了些什么。动作很急,
带着他惯有的那股子暴躁劲儿。写完,他啪地合上书册,随手丢回架上,转身就往外走,
步履匆匆。就是现在!在他身影消失在门口的同时,我如同离弦之箭,几步抢到那个书架前。
心脏在胸腔里疯狂擂动,几乎要破膛而出。指尖带着细微的颤抖,
准确地抽出那本被赵乾丢下的书——一本破旧的《前朝秘闻录》。翻开扉页。果然!
几行潦草的炭笔字迹跃入眼帘,是对书中某段记载的鄙薄批语:“一派胡言!
弘景帝何曾……此处大谬!”目光如同最精密的刻刀,
瞬间捕捉到谢珩提示过的细节:那个“谬”字的捺笔末端,
带着赵乾标志性的、用力回勾的锐角,几乎要划破纸页!而每一处句读停顿,
都用炭笔重重地点下了一个浓黑的圆点,位置精准,显露出他急躁专断的本性。成了!
巨大的狂喜和更深的恐惧交织着冲上头顶。我飞快地扫视四周,无人注意。
迅速将那几页关键的批语,连同赵乾那极具个人特色的笔锋转折,死死烙印在脑海里。然后,
毫不犹豫地将那本《前朝秘闻录》塞回书架深处。转身离开书肆,融入街市的人流,
直到走出两条街,拐进一条无人的窄巷,我才敢停下来,背靠着冰冷粗糙的墙壁,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冷汗浸透了后背,夜风吹过,带来一阵刺骨的寒意。任务完成了,
可心头那块巨石,却压得更沉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
我已经亲手将自己绑上了谢珩那艘行驶在惊涛骇浪中的孤舟。前路,是深不见底的权谋泥潭。
---藏书楼顶层的小室,空气依旧凝滞着旧纸和墨香。
谢珩听完我压低声音、几乎带着颤音的回报,脸上并无半分喜色。他端坐在书案后,
只是微微颔首,指尖习惯性地在案上轻叩了一下,发出笃的一声轻响。“好。
”他只说了这一个字。旋即,他摊开一张与四皇子府邸常用笺纸极其相似的素笺。研墨,
润笔,动作依旧带着那份病弱的迟缓,落笔时却稳如磐石。他并未直接书写,
而是抬眸看向我,眼神里是一种不容置疑的命令。“我说,你写。”声音低沉而清晰。
我心头一紧,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镇定下来,拿起另一支细狼毫,蘸饱了墨。指尖的颤抖,
在接触到冰凉的笔杆时,似乎平息了一些。“殿下钧鉴:”谢珩的声音在寂静的室内流淌,
冰冷得不带一丝情感,“前日密探自北境传讯,戍边大将李崇山,似与废太子余孽暗通款曲,
其麾下三千亲兵,动向诡秘,恐有异动。更查得,李崇山私藏前朝龙纹金矿所铸甲片百副,
匿于其老家颖州祖宅地窖之中。此獠手握重兵,心怀叵测,若不早除,
必成大患……”每一个字,都像淬了毒的冰锥。伪造赵乾的笔迹,
构陷手握重兵的戍边大将李崇山通敌、藏匿僭越之物!这已不仅仅是伪造文书,
这是要借四皇子萧玦之手,掀起一场滔天血浪!冷汗瞬间浸湿了我的掌心。“注意,
”谢珩的声音打断了我内心的惊涛骇浪,“‘李’字末笔,顿挫要狠,‘山’字三竖,
最后一竖须拖长,带出戾气。句读之点,墨要浓,力透纸背,显其杀伐决断。”我咬着下唇,
几乎要将唇瓣咬出血来。竭力回忆着在书肆看到的那几笔批注的神韵,
调动起全身的力气去模仿那份狠厉。笔锋落在纸上,沙沙作响。写那个“李”字最后一横时,
我刻意加重顿笔,笔锋几乎戳破纸背;“山”字的最后一竖,我用力拖曳,
带着一股蛮横的戾气;每一个句读停顿处,我都狠狠杵下笔尖,留下一个浓黑如墨的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