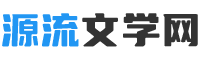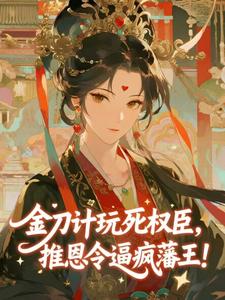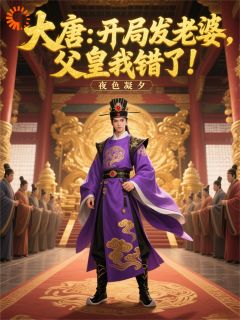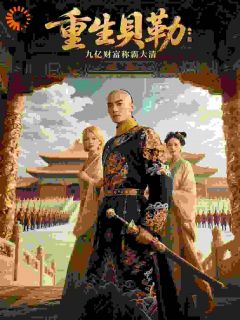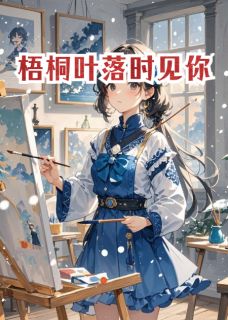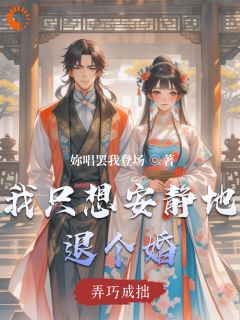
苏文是个行动派。
前世在公关行业摸爬滚打多年,他深知一个道理:危机发生后的黄金24小时,是决定舆情走向的关键。拖延和犹豫,只会让事态失控。
虽然他现在面临的不是品牌形象危机,而是实打实的生存危机,但原理是相通的。他必须抢在皇帝、秦家以及全京城的百姓对他“驯虎勇士”的新人设形成固定印象之前,主动出击,彻底打破这个预期。
他制定的A计划,名为“社会性死亡”,核心策略只有两个字——自污。
既然皇帝和世人觉得他“品性纯良,才思敏捷”,那他就反其道而行之,亲手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品性败坏,粗鄙不堪”的烂人。
一个男人,在古代社会最看重什么?无非是“德”与“才”。
德行方面,暂时不好操作,需要时间。但“才”,尤其是对于一个书生而言,却是可以速成的,当然,也可以速毁。
他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全京城的人都相信,他苏文,根本不是什么有才学的秀才,而是一个欺世盗名、胸无点墨的草包。
一个连“才”都没有的废物,怎么可能配得上战功赫赫的将军之女?秦家但凡要点脸面,必然会主动向皇帝请辞这桩婚事。皇帝为了安抚肱骨之臣,大概率也会顺水推舟。
计划通!
苏文为自己缜密的逻辑和完美的行动方案点了个赞。
他将行动地点,选在了京城文人骚客最爱聚集的“望江楼”。这里是舆论的发酵地,是八卦的集散中心,更是文人“人设”的塑造场和“翻车”现场。在这里搞出点动静,不出半日,就能传遍整个京城。
至于行动的“道具”,他花了一个时辰,精心“创作”了一首诗。这首诗,是他融合了前世网络上所有“口水歌”、“打油诗”的精髓,呕心沥血之作。其核心特点就是:毫无平仄,毫无对仗,毫无意境,直白得像一杯白开水,粗俗得像村口的叫骂。
他相信,这首诗一出,足以摧毁任何一个读书人视若生命的“文名”。
第二天午后,望江楼最是热闹。
三楼临窗的位置,早已坐满了衣冠楚楚的文人学士。他们或高谈阔论,或吟诗作对,空气中飘着酒香和墨香,一派风雅。
苏文揣着他的“大杀器”,一瘸一拐地走了进来。
他的出现,立刻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
“快看,那不是苏文吗?”
“就是那个被魏公子抢了未婚妻,又被陛下赐婚给秦家‘母老虎’的苏文?”
“听说他昨日得了圣旨,竟面不改色,还跟传旨的李公公探讨婚礼用度,当真是有几分胆色。”
“哼,我看是吓傻了吧!娶了秦如虎,他那小身板,怕是经不起一拳。”
议论声不高不低,刚好能传进苏文的耳朵里。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要让所有人都看着,见证他这个“文坛新星”的陨落。
苏文径直走到大堂中央,叫了一壶最烈的烧刀子。他故意做出豪迈的样子,给自己满上一大碗,咕咚咕咚灌下去一半。辛辣的酒液顺着喉咙烧下去,呛得他眼泪都流了出来。
在众人惊异的目光中,他一把抹去嘴角的酒渍,借着那股冲上头顶的酒劲,一脚踩在了旁边的椅子上,动作粗野无比。
“咳咳!”他清了清嗓子,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满堂宾客大喝一声:“诸位!静一静!”
嘈杂的望江楼,瞬间安静了下来。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聚光灯一样打在他身上,有好奇,有鄙夷,有期待,也有纯粹的幸灾乐祸。
苏文很满意这种万众瞩目的感觉。他环视一周,用一种带着几分醉意的、悲愤交加的语气朗声道:“在下苏文,遭逢大变,心中郁结,有感于怀,偶得一首拙作,还请诸君……品鉴!”
来了!重头戏来了!
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都想听听,这位经历了大悲大喜,被传得神乎其神的苏秀才,会作出怎样的惊世之篇。是自怨自艾?还是愤世嫉俗?
苏文深吸一口气,将胸中的郁闷与酒气一同喷薄而出,用一种近乎嘶吼的腔调,开始朗诵他那首足以名留“黑历史”的旷世杰作:
“望江楼上望江流,
江水滔滔向东流!
人生在世不得意,
不如回家烤红薯!”
……
诗一出口,石破天惊。
整个望江楼,陷入了一种诡异的、死一般的寂静。
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所有人都像被施了定身法一般,保持着各种各样惊愕的表情。有的张大了嘴,能塞进一个鸡蛋;有的端着酒杯,手悬在半空,忘了喝;有的甚至被呛到,剧烈地咳嗽起来,却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
苏文看到这一幕,心中狂喜。
成了!
他知道,这首诗的“杀伤力”有多大。它就像一颗精神炸弹,精准地炸毁了在场所有文人对于“诗”这个概念的一切美好想象。
没有平仄?没有对仗?没有意境?这些都算了。
“不如回家烤红薯”?!
这是何等粗鄙、何等直白、何等……不登大雅之堂的句子!这根本不是诗,这是街边三岁孩童的顺口溜!
苏文几乎能听到他们内心崩溃的声音。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明天京城各大报纸(如果有的话)的头条——《震惊!新晋文坛偶像苏文竟是草包,望江楼当众出丑!》、《从天才到废柴:苏文的陨落只用了一首诗的时间》。
然后,秦家将军府的大门会被踏破,无数人会劝说秦将军,万万不可将女儿嫁给这等不学无术之徒。
“哈哈哈……”苏文仰天长笑,笑声中充满了“计谋得逞”的快意。他将碗中剩下的酒一饮而尽,然后把碗重重地摔在地上,摔得粉碎。
他要用这决绝的姿态,为自己的“社会性死亡”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他转身,准备在一片鄙夷和嘲讽的目光中,潇洒离去。
然而,他没有等到预想中的嘲讽。
就在他转身的瞬间,一个苍老而颤抖的声音,从角落里响了起来,声音不大,却像一道惊雷,在死寂的大堂中炸响。
“好!好一个‘不如回家烤红薯’!”
苏文的脚步,猛地顿住。他愕然回头。
说话的,是一位须发皆白、身穿素色长袍的老者。他正被两个学生搀扶着,颤颤巍巍地站起身,一张老脸因为过度激动而涨得通红。
苏文不认识他,但在场的其他人,却都认识。
“是郑老先生!”
“郑文宗!他怎么会在这里?”
“我的天,郑老先生已经三年不曾公开评议诗文了!”
郑玄,字文宗,大徽王朝硕果仅存的文坛泰斗,当朝太子的老师。其在文坛的地位,如同定海神针,一言可兴邦,一语可废人。
苏文的心里,咯噔一下,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只见郑玄颤抖地指着苏文,浑浊的老眼中,竟闪烁着晶莹的泪光。他对着满堂依旧处于呆滞状态的宾客,用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语气,痛心疾首地说道:
“尔等竖子!只知平平仄仄,只懂对仗工整,却未见此诗中‘返璞归真,大巧不工’的无上境界!简直是买椟还珠,愚不可及!”
满堂哗然。
苏文懵了。返璞归真?大巧不工?老先生,你是不是喝多了?
郑玄没有理会众人的震惊,他像是打开了话匣子,自顾自地开始了他的“阅读理解”。
“‘望江楼上望江流,江水滔滔向东流。’此句看似浅白,实则气魄何其雄浑!望江楼,京城第一楼,天下名利之所在也!江水东流,光阴易逝,不可挽留!开篇即点明,这世间一切功名利禄,不过是过眼云烟,终将逝去!”
“有……有道理啊!”人群中,开始有人窃窃私语。
苏文的嘴角开始抽搐。
郑玄越说越激动,他挣开学生的搀扶,向前走了两步,目光灼灼地盯着苏文:
“而最妙,最绝,最是神来之笔的,便是这最后一句——‘人生在世不得意,不如回家烤红薯’!”
“何为‘烤红薯’?那是寻常百姓家,冬日里最朴素的温暖,是人间烟火,是安逸平和!苏小友遭逢大变,未婚妻被人所夺,反被赐婚给那……咳,那秦将军之女。此等大起大落,非常人所能承受。换做尔等,怕是早已心灰意冷,或愤世嫉俗,或寻死觅活!”
“然苏小友不然!他站在此地,看尽这满楼繁华,看穿了这世间名利,最终发出了这振聋发聩的呐喊!功名利禄算什么?权贵之争算什么?人生真正的意义,不就藏在那一只小小的、热气腾腾的烤红薯之中吗?”
“这!不是诗!这是‘道’!是以大俗喻大雅,看破红尘、回归本真的大道之言啊!”
一番慷慨激昂的陈词,说得是掷地有声,荡气回肠。
整个望江楼,再次陷入了寂静。但这一次,不再是鄙夷和嘲讽的寂静。
所有人的眼神,都变了。
他们看着苏文,那眼神中充满了震撼、敬佩、以及对自己刚才“有眼不识泰山”的深深愧疚。
“原来如此!我等愚钝!竟未解其中深意!”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苏兄,不,苏先生,真乃我辈楷模!”
“不畏强权,不慕名利,大起大落之后,竟有如此超然的感悟!这等风骨,我辈望尘莫及!”
赞誉声,如潮水般涌来。
苏文站在大堂中央,如遭雷击,浑身僵硬,手脚冰凉。他张了张嘴,想解释点什么。
想说:“各位,冷静!你们误会了!我真的只是想回家烤红薯!”
但看着郑文宗那双写满了“我懂你”的眼睛,看着周围那些文人学士狂热而崇拜的目光,他知道,一切都晚了。
他精心策划的A计划“社会性死亡”,在郑文宗这位“顶级脑补官”的权威解读下,不仅彻底破产,还朝着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一路狂飙,撞穿了南墙。
他不仅没有实现“社会性死亡”,反而,在一日之内,以一种他自己都无法理解的方式……
一诗封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