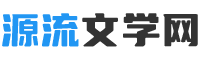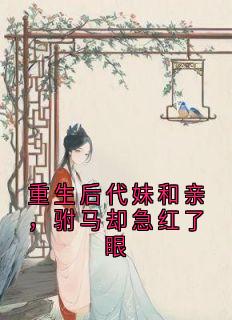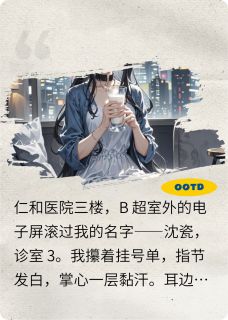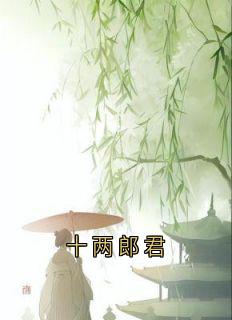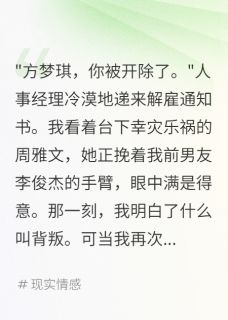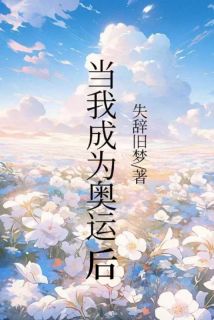林砚第一次注意到苏晚,是在高二开学那天的暴雨里。
她抱着一摞被淋湿的画纸站在教学楼门口,校服领口洇出淡淡的蓝,像宣纸上晕开的墨。
他撑着伞从她身边经过时,听见她小声数着画纸上晕染的色块,尾音带着点没睡醒的黏糊。
那天之后,他的视线总像被磁石牵引。她在画室里咬着铅笔发呆时,
阳光会顺着窗棂爬上她的发梢,在画板上投下细碎的金斑;她抱着作业本穿过走廊时,
帆布鞋踩在地面发出轻快的嗒嗒声,像在敲他骤然变快的心跳;她在晚自习时偷偷写日记,
笔尖划过纸页的沙沙声,总能盖过他耳机里的白噪音。他开始不动声色地靠近。
知道她总忘记带伞,他会在天气预报说有雨的日子,
把折叠伞藏在画室的储物柜里;知道她喜欢靠窗的位置,他会提前半小时到教室,
假装不经意地坐在斜后方;知道她画水彩时总缺赭石色,他会在美术用品店买两管,
悄悄塞进画室的公用颜料盒。这些隐秘的心思像藤蔓,在他十七岁的夏天疯狂生长。
他数着她笑起来时眼角的痣,记着她喝奶茶时只加三分糖,甚至能从一群人的脚步声里,
精准分辨出属于她的那一串。可每当她转过身朝他看来,他总会立刻低下头,
假装在看课本上的公式,耳尖却比谁都烫。苏晚对他是不同的。她会笑着问他数学题,
指尖偶尔擦过他的笔杆;她会把没吃完的橘子塞给他,
说“你好像总不怎么吃水果”;她会在体育课自由活动时,举着相机给他拍投篮的背影,
说“这张光影特别好”。这些瞬间像投入湖心的石子,在他心里漾开一圈圈甜,
却又很快被更深的恐慌淹没——他怕这些只是她待人温和的常态,
怕自己的心动不过是自作多情。高三的秋天,学校举办艺术节。苏晚要展出一幅水彩,
画的是教学楼后的银杏树。开展前一天,她抱着画框在走廊里来回踱步,眉头拧成个小疙瘩。
“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她喃喃自语,忽然抬头看向林砚,“你帮我看看好不好?
”画框被递过来时,他的手指不小心碰到她的。那点温热像电流,瞬间窜遍全身。
他盯着画布上金黄的银杏叶,喉咙发紧,半天才挤出一句:“挺好的。
”“可是……”她咬着唇,“我想加只猫在树下,但是不知道怎么画才自然。”那天晚上,
林砚在画室待到凌晨。他翻遍了所有的画册,对着网上的图片一遍遍练习,
终于画出一只蜷缩在银杏叶里的橘猫,眼神慵懒又温顺。他把画好的猫剪下来,
小心翼翼地贴在苏晚的画作角落,像给她的世界偷偷加了个秘密符号。艺术节开展那天,
苏晚站在自己的画前,惊喜地指着那只猫转头找他:“林砚,你看!是不是很神奇?
”他站在人群外,看着她眼里的光,忽然觉得所有的熬夜都值得。
可当她穿过人群朝他走来时,他却鬼使神差地转身,躲进了楼梯间。
他听见她在身后喊他的名字,声音带着点困惑。可他不敢回头,
怕自己眼里的汹涌会泄露秘密,更怕看到她恍然大悟后,礼貌却疏离的眼神。
冬天来得猝不及防。苏晚要转学的消息,是他从班主任那里听到的。那天下午,
他在画室待了很久,看着她常坐的位置空着,颜料盒里的赭石色还剩半管,
储物柜里的伞安静地躺着,忽然觉得心里像被掏走了一块。他写了整整三页的信,
字字句句都浸着没说出口的喜欢。可直到苏晚离开那天,那封信也没能送出去。
他站在教学楼上,看着她抱着纸箱坐进出租车,车窗外的雪花落在她的发间,像撒了把碎钻。
车开走的时候,他看见她从车窗里探出头,似乎在朝楼上望,可他下意识地缩到了墙后。
后来的很多年,林砚再也没见过苏晚。只是偶尔整理旧物时,会翻到那本没送出去的画集,
最后一页夹着片干枯的银杏叶,是他当年从她画里的那棵树下捡的。有次同学聚会,
有人提起苏晚,说她现在成了小有名气的插画师,画里总少不了一只橘猫。
有人笑着问:“你们还记得她高三那幅银杏画吗?角落里突然多出来的猫,
当时谁都不知道是谁画的。”林砚端着酒杯的手顿了顿。他想起那天躲在楼梯间时,
隐约听见苏晚和朋友说:“我觉得是林砚画的,他昨天看画的时候,眼神好奇怪。
”窗外的雨又下了起来,像极了他们初见那天。林砚望着玻璃上自己模糊的倒影,忽然明白,
有些心动一旦错过了时机,就会像被雨水打湿的画纸,再好的色彩,
也只能洇成一片模糊的痕。而那句藏在了他一个人的兵荒马乱,在无数个寂静的夜里,
反复潮起又潮落。林砚再次见到苏晚,是在七年后的画展上。
展厅中央的巨幅水彩前围了不少人,画里是漫山遍野的绣球花,蓝紫色的花瓣间卧着只橘猫,
尾巴尖沾着点嫩黄的花蕊。他站在人群外,看着署名栏上“苏晚”两个字,
指节无意识地蜷了蜷。有人轻轻撞了下他的胳膊:“林先生也是来看苏晚老师的展吗?
她的画总带着种……说不出的温柔。”他嗯了一声,视线却像被钉在画布上。
那只橘猫的眼神,和当年他贴在银杏画角落的那只几乎一模一样。“苏老师今天会来的,
”旁边的女生兴奋地翻着展览手册,“听说这幅《绣球与猫》是她的新作,
灵感来自高中时的一幅旧画呢。”林砚的心跳漏了一拍。他下意识地想转身离开,
脚却像灌了铅。就在这时,人群忽然骚动起来,有人低声说“苏晚来了”。
他顺着众人的目光望去,看见她穿着米白色的风衣,正笑着和策展人交谈。头发留长了,
挽成松松的发髻,露出光洁的额头,可笑起来时眼角的痣,还和十七岁时一样。
她似乎察觉到他的目光,转过头来。四目相对的瞬间,林砚像被施了定身咒,
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眼里闪过一丝惊讶,随即是礼貌的浅笑。“林砚?”她朝他走过来,
声音比记忆里沉了些,却依旧带着清润的调子,“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颤,手心里全是汗。“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
”她指了指他手里的展览手册,“你也喜欢水彩?”“嗯,随便看看。”他胡乱应着,
视线落在她颈间的项链上——那是枚银杏叶形状的银饰,叶尖微微卷曲。“这幅画,
”她转过身,望着那片绣球花海,“其实是补画给高三那幅银杏的。当年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后来才想明白,是少了个能一起看画的人。”林砚的喉结动了动,没敢接话。“说起来,
”她忽然侧过头看他,眼里带着点探究,“当年我那幅银杏画里的猫,是你画的吧?
”他猛地抬头,撞进她含笑的眼睛。“那天我在楼梯间捡到了一小块画纸碎屑,”她轻声说,
“上面有赭石色的颜料,和你总用的那个牌子一样。”原来她什么都知道。
心脏像是被什么东西攥紧了,钝痛沿着血管蔓延开来。他张了张嘴,
那些在无数个深夜里排练过的句子,此刻却堵在喉咙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找过你好几次,”她的声音低了些,“那天你躲在楼梯间,我喊你,你没回头。
”“我……”“后来我转学临走前,”她打断他,指尖轻轻摩挲着颈间的银杏项链,
“在画室的储物柜里看到了一把折叠伞,伞柄上刻着你的名字缩写。
还有颜料盒里多出的赭石色,靠窗的座位上总留着的空位……”她顿了顿,抬眼看向他,
眼里蒙着层薄薄的雾:“林砚,那时候你是不是……”“不是的。”他几乎是脱口而出,
说完就恨不得咬掉自己的舌头。苏晚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随即又恢复了平静,
只是眼底的光暗了下去。“是吗?”她轻轻点头,“可能是我想多了。”这时,
有工作人员喊她过去接受采访。她对他抱歉地笑了笑:“我先过去了。”“好。
”看着她转身的背影,林砚忽然想起高三那个下雪的午后。他站在教学楼上,
看着她坐的出租车越来越远,其实她探出头时,
他看得清清楚楚——她手里攥着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上面似乎写着什么。后来他才知道,
那天她在画室等了他整整一节课,手里拿的是给她的回信,问他愿不愿意周末一起去看画展。
采访结束后,苏晚被一群粉丝围住签名。林砚站在角落,看着她耐心地在画册上写下名字,
忽然觉得有些东西,从十七岁那个躲在楼梯间的下午开始,就已经错过了。他悄悄退出展厅,
外面不知何时下起了小雨。他摸了摸口袋,才想起今天没带伞。雨滴落在脸上,冰凉的,
像极了当年苏晚塞给他的橘子皮上的露水。手机忽然震动了一下,
是条陌生号码发来的短信:“其实那天在楼梯间,我想告诉你,我画银杏的时候,
总觉得树下少了个站着的人。”林砚站在雨里,看着那条短信,忽然蹲下身,捂住了脸。
迟来的告白像潮水,终于在七年后将他彻底淹没,可潮水里漂浮的,全是再也抓不住的过往。
他想起她画里的绣球花,想起她颈间的银杏叶,想起那只始终陪伴的橘猫。
原来那些年的心动从不是单向的,只是他的胆怯,让两束本该交汇的光,
最终只能在各自的轨道上,寂寞地亮着。雨越下越大,模糊了展厅的玻璃门。
他好像又看见十七岁的苏晚,抱着画纸站在教学楼门口,数着晕染的色块,而他撑着伞,
却始终没敢走到她身边。有些暗恋,注定只能是一场无声的潮,涨起来时汹涌澎湃,退去后,
只留下满地狼藉的遗憾。林砚在雨里站了很久,直到手机屏幕暗下去,映出他通红的眼眶。
那条短信像根细针,轻轻挑破了他用七年时间筑起的堤坝,
所有被压抑的悔意顺着裂缝涌出来,漫过心口。他最终还是没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