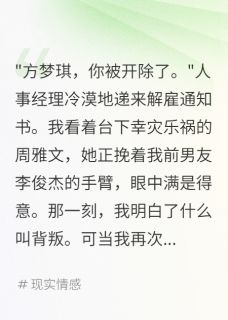残阳如血,将城郊破庙的断壁残垣染上一层诡谲的金红。宋一汀立在阴影里,
指尖一枚精巧的铜制香丸被捏得温热。她心跳如擂鼓,
目光死死锁住庙门——她在等“离十六”,那个名动江湖、神秘莫测的残江月大当家。
母亲周雪怡的催逼、尚书府令人窒息的规训,都让她决定剑走偏锋。生米煮成熟饭,
是她能想到最快摆脱家族掌控、抓住自己想要之人的法子。脚步声由远及近,
一道颀长的身影裹着暮色踏入破庙门槛,玄衣劲装,脸上正是离十六标志性的半截面具。
时机正好!宋一汀指尖一弹,香丸无声滚落香炉,一缕甜腻得发齁的烟雾袅袅升起。
“十六爷,”她款步上前,声音刻意放得柔婉,眼底却燃烧着孤注一掷的火焰,
“您要的东西,带来了。”她故意拖延着时间,诉说着自己如何仰慕他的神秘与强大,
如何在深闺中向往他刀尖行走的自由。烟雾弥漫开来,
她看到“离十六”的身形似乎晃了一下。药力发作了!宋一汀再不犹豫,欺身上前,
伸手便去解他腰间的束带。指尖刚触到冰凉的皮革,手腕却被一股大力猛地攥住!
她惊愕抬头,只见对方眼中闪过一丝锐利清明,全无中迷香的混沌。电光火石间,
两人推搡纠缠,她奋力一挣,手肘无意中狠狠撞上对方面门——“啪嗒!
”那半截面具应声而落,砸在布满灰尘的地上。露出的,
是南珩那张俊美却写满惊愕与尴尬的脸!“怎么是你?!”宋一汀失声尖叫,
羞愤瞬间烧红了她的耳根。破庙腐朽的木门在此时“砰”地被撞开,刺眼的火把光涌了进来,
将庙内照得亮如白昼。宋一梦冲在最前,满脸焦急,她身后,是押解着真正上官鹤的楚归鸿,
以及大队千羽军士兵。无数道目光如同芒刺,
聚焦在衣衫不整的宋一汀和脸色铁青的南珩身上。空气死寂。宋一汀的目光越过南珩的肩膀,
猛地钉在人群后方那个被反剪双手的白衣身影上——上官鹤。他低垂着头,看不清表情,
但那紧抿的唇线和绷紧的下颌,泄露了此刻的狼狈与难堪。
一股被命运戏弄的滔天怒火和被当众撞破的羞耻感,瞬间冲垮了宋一汀的理智。
她猛地从袖中掏出一个沉甸甸的锦绣钱袋,用尽全身力气,狠狠砸向上官鹤!
钱袋撞在他胸口,又无力地滚落在地,扬起一小片灰尘。“看够了吗?
”宋一汀的声音冰冷刺骨,带着一种刻意为之的、淬了毒的轻蔑,“阴沟里的潮虫,
也配我宋二**追?拿着你的赏钱,滚!”她一字一顿,清晰地传入在场每一个人的耳中,
“别再让我看见你,脏眼。”上官鹤的身体几不可察地晃了一下。他没有抬头,
也没有去捡那个钱袋。楚归鸿的手下粗暴地推搡了他一把,他踉跄着转身,
沉默地、近乎仓皇地被押离了这片令他窒息的地方。白色的衣角消失在庙门外浓重的夜色里,
像一片被骤然撕碎的月光。尚书府的西厢院连着几日都笼罩在低气压中。
宋一汀砸了母亲送来的所有锦缎首饰,对父亲宋聿德的苦口婆心充耳不闻。
她把自己关在房里,用暴躁掩饰着心底深处那丝挥之不去的刺痛——上官鹤被她当众羞辱后,
竟真的如人间蒸发,连残江月都不再踏足。“二**,夫人…夫人又请了南瑞殿下过府!
这次还带了贵妃娘娘的赏赐,说是…说是商议纳采之期!”小丫鬟战战兢兢地在门外禀报,
声音带着哭腔。最后一丝侥幸被掐灭。家族终于等不及了,要彻底把她当作巩固权势的棋子,
塞给那个她看一眼都觉得油腻的南瑞!宋一汀抓起桌上一壶冷透的烈酒,仰头便灌。
辛辣的液体灼烧着喉咙,也烧毁了仅存的理智。她踢开房门,
无视身后母亲周雪怡气急败坏的呼喊和南瑞故作深情的目光,
跌跌撞撞地冲出了尚书府森严的大门。去哪里?残江月?对,去残江月!那个**上官鹤,
一定躲在那里!夜风带着寒意,吹不散她浑身蒸腾的酒气。凭着模糊的记忆和一股蛮劲,
她竟真的摸到了残江月会馆那偏僻的后巷。月光清冷,照着一地狼藉的杂物。
她扶着冰冷的墙壁喘息,视线模糊,胃里翻江倒海。一个熟悉的白影就在这时,
幽灵般从角落一堆废弃的木箱后闪出,似乎正要悄然离去。是上官鹤!他看起来清瘦了些,
惯有的那点漫不经心的笑意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眉宇间一片沉寂的疲惫。“站住!
”宋一汀用尽力气嘶喊,声音破碎沙哑。她像只失控的小兽,不管不顾地扑了过去,
一头撞进他怀里,双手死死攥住他胸前的衣襟。浓重的酒气瞬间将上官鹤包围。
上官鹤猝不及防,被她撞得后退一步,下意识地伸手扶住她绵软下滑的身体。
怀中人滚烫的温度和浓烈的酒意让他眉头紧锁。“二**?”他声音干涩。
“上官鹤…你个**…王八蛋…”宋一汀把头埋在他胸前,含糊不清地咒骂着,
滚烫的泪水毫无预兆地涌出,迅速洇湿了他单薄的衣料,“你躲…你接着躲啊!
躲到老鼠洞里我也…我也把你揪出来!”她抬起泪痕狼藉的脸,
你…嫌你是黑工…是死囚…是见不得光的江湖草寇…配不上尚书府的千金…”她打了个酒嗝,
带着一种不管不顾的悲愤,声音陡然拔高,像受伤小兽最后的呜咽,“可我喜欢啊!上官鹤!
我就喜欢你!喜欢得要疯了!你知不知道?!”滚烫的泪水砸在上官鹤扶着她的手臂上,
灼得他心口一抽。他身体僵硬得像块石头,扶在她腰间的手,指尖无法控制地微微颤抖起来。
月光照亮她脸上狼狈的泪痕,那里面盛满了不掺一丝杂质的、近乎绝望的赤诚。许久,
他喉结艰难地滚动了一下,才发出低沉沙哑的声音,每一个字都像从砂纸上磨过:“二**,
你醉了。”他抬起另一只手,带着薄茧的指腹,极其缓慢、极其轻柔地,
擦过她湿漉漉的脸颊,拭去那滚烫的泪。动作间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珍惜,
却又浸透了无边的苦涩。“江湖上刀口舔血、朝不保夕的人…”他避开她灼人的视线,
望向巷子尽头无边无际的黑暗,声音轻得像叹息,又重得如同枷锁,
“…给不起尚书府千金任何承诺。明日酒醒,忘了今夜吧。”他试图将她推开,
动作却带着连自己都未察觉的犹豫。“承诺?”宋一汀却像被这个词彻底点燃了怒火,
猛地挣脱他的搀扶,踉跄着站稳,通红的眼睛死死瞪着他,声音尖锐而清晰,
“谁要你的狗屁承诺!我宋一汀要的,是你这个人!是你看我的眼神!是你躲着我的样子!
是你明明舍不得又不敢靠近的窝囊废样子!我只要你敢站在我面前,
说一句你也…”话未说完,一阵强烈的眩晕袭来,她身体一软,彻底醉倒在他臂弯之中,
失去了意识。上官鹤抱着怀中沉沉睡去、犹带泪痕的女子,站在冰冷死寂的深巷里,
像一尊被遗忘的石像。她滚烫的呼吸拂过他的颈侧,那句未吼完的话却像淬了火的鞭子,
狠狠抽在他自以为早已麻木的心上。月光将两人的影子拉长,纠缠在一起,
仿佛再也无法分开。京城局势风云诡谲,楚归鸿的千羽王父亲“死而复生”回朝,
掀起巨**澜。这位复活的“千羽王”实则是掌控剧本的编剧穿越而来,行事越发莫测。
一日,他竟在宫宴之上,当众宣布收残江月二当家上官鹤为义子,赐楚姓,享宗室子弟尊荣。
消息传开,举城哗然。昔日见不得光的江湖死囚、黑工上官鹤,竟一步登天,
成了千羽王府的“楚鹤公子”。这突如其来的身份转换,像一块巨石投入死水,
瞬间搅乱了所有既定的格局。最直接的结果是,尚书府再无法以“身份卑贱”为由,
强硬阻挠宋一汀与上官鹤的婚事。周雪怡看着那道加盖了王府金印的婚书,脸色铁青,
哑口无言。王府的聘礼流水般抬入尚书府那日,上官鹤(如今该称楚鹤)依礼登门。
宋聿德看着眼前这个身姿挺拔、容色俊美,
眉宇间褪去了几分江湖散漫、多了几分沉稳持重的青年,再想到他背后站着的千羽王府,
心中纵然仍有千百个不情愿,也只能强堆起笑容,在婚书上落了印。后院绣楼里,
宋一汀捏着侍女递进来的、关于“楚鹤公子”行止的密报,唇角勾起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
她屏退众人,对着铜镜,慢条斯理地描画着最明艳的妆容,换上最华贵的嫁衣。凤冠霞帔,
映得镜中人容光慑人,眼底却燃烧着猎人般的志在必得。洞房花烛,红烛高燃,
满室都是暖融的甜香。沉重的赤金凤冠被取下,宋一汀活动了一下发酸的脖颈,
目光如带着钩子,直直看向坐在桌边略显局促的新郎官。
上官鹤(他依旧习惯别人叫他这个名字)有些不自在地避开她过于灼热的视线,
拿起合卺酒杯:“二**…”话未说完,宋一汀已像一团燃烧的烈火扑了过来!
没有半分新嫁娘的娇羞,她带着一种近乎凶狠的气势,
将他重重按倒在铺满百子千孙被的喜床上。红烛跳跃的火光在她眼中燃烧,她俯下身,
红唇凑近他敏感的耳廓,温热的气息带着挑衅:“上官鹤,楚鹤公子?”她故意拉长了调子,
贝齿忽地张开,不轻不重地咬在他凸起的锁骨上!“唔…”上官鹤猝不及防,闷哼出声,
身体瞬间绷紧。那点刺痛混合着难以言喻的麻痒,像电流般窜遍全身。宋一汀抬起头,
看着他骤然暗沉翻涌的眼眸,笑得像只终于叼住猎物的狐狸,
语气带着得胜的骄纵和压抑太久的委屈:“再躲啊?现在看你还往哪里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