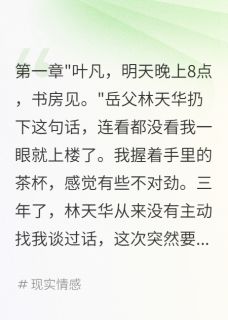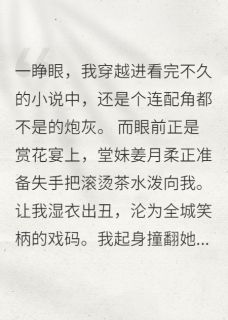清云的指尖掠过书页上“慈悲”而这时,檐角的风铃突然响了。她抬头望向窗外,
四月的雨丝正斜斜地织着,把对面的玉兰树洗得发亮。这样的雨天最适合读《金刚经》,
那些“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句子像温水,总能熨帖她那颗过分柔软的心。
她总觉得世间万物都裹着一层薄脆的玻璃壳,轻轻一碰就会碎。
楼下收废品的老张弯腰时脊梁骨发出的声响,地铁里年轻母亲哄哭闹孩子时沙哑的嗓音,
甚至办公室打印机卡纸时发出的呜咽,都会让她心里泛起细密的疼。
同事们说她“菩萨心肠”,她却知道,
那更像是一种无法治愈的敏感——像赤脚走在铺满碎玻璃的路上,
每一步都在感受他人的疼痛。独居的公寓在老城区的六楼,没有电梯。每天爬上爬下时,
清云都会数楼梯转角的裂缝。第一百零三级台阶有块菱形的缺损,
是去年冬天被楼上搬家的冰箱磕的;第三层平台的墙皮剥落处,露出里面暗红色的砖,
像块结痂的伤口。这些细微的印记构成了她生活的坐标,比日历更清晰地标记着时间的流逝。
清晨五点半,清云准时醒来。瑜伽垫铺在木地板上会发出轻微的摩擦声,她做下犬式时,
能听见楼下早点铺掀开蒸笼的声响,白汽混着葱花饼的香气顺着纱窗钻进来。
七点十五分出门,步行十五分钟到地铁站,三号线转一号线,出闸机时刚好八点零五分。
这份精确到分钟的规律,是她给自己筑起的堤坝,抵挡着外界汹涌的不确定。
2008年的夏天来得格外早。六月中旬,气象台就挂出了橙色预警。
清云的白衬衫后背总洇着淡淡的汗渍,地铁里的冷气吹得人关节发僵,
出站时被热浪裹住的瞬间,鼻腔里全是柏油融化的味道。那天她刚到公司,
就看见公告栏前围了群人,红底黑字的调令名单里,
她的名字后面跟着“调至第三事业部”。第三事业部在城郊的产业园,
离她的公寓四十二分钟车程。清云站在阳光下,看着自己的影子缩成小小的一团,
突然想起二十岁那年,母亲临终前攥着她的手说:“日子就像棉线,看着松散,
其实早被命运的针脚缝好了。”新办公室在二楼西侧,
整面墙的落地窗把阳光毫无保留地灌进来。清云整理工位时,发现窗台上摆着盆绿萝,
叶片上积着薄薄的灰。她找来抹布细细擦拭,指腹触到叶片边缘的锯齿时,身后传来一声笑。
“新来的同事很爱干净嘛。”那声音像冰镇酸梅汤滑过喉咙,清冽里带着点甜。清云转过身,
看见个穿浅蓝色衬衫的男人倚在门框上,袖口卷到手肘,露出的小臂上有道浅浅的疤痕。
他的头发剃得极短,跟光头差不多了,头皮在阳光下泛着青,反倒衬得眼睛更亮了,
像浸在水里的黑曜石。“我叫秦冲,负责供应链协调。”他走近时,
清云闻到淡淡的烟草味混着薄荷须后水的气息。他伸出的手骨节分明,虎口处有层薄茧,
“以后就是同事了,多多关照。”清云的指尖在掌心蜷了蜷,才轻轻握上去。他的手很烫,
像揣着团小火苗。“我叫清云。”她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些,
目光落在他衬衫第二颗纽扣上——那粒纽扣松了线,摇摇欲坠。秦冲的办公桌在斜对面,
隔着三排工位。清云整理文件时,总忍不住用余光瞥他。他打字时喜欢用食指敲键盘,
发出哒哒的声响;接电话时会下意识地摸耳朵,语气里总带着股子热乎劲儿,
哪怕对方在抱怨。有次供应商在电话里发了火,秦冲连声应着“是是是,您消消气”,
挂了电话却对着电脑屏幕做了个鬼脸,刚好被抬头的清云撞见。他愣了愣,随即咧开嘴笑了,
牙龈有点红,像刚吃过樱桃。午休时,清云习惯去天台吃自带的便当。
那天她正把腌黄瓜摆进米饭,秦冲端着泡面凑过来,在她旁边的水泥台上坐下。“清云老师,
你这便当看着比楼下食堂强多了。”他吸溜着泡面,热气模糊了眼镜片,
“我老婆做饭可没这手艺,顿顿离不开辣椒。”“秦哥结婚了?
”清云把筷子上的西兰花夹给他,“看不出来。”“孩子都已经七岁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钱包,抽出张照片给她看。照片里的小女孩扎着羊角辫,
正揪着秦冲的耳朵笑,背景是间逼仄的客厅,墙皮有些剥落。“叫念念,跟她妈一样,
是个小辣椒。”清云看着照片里秦冲眼角的笑纹,突然想起今早他黑眼圈下的青紫色。
她把自己的乌龙茶推过去:“少喝点咖啡,对胃不好。”秦冲接过杯子时,
手指碰到了她的手背。“还是清云老师细心。”他仰头喝了一大口,
喉结滚动的弧度像只吞咽的鸽子。七月的暴雨来得猝不及防。清云加班到七点,
发现伞落在了地铁里。她站在办公楼门口犹豫时,秦冲的车缓缓停在台阶下。“上车,
我送你。”他摇下车窗,额前的碎发被雨打湿,贴在光洁的额头上。车里放着邓丽君的歌,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清云系安全带时,看见副驾储物格里露出半截药盒,
上面写着“布洛芬缓释胶囊”。雨刷器来回摆动,把霓虹切成模糊的色块。
秦冲突然说:“我爸昨晚又发烧了,折腾到后半夜才睡着。”清云“嗯”了一声,
目光落在窗外掠过的公交站台。有个穿校服的女孩正抱着书包奔跑,雨衣的帽子被风吹掉,
露出湿漉漉的马尾。“我妈股骨头坏死,医生说要换关节,
可那手术费……”秦冲的声音低了些,“我老婆天天跟我吵,说嫁给我倒了八辈子霉。
”他猛打方向盘避开积水,轮胎溅起的水花打在护栏上,“有时候真觉得,活着就是熬。
”清云看着他握着方向盘的手,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发白。她想安慰些什么,
话到嘴边却变成:“前面路口停就好,我走路回去。”秦冲在便利店门口停了车。
清云推开车门时,他递过来把黑色的伞。“这把新的,没用过。”伞柄上还缠着价签,
“别淋感冒了。”雨夜里,清云撑着那把伞慢慢走。伞面很大,把她整个人都罩在里面,
像个移动的黑色帐篷。路过小区门口的馄饨摊时,她看见对老夫妻正收拾摊位,
老太太腿脚不便,老头就背着她跨过积水。清云站在路灯下,
看着那把摇摇晃晃的旧伞消失在巷口,突然想起秦冲虎口的茧子。第二次一起吃饭,
是在八月的一个周五。秦冲说部门完成了季度指标,要请客庆祝。清云本想拒绝,
却被同事们推搡着上了车。饭局设在城郊的农家乐,院子里种着葡萄藤,
紫莹莹的果实垂在头顶。秦冲以各种理由拒绝了那些灌他酒的同事,
推搡间被同事羞得脸颊通红,却总不忘给清云夹菜。他夹来一块糖醋排骨,
低声说:“念念最爱吃这个,每次做她都能多吃半碗饭。”清云咬着排骨,
酸甜的汁水流进喉咙,却有点发苦。她看见秦冲手机屏幕亮了,是条短信,
预览栏里写着“又死哪儿去了”。秦冲迅速按灭屏幕,端起酒杯跟别人碰了碰,
笑容里的疲惫像潮水般涌上来。散场时已近午夜。秦冲坚持要送清云回家,
说女孩子一个人不安全。车开上高架桥时,他突然把车停在应急车道,
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清云听见压抑的呜咽声,像受伤的兽在低吼。
她从包里摸出纸巾递过去,指尖不小心碰到他的头发——短短的发茬扎得人发痒。
“我真羡慕你,清云。”秦冲抬起头,眼睛红得吓人,“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多好。
”清云望着远处城市的灯火,那些星星点点的光在雨雾里模糊成一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她轻声说,“只是你看不见罢了。”秦冲发动车子时,
清云看见他手腕内侧有块淤青,像朵蔫掉的紫花。九月的第一个周一,
清云在茶水间遇见秦冲。他正对着镜子扯领带,脖子上有道浅浅的红痕。看见清云进来,
他下意识地把衣领竖了起来。“早啊。”他的声音有点哑,像是没睡醒。“念念开学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