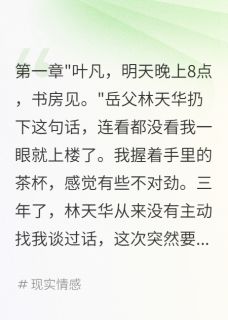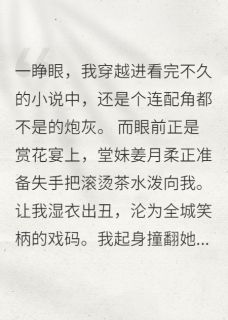新帝登基的仪仗,裹挟着明黄的旌旗与震耳的礼乐,如同一条喧嚣的、不容抗拒的洪流,
碾过京城的每一条御道。金水桥畔,残留的硝烟气息尚未散尽,
又被新漆的朱红和熏天的香烛强行覆盖。怀王府,这座曾浸透血雨腥风的府邸,
此刻却笼罩在一片奇异的寂静里。仆役屏息垂首,脚步放得极轻,仿佛怕惊扰了什么。
书房厚重的门扉紧闭,将外界的喧嚣彻底隔绝。萧临渊立在书案前,
窗外喧嚣的礼乐声隐约传来,如同隔着一层厚厚的帷幕。他面前摊着两份东西。左边,
是半块鱼形玉佩。玉佩边缘温润,鱼鳃处的银饰在烛光下流转着内敛的光泽,
只是鱼眼脱落处,那个刻着“同归”二字的金珠空洞,像一个沉默的伤口,
无声诉说着贡女血泪的过往。这是苏若若母亲留下的唯一遗物,
也是皇帝罪证链上冰冷的一环。右边,是一方沉甸甸、通体玄黑、以猛虎为纽的——虎符。
冰凉的触感透过指尖传来,象征着曾握在掌中的滔天兵权,
也象征着无数沙场征伐的生死与枯骨。他伸出手,没有半分犹疑。那只戴着黑皮手套的手,
指节依旧根根分明,却不再紧绷如铁。他拿起那半块玉佩,指尖拂过“同归”的刻痕,
动作是前所未有的轻缓。然后,
他将玉佩轻轻放入案几上一个半开的、褪了色的紫檀木画匣中。画匣里,
静静躺着几幅纸页泛黄、墨迹已淡的蝴蝶画。稚拙的笔触,或栖残枝,或逐落花,
右下角那行“若儿七岁涂鸦”的小字,墨色晕散,却灵气犹存。匣底深处,
还压着几片薄如蝉翼、用硝石精心处理过、色彩依旧鲜亮的蝴蝶标本(对应第五章百蝶劫)。
接着,他拿起那方虎符。玄铁沉冷,猛虎狰狞。他托在掌心,
感受着这份曾主宰无数人生死、也曾是他唯一安身立命之物的重量。片刻,
他手腕沉稳地一转,虎符被无声地置于画匣之上,压住了那些脆弱的蝶翅与旧梦。
“嘎吱——”书房门被推开一线,没有通禀。苏若若的身影出现在门口。她依旧清瘦,
但脸上那种濒死的灰败已褪去,只余大病初愈后的苍白。身上是一袭素净的月白襦裙,
发间没有任何珠翠,只用一根打磨光滑的桃木簪松松绾着。
她手中捧着一个小小的、以九宫格形制编织的柳条筐,筐里是新采的草药,
散发着清苦微辛的气息。她的目光掠过案上那方压在蝶画之上的虎符,又落回萧临渊脸上。
没有惊讶,没有询问,只有一种了然于心的平静。她走进来,
将柳条筐轻轻放在窗下的矮几上,草药的气息顿时在沉滞的书房里弥漫开一丝生机。
萧临渊拿起早已备好的一个青布包袱,走到她面前,递了过去。包袱入手微沉。
苏若若解开系带。里面是一套叠得整整齐齐的粗布衣裙,浆洗得发白。衣料下,
压着一只扁平的木匣。她打开木匣。匣内,左边,
整齐码放着一层色泽暗沉、散发着浓郁陈年甘香气息的——陈皮。右边,
是那个装着褪色蝴蝶画和半块玉佩的紫檀画匣。她的指尖拂过冰凉的紫檀木,
在那几幅蝴蝶画上停顿片刻,最终落在那半块玉佩上,轻轻摩挲着“同归”的刻痕。然后,
她合上木匣,抬起头,对着萧临渊,极轻、极缓地,点了一下头。没有言语。一个眼神,
一个动作,便已足够。京郊官道。一辆再寻常不过的青篷马车,碾过初春解冻的泥泞,
吱呀作响,驶离了身后那座庞大、喧嚣、浸满权力与血腥的城池。车帘低垂,
将新帝登基的煊赫仪仗与残留的硝烟彻底隔绝。车厢内很简陋。一只红泥小火炉煨着药吊子,
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清苦的药香弥漫。苏若若靠坐在软垫上,膝上放着那个青布包袱。
她取出木匣,打开,拿出那个装着蝴蝶画与玉佩的紫檀匣子,放在身侧。
目光落在匣底那几片蝴蝶标本上,指尖轻轻拂过薄脆的蝶翼。萧临渊坐在对面,背脊挺直,
闭目养神。他换下了象征亲王身份的蟒袍,穿着一身半旧的靛蓝棉布直裰,腰间没有佩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