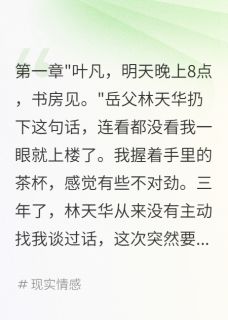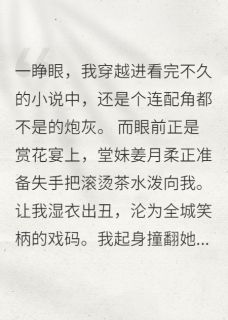1雪夜绝恋雪,纷纷扬扬地飘落,这座城市仿佛被披上了一层银白的纱衣,静谧而凄美。
我站在天台上,单薄的身影摇摇欲坠,凛冽的寒风如同一把把锐利的冰刀,
毫不留情地割裂着我的脸颊。可此刻,身体上的疼痛远远不及内心的万分之一。视线模糊中,
楼下宋源和白薇的身影在雪中晃动,他们仰头望向我,
白薇嘴角那抹得意的笑如同恶魔的印记,深深刺痛我的眼;而宋源,
那个曾经与我山盟海誓的男人,此刻眼神冰冷得仿佛千年寒潭,满满的厌恶几乎要将我吞噬。
我望着他的眼,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回到往昔,那是一段如梦如幻的美好时光。曾经,
我和宋源,是这世上最亲密无间的两个人。巷口那棵古老的梧桐树下,
留存着我们无数嬉笑玩耍的身影。每到夏夜,繁星点点如同碎钻洒满夜空,
我们便会躺在柔软的草地上,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语气中满是坚定与温柔:“绵绵,
等我们长大了就结婚,我要让你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新娘。”那些甜蜜的承诺,
犹如最香醇的美酒,沉醉了我的心,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憧憬。然而,
命运的轨迹总是如此无常。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无情地夺走了我父母的生命,刹那间,
我从一个被爱包围的幸福女孩,变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就在我感到绝望之时,
宋源向我伸出了援手,他将我带回了他家。那一刻,我以为自己找到了新的依靠,
希望生活将重新步入正轨,却万万没想到,这竟是噩梦的开端。我刚搬进宋源家时,
客厅的落地窗正对着院里那棵老梧桐。宋源把二楼朝南的房间收拾出来给我,
木桌上摆着个蓝白格子的陶瓷杯,是小时候我摔破过又被他粘好的那个。“绵绵你看,
”他指着衣柜最上层,“你以前总丢三落四的画具,我都收着呢。
”颜料管上还留着她歪歪扭扭写的名字,边角卷了毛的素描本里,
夹着张她偷偷画的他的侧脸。住进他家的这段时光像最甜的糖,融化在我心里,
我也开始慢慢走出父母去世的伤痛。多希望能永远这样该有多好,可三个月后白薇的出现,
彻底打破了我仅存的一丝希望。她作为宋源的表妹,自踏入这个家门的那一刻起,
便如同一个带着恶意的幽灵,开始对我展开了无休止的刁难。头一个月,
白薇还装得像模像样。她会端着温牛奶上楼,笑盈盈地说:“绵绵姐,源哥说你晚上容易饿。
”何绵绵接过杯子时,
总能瞥见她指甲缝里没擦干净的指甲油——和宋源前几天弄丢的**款一个色号,
但她没作声,只想着别给宋源添麻烦。直到某个雨夜,何绵绵起夜时听见白薇在客厅打电话。
“妈你放心,”她声音压得很低,却带着藏不住的得意,“宋源哥现在对我可好了,那孤儿?
不过是暂住罢了。等我拿到他妈妈留的那串玉镯,就……”我攥着楼梯扶手的手泛了白,
转身时撞翻了墙角的花瓶。白薇猛地挂了电话,冲过来扶住她:“绵绵姐你没事吧?
是不是吓到了?”那瞬间的惊慌一闪而过,很快又变回那副纯良模样。
第二天宋源发现碎瓷片,白薇红着眼圈说:“是我笨手笨脚碰掉的,绵绵姐劝我别告诉你,
怕你生气。”何绵绵张了张嘴,看见宋源眼里的疲惫,最终把“不是她”三个字咽了回去。
她那时还不懂,有些沉默,会变成刺向自己的刀。有次宋源加班到深夜,我热了粥等他。
白薇抢着端去书房,回来时哭着说被何绵绵推了一把,粥洒在地毯上烫红了脚踝。
宋源冲进厨房时,正看见何绵绵蹲在地上,用纸巾一点点擦着溅到鞋上的粥渍,
抬头时眼里的委屈像浸了水的棉花,重得让人心慌。“你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吗?
”他的话砸下来时,何绵绵手里的纸巾飘落在地,像一片提前凋零的梧桐叶。她没看见,
宋源转身回房后,对着手机里存着的、她十岁时笑得露出虎牙的照片,指尖悬了很久才落下,
最终只熄了屏。白薇进来的第三个周末,宋源带我去逛旧物市场。
在一个摆满搪瓷杯的摊子前,他拿起一个印着向日葵的杯子,
指尖摩挲着边缘:“你小时候总偷用我妈这个杯子喝水,说上面的花比你家院里的好看。
”何绵绵的手指刚碰到杯沿,就听见身后传来白薇的声音:“源哥,我脚好疼。
”转头看见白薇皱着眉扶着脚踝,新买的帆布鞋上沾了块泥渍。宋源下意识想过去,
却被何绵绵轻轻拉住:“那边有卖创可贴的,我去买。”她跑着买回创可贴时,
正看见白薇踮脚替宋源理了理被风吹乱的衣领,脸上带着她从未见过的亲昵。
宋源低头说着什么,阳光落在他侧脸,那副温和的模样,是这阵子何绵绵很少见到的。
她捏着那包创可贴站在原地,忽然觉得手里的向日葵杯子沉得像块石头。
有天夜里何绵绵发了高烧,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人在给她盖被子。她睁开眼,
看见宋源坐在床边,额头抵着她的额头试温度,眉头皱得很紧:“怎么烧得这么厉害?
”他的呼吸拂在她脸上,带着熟悉的薄荷牙膏味,像小时候她生病时他守在床边的样子。
可不等她说话,门“吱呀”一声开了。白薇穿着睡衣站在门口,眼眶红红的:“源哥,
我做了噩梦,想跟你睡……”话没说完就看见屋里的情景,立刻低下头:“对不起,
我打扰绵绵姐休息了。”宋源起身时,何绵绵攥住了他的衣角。那是她第一次主动挽留,
指尖却在触到他布料的瞬间松了劲。宋源最终还是走了,关门声轻得像叹息,
却在她心里震出一片空响。后半夜她烧得更厉害,想找水杯却打翻了床头柜,
陶瓷杯摔在地上的脆响里,混着楼下隐约传来的、白薇低低的啜泣声。
深秋时梧桐叶落了满地,宋源难得有空,提了扫帚拉着何绵绵去扫叶子。
“小时候你总说踩落叶像踩碎星星,”他笑着扬起扫帚,金黄的叶子在风里打着旋,
“今天让你踩个够。”何绵绵刚抬脚,就被白薇的尖叫打断。
她不知何时搬了把椅子坐在廊下,手里的毛线团滚到了落叶堆里,
针脚还勾着半只没织完的手套——那毛线的颜色,和宋源上个月说想要的一模一样。
“都怪你!”白薇跺着脚,“这是我给源哥织的手套!”宋源弯腰去捡毛线团,
手指被勾住的针尖划了道口子。何绵绵下意识掏出纸巾想给他擦,
白薇却抢先一步按住他的手:“源哥我看看!都流血了!肯定是何绵绵故意吓我,
不然毛线团怎么会掉!”那天的落叶最终没扫成。宋源被白薇拉着去包扎伤口,
走前回头看了何绵绵一眼,眼神复杂。她站在满地碎金似的落叶里,
看着那半只勾着线头的手套,忽然想起小时候宋源帮她摘梧桐果,被树枝划破手掌,
她把自己的糖纸贴在他伤口上,说这样就不疼了。2梧桐旧梦原来有些温暖,
真的会像落叶一样,落了就再也捡不起来了。冬至那天,宋源妈妈留下的老座钟坏了。
钟摆卡在三点十分,像凝固住的时光。宋源蹲在客厅修钟,何绵绵端着刚煮好的汤圆走过来,
瓷碗在茶几上磕出轻响。“小时候你总抢我碗里的芝麻馅,”她轻声说,
“说甜的能治你怕黑的毛病。”宋源手里的螺丝刀顿了顿,
没抬头:“那时候你总把我推到钟底下,说钟响的时候鬼就不敢来了。
”他指尖划过钟面的裂纹,那是去年台风天,他抱着怕打雷的何绵绵躲在钟旁,
被掉落的相框砸的。白薇突然从楼上跑下来,手里攥着条围巾:“源哥你看,我织好了!
”她把围巾往宋源脖子上绕,毛线蹭过他下巴时,故意往何绵绵那边瞥了眼,
“绵绵姐肯定不会织这些吧?毕竟以前在家都是娇**。”何绵绵的手缩了缩,
碗沿烫得指尖发红。她确实不会织,但她记得宋源脖子容易过敏,
特意去布店挑了纯棉的料子,想做条方巾。布料现在还压在衣柜最底层,叠得整整齐齐,
像她没说出口的关心。“我去热牛奶。”她转身要走,却被宋源叫住。“绵绵,
”他声音有点哑,“钟修不好了。”她回头时,正撞见白薇往他嘴里喂汤圆,
芝麻馅沾在他嘴角,白薇笑着伸手去擦。那画面刺得她眼睛发酸,
她低下头:“修不好就换一个吧。”“可这是……”宋源想说什么,
被白薇打断:“源哥别修了,我给你买新的!比这个旧钟好看一百倍!”她拽着他的胳膊晃,
“对了,下周同学聚会,你带我去吧?让大家看看我新织的围巾。”宋源最终点了头。
聚会那天何绵绵没去,她在房间整理旧物,翻出宋源送她的第一支钢笔。
笔帽上刻着歪歪扭扭的“绵”字,是他十岁时用小刀划的,划到手流血还嘴硬说不疼。
凌晨宋源回来时,带着一身酒气。他站在房门口,影子被走廊灯拉得很长。“他们问起你了,
”他说,“我说你不舒服。”何绵绵捏着钢笔没说话。“白薇在聚会上说,
你偷了她的钻石项链。”他声音里带着酒后的混沌,“我跟他们吵了一架。
”何绵绵猛地抬头:“你不相信我?”宋源却别过脸,喉结滚动:“绵绵,
你能不能……别总让我为难?”钢笔从掌心滑落,在地板上砸出清脆的响。
何绵绵看着他转身的背影,突然笑了,眼泪却掉了下来:“宋源,
你记不记得小时候我掉进水塘,你跳下来救我,自己呛得差点喘不上气?
你说就算全世界都不信我,你也信。”他的脚步顿在楼梯口,没回头。“现在我信了,
”她轻声说,“有些话,就像那座钟,停了就是停了。”后来白薇又生了事端。
她把宋源妈留下的玉镯藏进何绵绵的枕头下,当着宋源姑姑的面翻出来,
哭得浑身发抖:“姑姑你看!我说她惦记这镯子很久了!”姑姑指着何绵绵的鼻子骂不要脸,
宋源站在中间,脸色青一阵白一阵。何绵绵看着他,突然开口:“宋源,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送我回家,在巷口的梧桐树下,你说这镯子将来要当我的嫁妆吗?
”宋源猛地看向她,眼里翻涌着震惊和慌乱。“你说等我二十岁生日,
就把镯子取出来给我试戴,”她继续说,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死水,“你说我的手腕细,
戴这个肯定好看。”白薇尖叫起来:“你胡说!源哥怎么会跟你说这些!
”宋源却像被钉在原地,嘴唇翕动着,一个字也说不出来。那些被他遗忘的细节,
突然像潮水般涌来——他确实说过,在某个蝉鸣聒噪的夏夜,他蹲在她面前,
用树枝在地上画镯子的样子。那天最终以何绵绵被锁进房间收场。
宋源隔着门板说:“你先冷静几天。”3玉镯风波何绵绵贴着冰冷的门板滑坐在地,
听见他下楼的脚步声里,混着白薇委屈的哭诉。她想起他最后看她的眼神,
像看着一件棘手的旧物,舍不得丢,又不想再碰。“宋源,”她对着门板轻声说,
“我不怪你了。”只是这句话,他再也听不到了。玉镯事件后的第三天,
何绵绵在厨房煮姜汤。宋源前晚淋了雨,今早起来咳得厉害。她把姜片切成碎末,
想起小时候他感冒,她偷了家里的红糖,煮了碗甜得发腻的姜汤,他捏着鼻子喝完,
说比药还管用。“宋源,”我端着碗走进客厅,看见他正帮白薇整理书包,“喝点姜汤吧。
”白薇抢先接过碗,故意手一抖,姜汤洒在宋源的衬衫上。“哎呀对不起!”她跺着脚,
“都怪绵绵姐,煮这么烫!肯定是故意想烫源哥!”宋源皱着眉扯开湿衬衫,胸口红了一片。
何绵绵慌忙去拿毛巾,却被他推开:“够了!”他的声音带着压抑的怒火,“何绵绵,
你就不能安分点吗?非要找点事出来才甘心?”“我没有……”她想解释,
却被他冰冷的眼神堵回去。“没有?”宋源指着地上的姜汤渍,“从你住进来到现在,
家里就没安宁过!白薇手被针扎,我脖子过敏,
现在连喝碗汤都要被烫——你是不是见不得我们好?”何绵绵的手僵在半空,毛巾掉在地上。
她看着他,眼里的光一点点暗下去:“宋源,你真的觉得,我是这样的人?”“不然呢?
”他别过脸,语气里满是不耐,“以前觉得你单纯,现在才发现,你心思这么重。
”那天下午,白薇拉着宋源去买新衬衫。出门前,白薇往何绵绵的书桌上放了个音乐盒,
是宋源去年在她生日时送的,后来被她弄丢了。“绵绵姐,这是源哥找回来的,
”她笑得甜腻,“他说还是你拿着合适。”何绵绵刚碰到音乐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