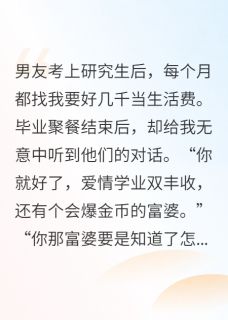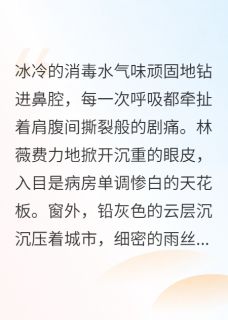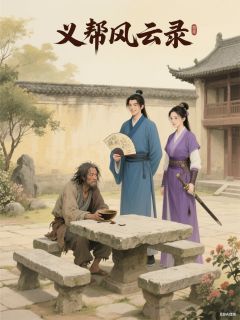>靖王萧景珩下令拆除街市所有违章摊位。>我的辣椒酱摊子首当其冲。>“王爷明鉴!
”我捧着酱坛拦住仪仗,“此乃民生之本!”>他垂眸冷笑:“刁民当斩。
”>当晚王府送来聘书——要我当厨娘。>我咬牙端上全辣宴,辣得他眼尾泛红。
>他却攥住我手腕:“辣椒开花时,像不像大婚的喜帕?”>后来敌军围城,
我在城门架起油锅。>热油浇下时,他嘶吼着劈开人墙:“晚意,回家酿你的辣椒酱!
”>——可我的酱坛子,早碎在他下令拆摊那日了。---永庆四年的寒露刚过,
京城的气温便一日冷似一日。清晨的寒意最是刁钻,凝成薄薄一层白霜,
严严实实地覆在街巷的青石板路上,踩上去又硬又滑,直往人骨头缝里钻冷气。
然而这冰冷的肃杀,却被东市早市鼎沸的人声与蒸腾的烟火气撕开了一道口子。
“新出笼的肉包子——皮薄馅大,热乎的嘞!”“糖葫芦!又脆又甜,不甜不要钱!
”“磨剪子嘞——戗菜刀!
”吆喝声、讨价还价声、锅碗瓢盆的碰撞声、骡马喷着响鼻的嘶鸣,
交织成一曲粗犷却生机勃勃的市井交响。
的味道:刚炸出锅的油条油饼的焦香、蒸笼里透出的面食甜香、新鲜蔬菜沾染着泥土的清气,
还有无处不在、浓烈霸道的卤煮下水味儿。就在这喧闹画卷的一角,
紧挨着“王记绸缎庄”那气派的雕花门楼,支着一个简陋却分外惹眼的小摊。
一张洗得发白、边缘已磨出毛边的青布铺在板车上,上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个粗陶小坛。
每个坛子都用红布蒙着口,扎着细细的麻绳。坛子旁立着一块半旧的木牌,
上面用墨汁淋漓地写着三个歪歪扭扭的大字:“朝天椒”。字迹虽不工整,
却透着一股子泼辣生猛的劲头。摊主林晚意裹了裹身上那件同样洗得发白的青布夹袄,
往冻得发红的双手间哈了口白气,用力搓了搓。
她的头发用一根褪了色的红头绳高高束在脑后,露出光洁饱满的额头和一双亮得惊人的眼睛。
此刻,那双眼睛正警惕地扫视着街面,像只随时准备扑击或闪避的小兽。“晚丫头,
还支着呢?不怕?”旁边卖针头线脑的刘大娘压低了嗓子,朝街口方向努了努嘴,
脸上满是忧虑,“昨儿后半晌,官差可又拿着告示来吆喝了一遍,说今儿是最后期限!
靖王爷亲自下的令,要清街!你这摊子,可是顶在风口浪尖上啦!”林晚意抬手,
用指节蹭了蹭被寒气冻得有些发痒的鼻尖,嘴角却倔强地向上弯起一个细微的弧度:“怕啥?
王大娘。我林晚意一不偷二不抢,凭本事吃饭,靠手艺养家。这‘朝天椒’是祖传的手艺,
街坊们吃了都说好,暖身开胃,寒冬腊月里顶顶管用!王爷他老人家日理万机,
总不能连老百姓一口热辣咸香的滋味儿都要管吧?”她声音清脆,带着点小姑娘特有的娇憨,
可字字句句都透着不服软的硬气。刘大娘被她这理直气壮的模样噎了一下,
无奈地摇头:“你这丫头啊,就是头犟驴!那告示上白纸黑字写着‘有碍观瞻,堵塞通衢’,
王爷的令,那就是铁板钉钉!待会儿……”话音未落,
一阵极其沉闷、极富压迫感的声响从长街的另一端滚雷般碾压过来。咚!咚!咚!
声音缓慢而沉重,仿佛巨兽的脚步踏在人心上。紧接着,是金属甲叶摩擦碰撞的冰冷脆响,
整齐划一,带着森然的寒意。原本喧闹如沸水的街市,像被一只无形巨手猛地扼住了喉咙。
叫卖声、谈笑声戛然而止,只剩下锅灶里柴火燃烧的噼啪声,显得突兀而惊惶。
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声音传来的方向。街口,一队玄甲卫士如同铁铸的潮水,
沉默地涌出。他们身披玄色重甲,头盔覆面,只露出一双双毫无感情、鹰隼般锐利的眼睛。
腰间佩刀的长鞘随着步伐规律地撞击着腿甲,发出“嚓、嚓”的死亡节拍。
沉重的脚步踏在冰冷的石板上,激起细小的冰屑粉尘。队伍中央,
簇拥着一匹通体墨黑、神骏非凡的高头大马。马背上端坐一人。玄色织金的亲王蟒袍,
包裹着挺拔如松的身躯。腰间束着玉带,悬着一枚毫无瑕疵的羊脂玉佩。他并未戴冠,
墨玉般的长发用一根简单的乌木簪束起,几缕碎发垂落,拂过线条冷硬的下颌。那张脸,
无疑是极其俊美的,鼻梁高挺,唇线薄而清晰。然而最慑人的,是那双眼睛。
深邃如寒潭古井,平静无波,目光扫过之处,仿佛连空气都被瞬间冻结,
只剩下绝对的威仪和一种俯视蝼蚁般的漠然。正是当朝天子胞弟,执掌京畿戍卫,
以铁腕冷峻闻名的靖亲王——萧景珩。他手中并未持鞭,只是随意地搭在鞍鞯上,
修长的手指骨节分明。在他目光的笼罩下,整条长街死寂一片。方才还鲜活生动的烟火气息,
瞬间被抽空,只剩下凛冬般的肃杀。摊贩们噤若寒蝉,纷纷下意识地往后缩,
恨不得将自己和摊子都嵌进墙壁里。林晚意的心脏,
也在那冰锥般的目光扫过自己摊位的瞬间,猛地一缩。一股寒意从脚底板直冲天灵盖。
她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带来一丝尖锐的痛感,
才勉强压住那股想要立刻推车逃跑的冲动。她看见,靖王身侧一名骑着枣红马的官员,
正抬手指点着街边的摊棚,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地穿透死寂:“……王爷明鉴,
此等私搭乱建,阻塞通衢,秽物横流,实乃京城之疥癣!尤以这绸缎庄旁之摊点,
公然污损商户门面,更是首恶!依令,当为首拆之!”那官员的手指,不偏不倚,
正指向她的“朝天椒”!轰的一声!一股滚烫的热血直冲林晚意的脑门,
瞬间烧干了所有的恐惧!拆她的摊?这是她爹娘留下的唯一念想,
是她在这偌大京城里安身立命的根本!没了这坛坛罐罐,她拿什么活下去?“不行!
”这两个字几乎是本能地从喉咙里冲了出来,带着破音的尖利,
在死寂的街道上显得格外突兀刺耳。所有人的目光,包括那高高在上的冰冷视线,
瞬间如同实质的针,狠狠扎在了林晚意身上。她什么也顾不上了!身体先于脑子做出了反应。
她猛地弯腰,
手用力抱起板车上最靠近自己、也是她最得意的一坛子秘制辣椒酱——那是她熬了三个通宵,
用了最上等的秋辣椒,加了独门香料才成的珍品!坛子沉甸甸的,
粗砺的陶壁冰着她冻僵的手指。她像抱着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又像抱着最后的救命稻草,
用尽全身力气,跌跌撞撞地朝着那缓缓行来的、代表着毁灭的黑色洪流冲了过去!“王爷!
王爷明鉴——!”林晚意瘦小的身影,在森严的铁甲卫队前,
渺小得如同一只扑向烈焰的飞蛾。玄甲卫士的反应快得惊人,几乎在她冲出的刹那,
前排两名卫士腰间长刀“锵啷”一声,已闪电般出鞘半尺!
雪亮的刀锋反射着冬日微弱的晨光,带着死亡的气息,瞬间横亘在她面前,
距离她的脖颈只有寸许!冰冷的刀气激得她颈后的汗毛根根倒竖。她猛地刹住脚步,
巨大的惯性让她怀里的酱坛子剧烈地晃荡了一下,发出沉闷的磕碰声。心跳如擂鼓,
撞击着单薄的胸膛,几乎要破膛而出。她强迫自己抬头,迎向那高高在上的目光。
萧景珩勒住了马缰。墨玉骓喷了个响鼻,前蹄不安地在地上刨动了一下。他微微垂眸,
那双寒潭般的眼睛终于聚焦在这个胆大包天的“刁民”身上。
她洗得发白的青布袄、冻得通红的脸颊、还有那双燃烧着不屈火焰的明亮眼睛上停顿了一瞬,
最终落定在她紧紧抱在胸前、视若珍宝的粗陶坛子上。坛口蒙着的红布,
在铁灰色的甲胄背景中,刺眼得像一滴凝固的血。他的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连眉毛都未曾抬动一分。薄唇微启,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遍整条死寂的街道,
每一个字都裹着寒冰的棱角,砸在青石板上:“刁民,拦阻仪仗,冲撞王驾。”他顿了顿,
那毫无温度的目光扫过林晚意瞬间煞白的脸,如同宣判,“按律,当斩。”“当斩”二字,
如同两道无形的冰锥,狠狠刺入林晚意的耳膜,直透心底!
她只觉得一股寒气从尾椎骨窜上头顶,四肢百骸瞬间僵硬冰冷。怀里的酱坛子仿佛有千斤重,
又似乎下一刻就要脱手摔碎。然而,就在这极致的恐惧攫住她的瞬间,
一股更加强烈的、混杂着委屈、愤怒和不甘的火焰猛地从心底蹿起!凭什么?
凭什么她安分守己做点小买卖糊口,就要被说成是“疥癣”?凭什么她视若珍宝的手艺,
在他口中就成了“秽物”?凭什么他轻飘飘一句“当斩”,就能碾碎她所有的希望?
恐惧被这骤然爆发的愤怒烧成了灰烬。林晚意猛地吸了一口气,
那带着寒意的空气刺痛了她的肺腑,却也让她的声音陡然拔高,
带着一种豁出一切的尖利和孤勇,清晰地在肃杀的空气中炸开:“王爷!民女冤枉!
”她抱着坛子,非但没有后退,反而倔强地挺直了单薄的脊背,仰着头,
直直地迎向那双冰冷的眼睛,“民女林晚意,世代清白!在此摆卖祖传秘制辣椒酱,
一为糊口,二为街坊邻里寒冬添一份暖辣!何来冲撞?何来当斩?”她腾出一只手,
用力拍在怀中粗陶坛冰凉的外壁上,发出“嘭”的一声闷响,
仿佛敲响了鸣冤鼓:“王爷请看!此乃民生之本!非是秽物,是暖意!是活命的口粮!
”她的声音因激动而微微发颤,眼圈瞬间红了,却倔强地不让眼泪掉下来,“王爷下令清街,
民女不敢不从!可王爷圣明,总要给条活路走!这坛坛罐罐,是民女的命!拆了它,
就是断了民女的生路!”她的话语像一串被点燃的炮仗,噼里啪啦地在寂静的街道上炸开。
周围的摊贩们听得心惊肉跳,却又隐隐被她话语中那股子不顾一切的悲愤所感染。
刘大娘捂住了嘴,眼泪在浑浊的老眼里打转。连那些铁甲卫士,
冰冷的眼神里似乎也掠过一丝极其细微的波动。萧景珩的眉头,几不可察地蹙了一下。
那双深不见底的寒眸,终于有了一丝涟漪。
他沉默地看着下方那个抱着粗陶坛子、仰着脸、像一株在寒风中倔强挺立的小辣椒般的女子。
她的愤怒是真实的,恐惧被压下后的孤勇也是真实的。尤其是那双眼睛,明明泛着红,
却亮得惊人,燃烧着不屈的火焰,仿佛能灼伤人。他的目光在她拍着坛子的手上停留了一瞬,
那双手冻得通红,指节粗糙,显然常年操劳。视线又扫过她摊位上那些蒙着红布的粗陶小坛,
在肃杀的冬日清晨,那一点点的红色,竟显得有些刺目,又有些……扎眼。时间仿佛凝滞了。
冰冷的空气似乎都停止了流动。整条街,上千双眼睛,
都死死盯在那个小小的身影和那高高在上的亲王之间。终于,萧景珩的薄唇再次开启,
声音依旧冰冷,听不出任何情绪,却不再是那催命的“当斩”:“拿下。”没有多余的解释,
只有两个冰冷的字。林晚意的心猛地一沉,抱着坛子的手臂骤然收紧!完了!
他还是不肯放过她!泪水终于不受控制地涌了上来,模糊了视线。然而,
预想中如狼似虎的扑拉并未发生。
只见靖王身侧一名身着玄青色劲装、气质精干的侍卫统领(陈锋)迅速上前一步,并未拔刀,
只是对着林晚意一拱手,动作干脆利落,语气虽冷硬却并无暴戾:“姑娘,请。”不是锁拿,
更像是……押送?林晚意愣住了,蓄满眼眶的泪水悬而未落,愕然地看着那名侍卫,
又茫然地看向马背上的靖王。萧景珩却已不再看她,目光漠然地投向远处,
仿佛刚才的一切争执从未发生。他轻轻一夹马腹,墨玉骓迈开步子,
沉重的玄甲卫队如同冰冷的潮水,绕过呆立原地的林晚意,继续向前碾压而去,
只留下被践踏得一片狼藉的街道和无数惊魂未定的目光。“姑娘,请随我来。
”侍卫统领陈锋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不容置疑的催促。
林晚意茫然地抱着她那坛宝贝辣椒酱,像一截失了魂的木桩,
被两名沉默的玄甲卫士“护送”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冰冷坚硬的青石板路上,
离她那个小小的“朝天椒”摊位越来越远。身后,
隐约传来木架被推倒、摊棚被扯烂的碎裂声,还有压抑的啜泣和低低的咒骂。她不敢回头,
只是死死抱着怀里的坛子,粗糙的陶壁硌得胸口生疼。坛子里浓郁的、辛烈霸道的酱香,
此刻闻起来却带着一种绝望的苦涩。王府的朱漆大门在望,高得仿佛要压到人头顶。
巨大的铜钉在惨淡的天光下闪着冷硬的幽光。门口蹲踞的石狮子龇牙咧嘴,栩栩如生,
冰冷的眼珠似乎都在盯着她这个渺小的闯入者。门楣上巨大的匾额,
“靖亲王府”四个鎏金大字,铁画银钩,带着沉甸甸的、不容置疑的威严。
林晚意被从王府的角门带了进去。一入府内,仿佛进入了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外面市井的喧嚣、烟火气、乃至那刺骨的寒意,瞬间被隔绝。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窒息的、近乎凝固的寂静和无处不在的、冰冷的奢华。
脚下是光可鉴人的青色水磨石砖,严丝合缝,冰冷坚硬。回廊曲折幽深,
两侧是朱漆雕花的长窗。庭院里古木参天,枝桠虬劲,在冬日里只剩下光秃秃的黑色线条,
切割着灰蒙蒙的天空。偶有身着统一服色的侍女或小厮垂首快步走过,步履轻得如同猫儿,
目不斜视,偌大的府邸,竟听不到多少人声。她被带到一间偏厅。厅内陈设简单,
却无一不精。紫檀木的桌椅泛着沉稳的暗光,墙上挂着意境悠远的水墨山水,
墙角高几上摆着一盆素雅的兰草。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清冷的檀香气息。“在此等候。
”陈锋丢下一句话,便转身离去,留下林晚意一人。时间一点点流逝,每一刻都无比漫长。
怀里的辣椒酱坛子似乎越来越沉。林晚意僵硬地站着,不敢坐,也不敢随意走动。
厅外偶尔有极轻的脚步声经过,都让她心惊肉跳。恐惧像冰冷的藤蔓,再次悄然缠上心头。
他会怎么处置自己?那个眼神冰冷得能冻死人的王爷……那句“当斩”还在耳边萦绕。
她开始后悔自己的冲动,后悔那不顾一切的顶撞,
后悔抱住了这坛酱却丢了整个摊子……绝望的情绪一点点啃噬着她。
就在她快要被自己的胡思乱想压垮时,门外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林晚意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猛地攥紧了怀里的坛子,指节用力到发白。
进来的却并非靖王,
而是一位穿着体面藏青色锦袍、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面容严肃的老者(赵总管)。
他手里捧着一个托盘,上面放着一卷用红绸系着的文书。
赵总管的目光在林晚意和她怀里的酱坛子上扫过,带着审视,
也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近乎怜悯的复杂。他走到林晚意面前,将托盘往前一递,
声音平板无波,听不出喜怒:“林氏晚意,王爷有命。即日起,入王府司膳房听用,
专司辣味膳食。”林晚意愣住了,眼睛猛地瞪大,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她茫然地看着托盘上那卷红绸文书,又看看赵总管那张刻板的脸。“聘……聘书?
”她下意识地重复着,声音干涩沙哑。不是锁拿下狱?不是砍头?而是……聘她当厨娘?
这峰回路转的荒谬感,让她一时反应不过来。赵总管似乎懒得解释,
只将那托盘又往前送了送,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签了它,收拾东西,
明日辰时到司膳房报到。你带来的那坛子……‘东西’,”他目光扫过林晚意怀里的粗陶坛,
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嫌弃,“一并带去。王爷……口味特殊。”说完,
不等林晚意有任何反应,赵总管放下托盘,转身便走,
留下林晚意一人对着那卷刺目的红绸聘书发呆。聘书?厨娘?专吃辣味?
几个词在她脑子里嗡嗡作响。先是拆摊的蛮横,然后是当街的羞辱威胁,
现在又丢给她一张聘书?这算什么?打一棒子给个甜枣?还是另一种更羞辱的惩罚?
把她当街抓来,关进这华丽的牢笼里,从此给他当牛做马?一股被戏弄、被轻贱的怒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