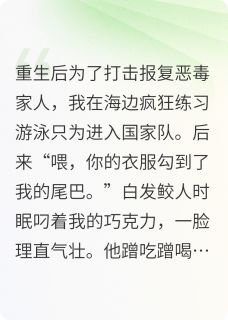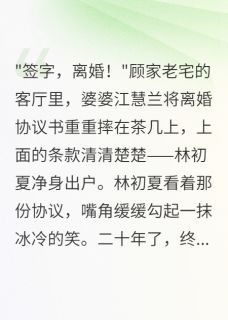##他记得所有痛苦,唯独忘了我>我和沈砚在故障电梯里初遇时,他把我护在身下。
>七年后重逢,他成了我的顶头上司,眼神却冷得像陌生人。>公司电梯再次坠落时,
他本能地护住新来的实习生。>我在医院走廊听见他助理低吼:“沈总脑部旧伤复发了!
他根本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讨厌电梯!”>翻开他从不离身的笔记本,
每一页都写满我的名字:>“今天在茶水间碰到林晚了,她没看我。”>“她的婚戒很刺眼。
”>“医生说我的记忆随时会清零...这样也好,她值得更好的未来。
”---金属摩擦的刺耳尖啸,像一把钝锯,猛地切断了电梯厢里微弱的光线。
视野骤然陷入一片令人窒息的黑暗。紧接着,是更可怕的失重感,身体被狠狠抛起,
又重重砸下,五脏六腑都仿佛移了位。失控的下坠!我喉咙里挤出一声短促的尖叫,
被巨大的恐惧扼住,整个人天旋地转,只能徒劳地伸出双手在虚空中乱抓。就在这时,
一股沉稳的力道猛地将我拽了过去。后背重重撞上冰冷的厢壁,疼痛还未炸开,
一个温热的胸膛已经覆盖下来,带着一种不由分说的强硬,
将我整个身体都圈禁在他与墙壁之间。他的手臂横亘在我颈侧,
另一只手掌牢牢护住我的后脑勺,用力按向他剧烈起伏的胸口。黑暗中,感官被无限放大。
我脸颊紧贴着他衬衫下滚烫的皮肤,急促的心跳声穿透薄薄的布料,一下下撞击着我的耳膜,
震耳欲聋。是他自己的心跳,还是我自己的?早已分不清。
他温热的呼吸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拂过我头顶的发丝。
鼻尖萦绕着一股清冽又干燥的气息,像是松林深处被阳光晒透的木屑,
混合着一丝消毒水的洁净味道,在这狭小、充满死亡威胁的空间里,
莫名地带来一点令人心安的错觉。下坠仍在持续,
每一次颠簸都让我们的身体更紧密地贴在一起。金属扭曲的**、钢缆摩擦的嘶吼,
如同地狱的序曲。每一次剧烈的震动,他箍住我的手臂就收紧一分,像最坚固的藤蔓,
死死缠住唯一的浮木。我的额头抵着他紧绷的下颌,
能清晰地感受到他每一次吞咽时喉结的滚动,以及那压抑在喉间的、沉重的喘息。
时间在恐惧中无限拉长。不知过了多久,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和令人牙酸的金属摩擦声,
电梯厢终于猛地顿住,停止了疯狂的下坠。巨大的惯性让我们狠狠撞在一起,
又狼狈地弹开少许。死一般的寂静瞬间降临,
只有两人粗重紊乱的呼吸声在狭小的空间里交织回荡。“没事了。
”他的声音在我头顶响起,低沉沙哑得厉害,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粗砺感,
还有一丝难以言喻的紧绷。圈着我的手臂却没有立刻松开,反而又收拢了一点,
像是在确认什么。我僵硬地抬起头,试图在浓稠的黑暗中看清他的轮廓,
却只能感觉到他温热的呼吸近在咫尺。一片漆黑里,唯有他身体的轮廓是清晰而坚实的依靠。
“谢…谢谢。”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几乎只剩气音。他没有回答。黑暗中,
我感觉到他的下颌似乎轻轻蹭了蹭我的发顶,一个极其细微、近乎错觉的动作。随即,
他护在我脑后的手微微动了一下,指腹不经意间擦过我的耳廓,带着灼人的热度。那一瞬间,
仿佛有微弱的电流窜过皮肤。黑暗放大了所有感官,他的温度,他的气息,
他身体传递过来的每一丝力量,都像烙印,深深地刻进这生死一线的黑暗里。
冰冷的金属壁紧贴着我的脊背,而他怀抱的方寸之地,是这片绝望中唯一的、滚烫的孤岛。
---七年。时间像一把锋利的刻刀,不动声色地削去了曾经的惊心动魄,
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带着尘埃味的印记。那个电梯里的男人,连同那生死相拥的瞬间,
早已被我小心地封存进记忆的角落,落满灰尘。直到此刻。冰冷的雨水像断线的珠子,
噼里啪啦地砸在巨大的玻璃幕墙上,蜿蜒流下,将窗外灰蒙蒙的城市切割成模糊的色块。
我端着刚冲好的咖啡,站在茶水间巨大的落地窗前,看着雨幕发呆。指尖传来的温度,
是这阴冷午后唯一的慰藉。高跟鞋清脆的回音由远及近,打破了茶水间的安静。
几个衣着光鲜的女同事簇拥着走了进来,叽叽喳喳的议论声立刻填满了空间。“快看快看!
沈总的车!刚停楼下!”一个声音带着难以抑制的兴奋。“真的?新上任的大老板?
听说帅得人神共愤?”另一个立刻接口,语气满是好奇。“岂止是帅!年轻有为!
听说还是单身!”先前那个声音拔高了几分,“刚从国外总部空降过来的,
以后就是我们的大BOSS了!沈砚,这名字就够苏的!”沈砚。
这两个字像两颗冰冷的石子,猝不及防地砸进我毫无防备的心湖,瞬间冻结了表面的平静。
指尖微微一颤,滚烫的咖啡溅出几滴,落在手背上,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我猛地缩回手,
下意识地握紧了温热的杯壁,仿佛那点温度能驱散心底骤然涌起的寒意。
心脏在胸腔里毫无章法地狂跳起来,几乎要撞碎肋骨。我强迫自己维持着背对她们的姿势,
视线死死胶着在窗外雨幕中那辆缓缓驶近的黑色轿车上。车门被穿着制服的司机恭敬地拉开。
一只锃亮的黑色皮鞋稳稳踏在湿漉漉的地面上。接着,是包裹在笔挺黑色西裤里的长腿。
男人弯身下车,动作利落而沉稳。司机迅速撑开一把宽大的黑伞,遮住他头顶倾泻的雨水。
隔着厚重的雨幕和冰冷的玻璃,我看不清他的脸,但那身形轮廓——宽阔的肩,挺拔的背脊,
那种习惯性掌控一切的姿态——像一道无声的闪电,瞬间劈开了记忆的封印。是他。
那个在黑暗和坠落中,用身体为我筑起屏障的男人。七年了。他竟然回来了。而且,
是以这样一种高高在上的方式——顶头上司。我的顶头上司。电梯门“叮”一声滑开,
打断了茶水间里热烈的议论。我深吸一口气,压下心头翻涌的惊涛骇浪,端着咖啡杯转身,
准备回自己的工位。几乎是同时,从总裁专用电梯的方向,传来一阵刻意压低的问好声。
“沈总早!”“沈总好!”人群如同摩西分海般自动向两边让开一条通道。他走了过来。
一身剪裁完美的深灰色西装,衬得他肩线愈发挺括。没有打领带,
衬衫领口随意地解开一颗纽扣,却丝毫不减迫人的气场。他的步伐从容不迫,目光平视前方,
深邃的眼眸像是封冻的寒潭,没有任何情绪起伏。
那曾经在黑暗中给予我唯一温暖和庇护的眉眼,此刻只剩下一种冰封的锐利和疏离,
仿佛能轻易穿透人心,却又吝于在其中留下任何属于人的温度。他径直走来,离我越来越近。
我甚至能闻到他身上传来的、极其淡雅的冷冽木质香调,陌生而遥远。我的脚步钉在原地,
血液似乎凝固了,四肢冰凉。脑海中闪过无数混乱的念头——他会认出我吗?
哪怕只是一个疑惑的眼神?毕竟,那个夜晚,我们曾贴得那样近,近到能听到彼此的心跳。
他的视线,终于扫了过来。没有任何停留。就像扫过一件毫无价值的摆设,
一片无关紧要的空气。那眼神冷得彻骨,没有探究,没有波澜,
只有一片彻底的、令人心寒的漠然。他甚至没有放慢脚步。带着那股冷冽的松木香风,
他与我擦肩而过,径直走向走廊深处他那间象征着权力顶峰的办公室。黑色的背影,
决绝得像一把出鞘的刀。咖啡杯壁的温度,彻底消失了。只剩下指尖一片刺骨的冰凉。
茶水间里刚才那些兴奋的议论声,此刻听在耳中,只剩下空洞的嗡嗡回响。原来,
被彻底遗忘的滋味,比七年前那场失控的下坠,更让人窒息。
---日子在一种奇异的紧绷感中滑过。沈砚,这位新上任的沈总,
如同一个精确运转的符号,完美地嵌入了公司的权力核心。他高效,冷静,决策精准,
手腕强硬。公司上下,包括那些曾对他颜值和单身身份津津乐道的女同事,提起他时,
语气里都只剩下敬畏。他像一个巨大的、无形的磁场,无声地笼罩着整个楼层。而我,
像是磁场边缘一颗被排斥的小小石子,小心翼翼地绕着他巨大的引力范围行走。
走廊里偶然的迎面相遇,大型会议上他坐在主位扫视全场的目光,
每一次都让我下意识地屏住呼吸,低下头,加快脚步。他的目光从未在我身上多停留一秒。
那电梯里的生死与共,仿佛只是我臆想出来的一场幻觉。只有一次,在茶水间门口,
我端着空杯子出来,他正拿着他的黑色保温杯走进去。空间瞬间变得无比狭窄。
我几乎是贴着门框侧身让开,指尖因为用力而泛白。他目不斜视地走进去,
肩膀与我错开的瞬间,那股熟悉的、冷冽的木质调气息再次掠过鼻尖。我僵在原地,
直到他打开饮水机接水的声音响起,才像被烫到一般,猛地逃开。他记得。
这个念头荒谬地跳出来。他记得电梯里的事,所以才会用这样冰冷的姿态,
彻底斩断任何可能被提起的过去?还是说,对他而言,那真的只是一次微不足道的职业救援,
早已在七年时光的洪流中被冲刷得干干净净?我找不到答案。答案本身似乎也毫无意义。
这天下午,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再次笼罩了城市。项目组临时需要一份紧急文件签字,
主管的目光在办公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我身上:“林晚,快!这份文件,
赶在沈总下午出差前务必请他签个字!他马上要下楼了!”心脏猛地一沉。
我捏着那份薄薄的文件,指尖冰凉,却只能硬着头皮起身,快步走向总裁办公室区域。
刚转过走廊拐角,就看到沈砚颀长的身影站在总裁专用电梯门前。他身后半步,
站着他的助理,还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设计部新来的实习生,叫苏晓,笑容甜美,
充满活力。“沈总,这次多亏您指点,那个方案客户一次就通过了!太感谢您了!
”苏晓的声音清脆悦耳,带着毫不掩饰的崇拜。沈砚侧头看了她一眼,
轮廓冷硬的侧脸似乎柔和了一瞬,极其轻微地点了下头:“是你自己思路清晰。
”语气虽然依旧平淡,却少了平日那份冰封的距离感。电梯门“叮”一声,
平滑地向两侧打开。里面空无一人,光洁的金属内壁反射着顶灯冷白的光。就在这一刹那!
脚下的地板毫无征兆地剧烈一震!头顶的灯光疯狂闪烁了几下,骤然熄灭!紧接着,
是那令人魂飞魄散的、来自地狱深处的金属扭曲断裂的巨响!“轰——!!!
”不是缓慢的下坠,而是像被一只无形的巨手狠狠扯断!整个电梯厢体发出令人牙酸的**,
以恐怖的速度向下砸去!“啊——!
”苏晓的尖叫声瞬间被淹没在巨大的失重轰鸣和金属摩擦的噪音中。
巨大的惯性把所有人都狠狠抛向电梯厢壁!文件从我手中飞脱,
纸张在狭窄的空间里疯狂翻飞。世界在眼前颠倒旋转,胃里翻江倒海。
一片混乱的尖叫声和撞击声中,时间被拉长,又被压缩成模糊的片段。
就在身体即将失控撞上冰冷厢壁的瞬间,我的视线模糊地捕捉到了沈砚的动作。
没有一丝犹豫。他的身体像一张瞬间绷紧的弓,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目标却不是离他最近、或者说,理应是他最“熟悉”的我。
他猛地扑向离他稍远、正失控尖叫着向后倒去的苏晓!手臂如同铁箍,带着不顾一切的决绝,
一把将那个吓得花容失色的女孩死死地护进怀里!用自己的后背和肩膀,将她完全覆盖,
形成一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屏障。动作快得只在视网膜上留下一道模糊的残影。那姿态,
那瞬间爆发出的保护欲,与七年前那个黑暗电梯里,将我护在身下的身影,诡异地重合了。
而我,被巨大的惯性狠狠甩向另一侧的厢壁。后背撞上冰冷的金属,发出沉闷的响声,
剧痛瞬间蔓延开来。眼前阵阵发黑,耳朵里灌满了金属的哀鸣和苏晓惊恐到变调的哭声。
身体在剧烈的颠簸和撞击中弹起又落下,每一次都像是骨头要散架。在混乱和疼痛的间隙,
我艰难地抬起头。视线穿过翻飞的纸张和闪烁不定的应急灯光,死死地钉在对面角落。
沈砚将苏晓严严实实地护在身下,他的手臂横亘在她颈侧,手掌护着她的后脑,
宽阔的后背弓起,承受着每一次剧烈的撞击。他紧抿着唇,下颌线绷得像刀锋,
额角似乎有汗珠滚落,眼神却异常沉冷,专注地护着怀里的女孩,仿佛那是他唯一的世界。
那姿态,如此熟悉。却又如此陌生。这一次,他守护的,不再是我。
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捏得血肉模糊。后背撞击的疼痛,
远不及心口那瞬间炸开的、尖锐到无法呼吸的钝痛。剧烈的震荡终于停止,
电梯厢卡在某个位置,发出垂死的喘息。应急灯发出惨淡的红光,
映照着电梯内的一片狼藉和惊魂未定的人们。苏晓在沈砚怀里瑟瑟发抖,小声啜泣着。
沈砚缓缓松开她,动作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僵硬,他低头查看她,声音低沉:“有没有受伤?
”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关切。苏晓惊魂未定地摇摇头,泪眼婆娑地看着他,
充满了劫后余生的依赖。沈砚这才抬起头,目光扫过混乱的电梯内。
他的视线掠过瘫坐在另一侧、脸色惨白、手肘擦伤流着血的助理,掠过几个惊魂未定的员工,
最后,毫无波澜地,落在了我身上。那眼神,像在看一件冰冷的、与己无关的摆设。
没有询问,没有一丝一毫的关切,只有一片深不见底的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