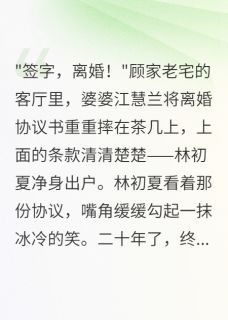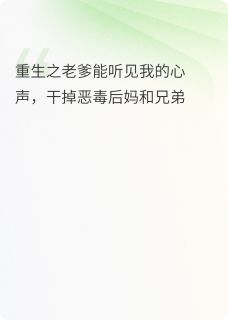
---雨水,冷得刺骨,像无数根冰冷的针,扎在黑色丧服的布料上,又迅速渗进来,
贴着皮肤往里钻。灵堂里惨白的灯光,把每一张哀戚的脸都照得发青,
如同劣质蜡像馆里的陈列品。空气沉甸甸的,压着低泣、叹息和香烛燃烧后呛人的焦糊味。
我,林欣,木然地跪在冰冷的灵前,视线穿过袅袅盘旋的青烟,落在正中央那张黑白照片上。
照片里的女人,眉眼温柔,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安抚人心的笑意。那是我的母亲。
昨天,她还笑着替我整理衣领,今天,她就成了镜框里一个单薄的影像。
心脏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
每一次跳动都牵扯着深入骨髓的钝痛和一种几乎要冲破喉咙的、冰冷的愤怒。就是这里,
上一世,同样的场景,同样的冰冷,同样的绝望开端。命运的齿轮,
又一次严丝合缝地咬合在了这个痛彻心扉的原点。
“欣儿……”一个带着浓重鼻音、刻意放得无比柔软的女声在我身侧响起,
像一条滑腻冰冷的蛇,猝不及防地缠上我的耳膜。
一只保养得宜、涂着淡粉色蔻丹的手伸了过来,轻柔地搭在我的小臂上,
带着一种不容抗拒的搀扶力道。指尖冰凉。是柳梦璃。她来了。比我记忆里第一次见她时,
更年轻,皮肤紧绷得没有一丝皱纹,精心修饰过的眉眼间,那份刻意营造的悲悯和关切,
像一层薄薄的油彩,浮在深不见底的算计之上。她身上那股甜腻得发齁的香水味,
混合着灵堂的香烛气息,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怪味。胃里一阵翻搅。
上一世最后时刻的记忆碎片,带着血腥和铁锈的腥气,
猛地冲撞进脑海——地牢里不见天日的绝望冰冷,她站在铁栏外俯视我时眼中淬毒的得意,
还有那双此刻正“温柔”搀扶着我的、涂着蔻丹的手,是如何在某个黑暗的房间里,
死死扼住我的脖颈……窒息感瞬间攫住了我,喉咙里发出无声的嘶吼。【这双手!
就是这双手!三年后!她就是用这双手掐死了我!就在父亲病床前!
】巨大的恐惧和恨意在我胸腔里疯狂冲撞,无声的尖叫在我脑子里炸开,
震得我耳膜嗡嗡作响。我几乎要控制不住地甩开她,身体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
就在那一刹那,站在灵柩另一侧的父亲——林国栋,身形极其轻微地晃动了一下。
他原本低垂着头,沉浸在巨大的悲痛里,宽阔的肩膀垮塌着,像一座被抽走了脊梁的山。
可就在我心中那无声的尖叫爆发的瞬间,他猛地抬起了头!
那双总是沉稳深邃、洞悉商海风云的眼睛,此刻布满了血丝,盛满了沉痛和疲惫。
可就在这沉痛疲惫的深处,一丝极其锐利、极其陌生的惊愕如同闪电般划过!他的目光,
像两束被无形的力量牵引的探照灯,直直地、带着一种近乎穿透的力量,
射向柳梦璃刚刚搭在我小臂上的那只手!时间仿佛凝固了一秒。
灵堂里低沉的哀乐、压抑的啜泣、香烛燃烧的噼啪声,都成了模糊的背景噪音。
整个世界只剩下父亲那双骤然变得异常清醒、异常锐利的眼睛,死死地钉在柳梦璃的手上。
柳梦璃似乎毫无所觉,她甚至更用力地、带着一种表演性质的关切,
想把我从冰冷的地上扶起来,嘴里还在柔声劝着:“欣儿,地上凉,快起来,
别让妈妈走得不放心……”父亲依旧僵立着,他的胸膛微微起伏,
喉结艰难地上下滚动了一下,那惊愕锐利的眼神深处,
翻涌起惊涛骇浪般的困惑和一种……难以置信的审视。他盯着柳梦璃,
又极其快速地瞥了我一眼,那眼神复杂得像一团纠缠不清的乱麻。
***巨大的红木门在身后无声地合拢,将外面办公区的喧嚣彻底隔绝。
林氏集团顶楼的这间董事长办公室,像一座漂浮在云端、由金钱和权力构筑的孤岛。
空气里弥漫着昂贵雪茄的余味、真皮座椅的皮革气息,还有一种无形的、令人窒息的威压。
我垂着眼,安静地站在宽大的办公桌侧后方,像个最标准的背景板,
一个被父亲带来“旁听学习”的、沉默寡言的大**。落地窗外,
城市的天际线在灰蒙蒙的雨雾里若隐若现,玻璃上凝结的水珠蜿蜒滑落,
像一道道无声的泪痕。长条形的会议桌两侧,坐满了林氏的实权人物。他们的目光,
或明或暗,如同聚光灯般落在我身上——审视,探究,带着不易察觉的轻蔑和不以为然。
一个刚死了亲妈、被父亲临时拎进公司的小丫头片子,在他们这些商场老狐狸眼里,
恐怕连只碍眼的蚊子都算不上。坐在父亲右手边最近位置的,是我的三叔,林国梁。
他今天穿了件深灰色的定制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挂着恰到好处的沉痛和凝重。
他正微微倾身,手指点着摊开在桌上的厚厚文件,用一种沉稳可靠、条理清晰的语调,
向父亲汇报着某个重要地产项目的进展。“大哥,目前资金链这块,压力确实很大,
”林国梁的语气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忧虑,手指在报表的某个数字上轻轻敲了敲,
“银行那边的贷款审批卡得严,几个承建商的预付款要求又提高了。项目一旦停滞,
每天的损失都是天文数字啊。”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全场,带着一种寻求共识的意味,
“我的建议是,动用集团总部的储备金,先顶过这三个月。等项目一期销售回款,
立刻就能填上,风险可控。”他话音刚落,会议桌另一端立刻有人附和:“是啊董事长,
三总说得在理。这项目是集团未来三年的利润增长点,拖不得!”“储备金动用流程长,
而且牵一发动全身……”也有人谨慎地提出异议。会议室里响起低低的议论声。
父亲林国栋靠在宽大的高背皮椅里,指关节习惯性地抵着太阳穴,眉头紧锁,
像是在仔细权衡林国梁的提议。他看起来比葬礼那日更加疲惫,眼下的青黑色浓重,
仿佛几天几夜未曾合眼。就在这时,办公室侧门被轻轻推开。
一股甜腻的香气先于人影飘了进来。柳梦璃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米白色套装,妆容精致,
脸上带着温婉得体的微笑,手里端着一个精致的骨瓷盅,脚步轻盈地走了进来。她的出现,
像是一道柔光,瞬间打破了会议室里紧绷沉闷的气氛。“国栋,”她的声音又软又柔,
带着天然的抚慰力量,“你昨晚又没睡好,脸色这么差。我特意让厨房炖了点参汤,
加了安神的药材,快趁热喝一点。”她旁若无人地走到父亲身边,将瓷盅轻轻放在他面前,
体贴地掀开盖子。一股浓郁的参味混合着药香弥漫开来。她俯身时,
一缕精心烫卷的发丝垂落,拂过父亲的手臂。她的动作那么自然,那么亲昵,
带着一种女主人的理所当然。【呵,好一副贤妻良母的做派。】我垂在身侧的手指,
指甲几乎要掐进掌心里。胃里那股熟悉的翻搅感又涌了上来,喉咙像是被那甜腻的香气堵住。
【慢性毒药!当归、熟地、人参……几味大补的药掺在一起,配上她特制的‘料’,
一天天蚕食心肺,神不知鬼不觉!
化验单……就夹在您书房那本《资治通鉴》第三层抽屉的旧相册里!
】我死死盯着那盅热气腾腾的汤,仿佛能看到里面翻滚着无形的、致命的毒液。
上一世父亲后期那缠绵病榻、痛苦咳血的模样,那逐渐浑浊、失去神采的眼睛,
再次清晰地浮现眼前。恨意如同冰冷的毒蛇,缠绕着我的心脏,越收越紧。“啪嗒!
”一声清脆的碎裂声,骤然打破了会议室的低语!是父亲!他那只原本抵着太阳穴的手,
不知为何猛地一抬,手肘毫无预兆地撞翻了面前那盅刚被柳梦璃掀开盖子的参汤!
滚烫的、色泽深沉的汤液猛地泼溅出来!褐色的汤汁、炖得软烂的参片和药材,
瞬间洒满了昂贵的红木桌面,流淌下来,滴落在深色的地毯上,留下深色的污迹。热气腾腾,
狼藉一片。“啊!”柳梦璃惊叫一声,下意识地后退半步,脸上那温婉得体的笑容瞬间僵住,
被猝不及防的惊吓和一丝来不及掩饰的慌乱取代。她精心描画的眼睛瞪得溜圆,
看着自己沾上几点汤汁的袖口和一片狼藉的桌面。整个会议室,死一般寂静!
所有议论声戛然而止。所有人的目光,都从被打翻的汤盅,惊愕地转向坐在主位上的林国栋。
林国栋自己也似乎愣住了。他看着满桌的狼藉,又看了看自己那只仿佛不受控制的手,
眉头拧成了一个深刻的“川”字。他脸上的疲惫似乎更深了,
还混杂着一丝难以言喻的烦躁和……一种更深沉的东西。他没有理会柳梦璃的惊呼,
没有看任何人。几秒钟令人窒息的沉默后,他那双布满血丝、却异常锐利的眼睛,
缓缓地、像两柄淬了冰的刀子,转向了我。“欣儿,”他的声音低沉沙哑,
带着一种奇异的平静,却像投入死水中的巨石,在寂静的会议室里激起千层浪,
“你……觉得呢?”嗡——我感觉脑子里嗡的一声,像是什么东西炸开了。
全身的血液似乎都涌到了脸上,又瞬间褪去,只剩下冰冷的麻木。整个会议室的目光,
那些刚才还带着轻视的目光,此刻像无数根针,齐刷刷地刺向我。
惊愕、不解、探究、怀疑……汇成一片无形的压力之网,将我死死罩住。他问我?
在董事会上?在柳梦璃精心准备的汤被打翻、场面如此难堪的时候?他问我什么?
问我怎么看这盅汤?还是……问我怎么看三叔刚才的提议?
我甚至不敢去深想他这突兀问话背后的含义。
般在我心底炸开的秘密——他能听见我的“声音”——此刻像一只冰冷的手扼住了我的喉咙。
我强迫自己抬起眼。
视线飞快地掠过父亲那双深不见底、带着某种审视和……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鼓励的眼睛?
然后扫过柳梦璃那张妆容精致却难掩惊疑和一丝阴鸷的脸,最后落在三叔林国梁身上。
他依旧端坐着,姿态沉稳,仿佛刚才的变故与他无关,但那微眯起的眼睛里,
一闪而过的精光却像毒蛇的信子。空气粘稠得如同凝固的胶水,每一秒都拉得无限漫长。
我能听到自己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的声音。【稳住……林欣,稳住!
】我在心里狠狠地对自己嘶吼,指甲更深地掐进掌心,用那点锐痛逼迫自己冷静。
脸上却迅速调整,努力挤出属于“林欣”的、那种怯懦的、没什么主见的茫然表情,
甚至还恰到好处地带上了一点被父亲突然点名而受宠若惊的惶惑。我微微垂下头,
声音放得又轻又细,带着点不知所措的颤抖:“爸……我……我不懂这些的。
您和三叔都是为集团好……”我刻意停顿了一下,像是鼓足了勇气才敢继续,
“就是……就是觉得,三叔说的那个项目……动储备金……是不是再慎重一点?
万一……万一有点什么意外呢?”我越说声音越小,头也埋得更低,
活脱脱一个未经世事、只凭直觉瞎担心的小女孩。【好险!差点就露馅了!
】心底那个声音在疯狂庆幸,【慢性毒药!当归熟地配人参,还有她特制的‘料’,
化验单就在您书房《资治通鉴》第三层抽屉的旧相册里夹着!爸,您听见了吗?!
一定要看见啊!】表面上,我依旧维持着那份怯懦和茫然,甚至因为紧张,
肩膀还微微瑟缩了一下。我飞快地抬眼偷瞄了一下父亲。林国栋脸上没有任何多余的表情。
他没有看我,也没有看任何人,只是目光沉沉地落在那片被他亲手打翻的狼藉上,
看着褐色的汤汁在红木桌面上蜿蜒流淌,慢慢渗入地毯深处。他的指节,
依旧习惯性地抵着太阳穴,只是按得更用力了,指关节泛着青白。
他周身散发出的那股低沉的气压,让整个会议室如同冰窖。柳梦璃脸上的惊疑未退,
又添了一层被忽视的委屈。她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接触到林国栋那深不可测的眼神,
又硬生生把话咽了回去,只是拿出丝巾,默默地擦拭着自己袖口和桌面。
林国梁脸上的沉稳也出现了一丝裂痕。他看着我,那眼神不再是之前的轻视,
而是带上了一种深沉的、重新评估的审视,像在打量一件突然出现、打乱棋局的未知物品。
他清了清嗓子,试图把话题拉回正轨:“大哥,欣儿还小,
不懂资金运作的风险和收益比是正常的。这个项目……”“散会。”林国栋突然开口,
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斩钉截铁的冷硬,瞬间截断了林国梁所有未出口的话。那两个字,
像两块冰砸在地上,寒气四溢。没有任何解释,没有任何多余的情绪。他猛地站起身,
动作幅度之大,带得沉重的皮椅向后滑开,发出一声刺耳的摩擦声。
他甚至没有再看那桌狼藉一眼,也没有看柳梦璃,更没有看我。
他那高大却带着浓重疲惫的身影,裹挟着一股山雨欲来的凛冽气息,
径直走向办公室那扇厚重的门,拉开,消失在了门后。留下满室死寂,
和一地(一桌)的狼藉。柳梦璃拿着丝巾的手僵在半空,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林国梁盯着那扇关上的门,眼神阴鸷得像要穿透厚厚的门板。其他与会者面面相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