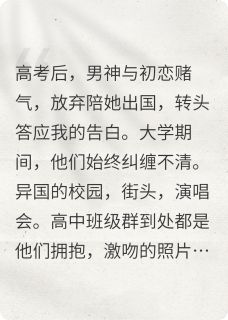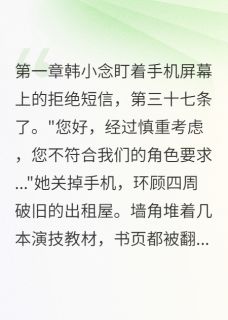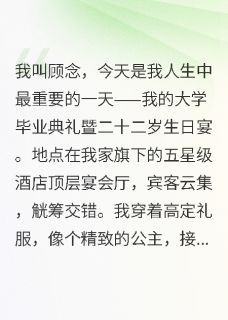灵堂内,死寂如墓。##浸猪笼?好啊(终章)冰冷的指尖抚过灵位上那凹陷的刻痕,
如同抚过一段早已冰封的、被尘灰覆盖的岁月。那滴砸落在底座上的泪,无声无息,
却仿佛带着千钧的重量,沉甸甸地压在灵堂里每一个人的心头。青娥缓缓收回了手。
指尖残留着灵位木质的粗糙和刺骨的冰凉。
她没有看陈福手中那张墨泪交融、字迹扭曲的休书,仿佛那只是一张无关紧要的废纸。
她的目光,越过供桌上跳跃的烛火,越过陈金山画像上那永恒温润的眉眼,
似乎穿透了灵堂厚重的墙壁,投向了更远、更冰冷的虚空。那张惨白如纸的脸上,
所有的悲恸、愤怒、疯狂,都已沉淀下去,只剩下一种近乎死寂的平静。
这平静比之前的歇斯底里更令人心悸,如同暴风雨后深不见底的、吞噬一切的海渊。
陈福捧着休书的手僵在半空,额角渗出细密的冷汗。族长交托的对牌,眼前这封代写的休书,
似乎都无法撼动这女人分毫。她到底要什么?就在这时,青娥的嘴唇极其微弱地翕动了一下。
无声。但陈福看懂了那个口型。“……钥……匙……”钥匙?库房钥匙?
对牌不就在她手边吗?陈福心头猛地一跳!不!不是库房钥匙!是……是那个!他猛地想起!
金山少爷……金山少爷生前最后押运的那批货!
那批价值万贯、最终葬身鹰愁涧、人货皆亡的绸缎!那批货……出发前,
金山少爷亲手将库房钥匙交给了老太太保管!
那是长房库房最深处、存放最贵重物品的库房的钥匙!
是金山少爷留下的、最后一点没被陈金宝染指的、属于他自己的东西!陈福的呼吸瞬间停滞!
他难以置信地看着青娥!她连这个都知道?!
她竟连金山少爷将钥匙交给老太太保管的细节都知晓?!
一股难以言喻的寒意再次从陈福脚底窜起。这个女人……她究竟在黑暗中窥探了多久?
谋划了多久?她今日所求的,根本不是虚妄的权力或一纸休书!
她要的是亡夫留下的、最后的、纯粹的念想!她要斩断与陈家所有肮脏的牵连,
带着属于亡夫的最后一点干净东西,离开这个吃人的魔窟!“老奴……明白!
”陈福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他不敢再有半分迟疑,立刻躬身,
“老奴这就去取!立刻去!”他几乎是跌跌撞撞地冲出了灵堂,
沉重的脚步声在死寂中格外刺耳。灵堂内,只剩下烛火幽微的噼啪声,
青娥挺立如孤松的身影,角落里如同烂泥般瘫软呜咽的王妈,
以及那两个噤若寒蝉的旁支族老。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风雨前的低气压,沉重得令人窒息。
时间在死寂中缓慢流淌。每一刻都像一个世纪般漫长。终于,陈福的身影再次出现在门口。
他跑得气喘吁吁,脸色煞白,
手里紧紧攥着一枚东西——一枚式样古朴、黄铜打造的、带着岁月磨痕的钥匙。
他快步走到青娥面前,双手将那枚钥匙奉上,姿态恭敬到了极致,
甚至带着一丝难以言喻的敬畏。
“少奶奶……钥匙……金山少爷留下的库房钥匙……老奴……取来了。
”他的声音带着喘息。青娥的目光终于从那虚空中收回,落在了那枚黄铜钥匙上。
钥匙在烛光下泛着幽暗的光泽,边缘已经被摩挲得光滑圆润,仿佛还残留着亡夫指尖的温度。
这是她夫君留下的、未被陈家污浊沾染的最后一点实物。她缓缓地、极其缓慢地伸出手。
那只枯瘦、苍白、带着薄茧的手,越过陈福恭敬奉上的双手,
直接、稳稳地握住了那枚冰冷的钥匙。冰冷的金属触感瞬间传递到掌心,
带来一丝清晰的刺痛。她将钥匙紧紧攥在手心,坚硬的棱角硌着皮肉,
带来一种奇异的、令人心安的实在感。仿佛握住了亡夫最后一点存在的证明,
握住了通往解脱之路的凭证。做完这一切,她仿佛耗尽了最后支撑身体的力气。
挺直的脊梁再也无法维持,身体猛地一晃!“呃……”一声压抑的闷哼从唇间溢出,
带着无法承受的剧痛。膝盖处如同炸裂般的痛楚瞬间席卷全身!眼前阵阵发黑,金星乱冒!
她再也支撑不住,身体如同断线的风筝,软软地向后倒去!“少奶奶!”“快!”惊呼声中,
旁边的粗实丫头和陈福手忙脚乱地扶住了她下滑的身体。
青娥的脸色在瞬间褪尽最后一丝血色,变得如同透明的薄纸,
冷汗如同溪流般从额角、鬓发间涌出,瞬间浸透了粗布衣领。她双眼紧闭,
长长的睫毛如同脆弱的蝶翼,覆盖在毫无生气的眼睑上,
只有胸口极其微弱的起伏证明她还活着。“快!抬回房!王大夫!快去请王大夫!
”陈福的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惊惶。族长千叮万嘱要保住的孩子!绝不能有失!
***陈府最偏僻的小院,再次被浓重得化不开的苦涩药味笼罩。
王大夫的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结,额头上全是细密的汗珠。他刚刚再次施针完毕,
又撬开青娥的牙关,灌下了一碗浓黑如墨、散发着奇异腥气的药汁。“如何?
”陈福的声音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颤抖,眼睛死死盯着王大夫。
王大夫收回搭在青娥腕间的手指,长叹一声,疲惫地摇了摇头:“凶险……太凶险了!
悲恸过度,心力交瘁,旧伤复发,寒气入骨……这胎气……已是悬于一线!方才那碗药,
是虎狼之剂,强行吊命固元,但也只是……尽人事,听天命了!
”他看了一眼床上气息微弱得如同游丝的青娥,又看了看陈福,“陈管家,
族长那里……您还是……早做准备吧。”“准备”二字,如同冰冷的铁锤,
狠狠砸在陈福心上。他脸色瞬间灰败下去,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早做准备?
准备什么?准备一尸两命?准备陈家长房最后的希望彻底破灭?族长……能承受得住吗?
王大夫摇摇头,不再多言,收拾药箱,拖着沉重的脚步离开了。屋内,
只剩下令人窒息的死寂和浓得让人作呕的药味。昏黄的油灯将影子拉扯得扭曲变形。
王妈不知何时又如同幽灵般缩回了床尾的阴影里,垂着头,像一尊没有生命的石像。
只有偶尔从她袖口传出的、极其细微的、指甲掐入掌心的声音,证明她还活着。
陈福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在狭小的屋内来回踱步,每一步都沉重异常。他不敢离开,
又不知该如何是好。目光一次次扫过床上那毫无生气的靛蓝色身影,
每一次都让他心头沉下去一分。那枚黄铜钥匙,依旧被她紧紧攥在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