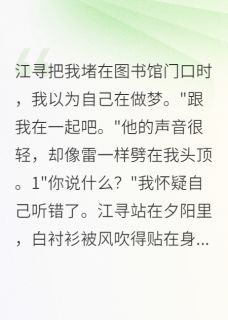颁奖礼上,我踮脚吻了影帝谢聿行:“谢老师,玩玩?”闪光灯淹没了他苍白的脸。
全网都在骂我蹭他热度,
戒昏迷不醒:“晚晚…快逃…”我这才撕开血淋淋的真相:当年他推开我说“玩玩而已”时,
身后十吨重的货车正朝他撞来。————————镁光灯像不要钱的碎钻,
噼里啪啦砸在脸上,几乎要把我的视网膜灼穿。
空气里是高级香水、定型发胶和一种名为“名利”的、滚烫的荷尔蒙混合发酵的味道。
金鼎奖颁奖礼现场,衣香鬓影,浮光掠金,人人脸上挂着精心调试过的、无懈可击的弧度。
我,姜晚,一身烈焰般的高定红裙,踩着七寸的细高跟,像把出鞘的利刃,
精准地切开这片华丽的浮沫,目标明确地走向红毯尽头那个被簇拥着的男人。谢聿行。
三年了。这个名字像根淬了毒的针,深扎在我心口最烂的那块腐肉里,不动则已,
一动就是锥心刺骨的钝痛。他依旧是人群的绝对焦点。一身剪裁完美的墨色西装,
衬得他肩宽腿长,身姿挺拔如松。那张被媒体誉为“女娲毕设”的脸上,没什么多余的表情,
只一双深邃的眼眸,在流转的灯光下沉淀着旁人看不懂的暗色,平静地注视着我的靠近。
他周围那些刚刚还谈笑风生的名流大腕,此刻都默契地屏息敛声,
眼神在我和他之间微妙地逡巡,空气里绷紧了一根无形的弦。三年前那个暴雨倾盆的夜晚,
他撑着伞,站在我家楼下昏黄的路灯里,雨水顺着他紧绷的下颌线滑落,砸在地上,
也砸碎了我所有关于未来的粉色泡泡。“姜晚,”他的声音比那夜的雨水更冷,穿透雨幕,
清晰地刺进我耳膜,“我们之间,不过是我一时兴起,玩玩而已。”“玩玩而已。
”这四个字,成了我此后一千多个日夜挥之不去的梦魇,
也成了钉死我在娱乐圈“痴心妄想”、“不自量力”标签的耻辱柱。
我成了所有人茶余饭后的笑料,那个妄图攀附影帝却被无情踩进泥里的十八线。那晚之后,
他像人间蒸发。而我,带着心口那个被他亲手捅出的血窟窿,一头扎进了最苦的剧组,
最累的行程,最深的泥潭。我用近乎自虐的方式打磨自己,
把所有的痛、恨和不甘都淬炼成了向上攀爬的阶梯。血泪模糊了视线,
我就擦干再走;流言蜚语如影随形,我就把它们踩在脚下当垫脚石。三年后的今天,
我姜晚的名字,终于和他谢聿行一起,被提名为金鼎奖最佳男女主角。从泥沼到云端,
我爬回来了,带着满身的荆棘和淬过火的锋芒。高跟鞋敲击光洁地面的声音清脆而富有节奏,
如同战鼓。我在他面前站定,
距离近得能闻到他身上那点熟悉的、清冽如雪后松林般的冷调木质香。
这味道曾经让我安心沉溺,如今只让我胃里翻江倒海。
周围的抽气声和快门声瞬间达到了顶峰。无数镜头贪婪地对准我们,
捕捉着这堪称世纪同框的每一帧。我微微歪头,红唇勾起一个毫无温度、堪称完美的弧度,
眼神却像淬了冰的刀子,直直地剜进他沉静的眼底。三年的恨意、三年的委屈、三年的孤勇,
在这一刻找到了唯一的宣泄口。然后,在所有人惊愕到失语的目光中,
在足以闪瞎人眼的疯狂闪光灯下,我踮起脚尖。冰凉的、带着红酒气息的唇瓣,
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决绝,重重地印在他微抿的、没什么血色的薄唇上。一触即焚。
时间仿佛被按下了暂停键。世界安静得可怕,
只剩下我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和血液冲刷耳膜的轰鸣。我退开一步,
无视他瞬间僵直的身体和眼底一闪而逝、快得抓不住的复杂暗流——也许是惊愕,
也许是厌恶,管他呢。我迎着他骤然深沉的目光,红唇开合,声音不高,却像淬了毒的冰凌,
清晰地穿透这片诡异的死寂,砸进在场每一个竖起耳朵的人心里:“谢老师,
”我笑得风情万种,眼神却冷得能冻死人,“玩玩?”……“玩玩”两个字,
像一颗深水炸弹,把整个互联网炸得底朝天。#姜晚强吻谢聿行#的词条后面,
跟着一个刺眼的、血红的“爆”字,像一块耻辱的烙印,死死焊在我的名字旁边。点进去,
是铺天盖地的口诛笔伐,恶意的浪潮几乎要将我吞没。【****!姜晚疯了?!
当众强吻谢影帝?!这操作太骚了吧!】【年度最大碰瓷现场!为了热度脸都不要了?
谢影帝实惨!】【姜婊滚出娱乐圈!三年前倒贴不成现在又来?手段真下作!】【呵呵,
我就说当年谢影帝甩她甩得对!这种为了上位不择手段的心机婊,活该!
】【蹭热度蹭到这份上,姜晚真是刷新下限了!心疼我谢哥!
】手机屏幕幽幽的光映着我没什么表情的脸。经纪人林姐焦头烂额地在旁边踱步,
电话一个接一个,全是媒体追问和合作方施压,语气一次比一次暴躁。“姜晚!
你到底有没有脑子?!”她终于挂了电话,把手机“啪”地拍在化妆台上,胸口剧烈起伏,
“你知道现在外面都骂成什么样了吗?‘玩玩’?亏你说得出口!
你知不知道谢聿行是什么地位?他背后的资本动动手指头就能把你碾死!
你这三年辛辛苦苦爬上来,就为了今天这一下全毁掉?!”化妆间里冷气很足,
我却觉得心口那点被他亲手浇灭的余烬,又被这些铺天盖地的恶意扇得死灰复燃,
烧得五脏六腑都疼。我盯着镜子里那个穿着红裙、妆容精致却眼神空洞的自己,
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留下几个月牙形的红痕。“林姐,”我开口,声音有点哑,却异常平静,
“我的通告,照旧。该拍的戏,一场不落。”“你……”林姐被我噎住,
恨铁不成钢地瞪着我,“行!你硬气!我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谢聿行那边到现在没吭声,
你以为是什么好兆头?那是暴风雨前的宁静!”暴风雨前的宁静?我扯了扯嘴角。
我倒是希望他来场暴风雨,把我彻底掀翻在地,也好过现在这样,像个无声的幽灵,
任由我被千夫所指。接下来的日子,我成了整个娱乐圈的“瘟疫源”。片场里,
那些曾经对我笑脸相迎的演员、工作人员,眼神都变得躲闪而微妙,背着我窃窃私语。
合作的品牌方委婉地表示“需要重新评估”,原本十拿九稳的高奢代言也黄了。
网上更是骂声不绝,我微博评论区彻底沦陷,点开就是一片污言秽语的海洋。
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没有痛觉的工作机器。在镜头前,我是光芒四射的顶流姜晚,眼神锐利,
气场全开;镜头一关,所有的疲惫和心口那点细密的、连绵不绝的抽痛才汹涌而至。
我用浓妆掩盖眼底的青黑,用高强度的拍摄麻痹自己。谢聿行那边,依旧沉默得像一潭死水。
他的沉默,比任何反击都更让我感到一种被彻底无视的、冰冷的羞辱。
这天拍的是场重头爆破戏。废弃的化工厂场景搭建得阴森逼真,
空气里弥漫着灰尘和铁锈的味道。我穿着特制的防护服,站在指定位置,
听着爆破组在对讲机里做最后的确认。心里那点不安,像藤蔓一样悄悄缠绕上来。
“各组准备!五、四、三……”倒计时的声音像催命的鼓点。就在“二”字落下的瞬间,
我的视线无意中扫过远处一个堆满化工原料桶的高台。瞳孔骤然一缩!
一个穿着场务马甲、戴着鸭舌帽的身影,正鬼鬼祟祟地蹲在那里,
手里拿着一截明显是剪断的电线,正试图往旁边一个**的、火花四溅的配电箱里塞!
“小心——!”我的尖叫几乎破音,身体比脑子更快地朝旁边猛地扑去!“轰——!!!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几乎撕裂耳膜!不是预设的爆破点!
一股灼热的气浪带着毁灭性的力量从高台方向猛地炸开!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巨大的冲击力将我狠狠掀飞出去,后背重重撞在冰冷的钢铁支架上,喉头一甜,
五脏六腑都像移了位。世界瞬间被刺耳的警报、惊恐的尖叫和呛人的浓烟淹没。“姜晚!
”“快救人!”“爆破点失控了!有东西提前炸了!”混乱中,
我被人七手八脚地从地上拖起来。后背剧痛,耳朵嗡嗡作响,眼前一片模糊的烟尘。
有人在大喊着叫救护车,有人在哭喊。“谢老师!谢老师还在里面!
”一个场务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像一把冰冷的锥子,狠狠扎进我混沌的意识!谢聿行?!
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瞬间停止了跳动!他不是今天的通告!他怎么会在这里?
!一股巨大的、冰冷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比三年前听到那句“玩玩而已”时更甚!
我猛地推开搀扶我的人,不顾后背撕裂般的疼痛和呛人的浓烟,
跌跌撞撞地朝着爆炸的中心、那个火光未熄的高台方向冲去!“姜晚!你疯了!回来!
”林姐惊恐的尖叫被我甩在身后。视野里一片狼藉,扭曲的钢铁支架,燃烧的布景碎片,
呛得人睁不开眼的黑烟。消防水龙带嘶吼着喷出白色的水柱,与火焰搏斗。
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在混乱中穿梭。我像没头的苍蝇,在混乱和废墟里踉跄着寻找,
心沉到了冰点,恐惧像冰冷的潮水淹没头顶。就在绝望几乎要将我吞噬的时候,
前方隔离带外,刺耳的救护车鸣笛由远及近。几个医护人员正小心翼翼地将一副担架抬上车。
担架上的人……即使隔着混乱的人群和浓烟,即使他脸上布满烟尘和血污,
我依然一眼就认了出来!是谢聿行!他毫无知觉地躺在那里,脸色是骇人的惨白,
墨色的西装外套被撕裂,露出里面染血的衬衫。一只手臂无力地垂落在担架边缘。
就在担架即将被推入救护车后门的刹那,一阵风吹散了些许浓烟。我清晰地看到,
他那沾满灰尘和暗红血迹、似乎已失去所有力气的手指,竟以一种近乎痉挛的姿态,
死死地、死死地攥着一样东西!一枚戒指。
一枚款式极其简单、甚至有些老旧的铂金素圈戒指。边缘已经磨损得有些发亮,
在污浊和血色中,固执地折射出一点微弱却刺眼的光芒。那枚戒指……我认得!那是三年前,
我们最甜蜜的时候,一起在街角小店买的。很便宜,不是名牌,甚至没有钻石。他说,
等以后有钱了,再给我换鸽子蛋。我笑着说,这个就很好,我喜欢。后来分手那晚,
我疯了一样找过,没找到。
戒……被他死死攥在濒死的手心……“晚晚……”一个极其微弱、破碎得几乎听不见的气音,
从他毫无血色的唇间艰难地溢出,像风中即将熄灭的烛火,“快……逃……”快逃?
这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心上!三年前那个雨夜,他推开我时,
已”……还有此刻他昏迷中绝望的呓语……一个极其可怕、却又瞬间贯通了所有疑点的念头,
如同闪电般劈开我混乱的脑海!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冻结!我猛地转身,
像疯了一样冲向片场外!后背的剧痛和身体的虚脱感被一股更强大的力量死死压制下去。
“林姐!车!立刻去市一院!联系陈院长!我要谢聿行所有的病历!所有的!包括三年前的!
”我的声音嘶哑尖锐,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近乎疯狂的决绝,“立刻!马上!
”市一院顶层的VIP病房区,弥漫着消毒水冰冷而刺鼻的味道,
安静得能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厚重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只有仪器发出规律而冰冷的滴答声,在死寂的空间里回响,像生命的倒计时。
谢聿行躺在病床上,身上连着各种管子,脸色比雪白的床单还要惨白几分,
脆弱得仿佛一碰即碎。那枚染血的旧戒指,被我紧紧攥在手心,冰冷的金属硌着皮肉,
却远不及我心口那份寒意。病房门被无声推开。林姐脸色凝重得像结了一层冰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