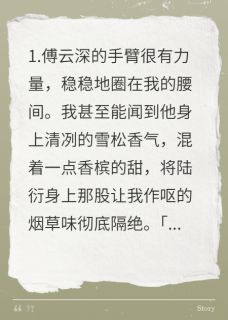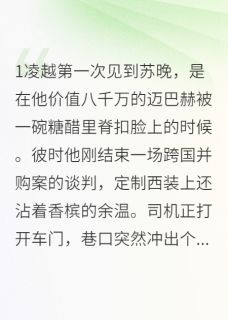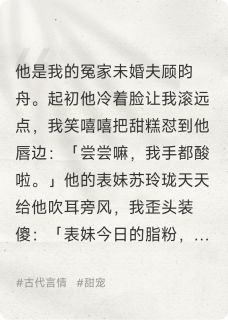
他是我的冤家未婚夫顾昀舟。起初他冷着脸让我滚远点,
我笑嘻嘻把甜糕怼到他唇边:「尝尝嘛,我手都酸啦。」他的表妹苏玲珑天天给他吹耳旁风,
我歪头装傻:「表妹今日的脂粉,瞧着像刚挖过煤?」1我是将军府的小**沈清辞,
他是永宁侯世子顾昀舟,我的……冤家未婚夫。第一次见面,大概是我五岁,他七岁。
我爹和他爹在花厅里喝茶,谈笑风生,定下了这桩娃娃亲。
小小的顾昀舟板着一张玉雪可爱的脸,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看我的眼神,
活像我看厨房里那只总想偷我糖糕的肥猫——充满了嫌弃和不耐烦。哼!他懂什么?
本**从小就知道,好看的东西,多看几眼,心情总会变好的。他长得那么好看,
比年画娃娃还精致,就算冷着脸,那也是顶顶好看的冷脸!我爹娘总说我心大,这话真没错。
顾昀舟那点冷言冷语?啧,像春日里最后那点薄冰,太阳一晒就没了,半点不往心里去。
他越是想用那张冷脸冻退我,我沈清辞就偏要凑上去,用我的笑容把他烤化!
机会很快就来了。侯府办春日宴,我特意起了个大早,挑了最鲜亮的鹅黄襦裙,
像只刚破茧的小蝴蝶,扑棱棱就飞进了永宁侯府的花园。远远地,我就瞧见他了。顾昀舟。
他独自站在一株开得正盛的玉兰树下,身姿挺拔如青松,
阳光透过稀疏的花瓣落在他月白的锦袍上,清冷又孤高。啧啧,真真是画里走出来的人儿,
就是那表情……嗯,有点煞风景。我捏紧了手里刚出锅、还温热的芙蓉甜糕,
调整出最甜的笑容,哒哒哒就冲了过去。「昀舟哥哥!」声音脆生生,带着十二分的甜腻。
他闻声侧过头,眉头果然立刻蹙了起来,那双漂亮却冷淡的凤眼扫过我,
薄唇微启:「沈**。」声音也是凉的,没半点温度。「请自重。」又是这句!
我耳朵都要听出茧子了!心里的小人翻了个白眼,脸上笑容却更灿烂,
像朵迎着太阳的向日葵。我不管不顾地凑得更近,几乎能闻到他身上清冽的松针气息。
手腕一抬,油纸包着的甜糕就精准地怼到了他紧抿的薄唇边。「尝尝嘛!我特意带来的!」
我眨巴着眼睛,使出浑身解数,声音又软又糯,带着点撒娇的颤音,「刚出锅,可香可软啦!
你看,」我把另一只空着的手伸到他眼前,故意晃了晃,「拎了一路,手都酸酸的呢!」
指尖微微蜷着,做出很累的样子。顾昀舟明显僵住了。
他的视线在我满是期待的脸和我指尖那块冒着热气的、莹白软糯的甜糕之间来回扫了一下。
我看见他那形状优美的喉结,极其轻微地滚动了一下。哈!有戏!
我就知道没人能抵抗刚出炉甜点的诱惑,尤其是本**亲手奉上的!他长长的睫毛垂下来,
遮住了眼底的情绪,似乎在极力忍耐。那副挣扎的样子,看得我差点笑出声。
僵持了大概有……嗯,三息?或者五息?他终于极其缓慢、极其不情愿地,微微张开了嘴。
成了!我眼疾手快,趁着他唇缝开启的那一刹那,手腕灵巧地一递,
一小块温软的甜糕就塞了进去。指尖不可避免地蹭过他微凉的下唇,
那触感……像上好的冷玉,让我心尖也跟着莫名地麻了一下。他猛地闭紧了嘴,
腮帮子微微鼓起一块,被迫咀嚼着。那张万年冰封的俊脸上,飞快地掠过一丝错愕,
随即是浓浓的羞恼。他的耳根,在阳光底下,一点一点,慢慢地染上了薄薄的绯色,
像天边初绽的霞。真好看啊。我盯着他那抹绯红,心里乐开了花,比吃了十块甜糕还甜。
「沈清辞!」他含糊地低吼,带着被冒犯的怒气,却又因为嘴里含着东西,
气势莫名短了一大截,听着竟有几分……嗯,奶凶奶凶的?我噗嗤一声笑出来,
赶紧用手捂住嘴,眼睛弯成了月牙:「好吃吧?甜不甜?我就说我的手艺……」话没说完,
他像是再也无法忍受,猛地转过身,只留给我一个清冷决绝、甚至有点落荒而逃意味的背影。
那月白的袍角在玉兰花下划过一道利落的弧线。2看着他仓促离去的背影,我站在原地,
捏了捏自己还残留着他唇上微凉触感的指尖,心里的小人得意地叉起了腰。首战告捷!
顾昀舟,你跑不掉的!顾昀舟这块冰,是没那么好啃的。就在我以为甜糕攻势初见成效,
能稍稍融化他一点的时候,他那位好表妹,苏玲珑,出场了。
像朵精心培育、随时准备攀附的菟丝花,柔弱无骨,又带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黏腻。
每次我去侯府,十次里有八次能“偶遇”她。她总能找到各种理由,像块甩不掉的牛皮糖,
黏在顾昀舟身边。不是「表哥,玲珑新得了本琴谱,有几处不明,可否请教?」就是「表哥,
这莲子羹是玲珑亲手熬的,你尝尝合不合口味?」声音那个婉转,那个娇柔,
听得我后槽牙有点发酸。顾昀舟嘛,对她倒也说不上多热络,但碍于亲戚情面,
基本保持着礼貌性的点头和应声。可这落在苏玲珑眼里,大概就成了默许和鼓励?
她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那天午后,我提着一小坛我爹珍藏的梅子酿,
打算去“慰问”一下据说在书房苦读的世子爷。刚走到回廊拐角,
就听见了苏玲珑那刻意压低、却又能让我听得清清楚楚的声音。「……表哥,
你性子也太好了些。」她语气里充满了替顾昀舟不值的委屈,「沈**她……唉,
我知道这话不该我说,可她到底是武将之女,行事未免太过……太过不拘小节了些。
上次在花园,当着那么多下人的面就……就那样凑近表哥,实在有失体统。旁人看了,
议论起来,对表哥的清誉……」我脚步一顿,抱着酒坛子,倚在廊柱后面,饶有兴致地听着。
哟,告状告到我头上来了?还“有失体统”?本**光明正大看自家未婚夫,
碍着你苏表妹什么事了?我悄悄探出半个脑袋。顾昀舟背对着我,站在廊下,
身影依旧挺拔清冷。苏玲珑站在他侧后方半步,微微仰着脸,
一副楚楚可怜、为他着想的模样。啧,这角度选得真好,阳光打在她脸上,
显得格外柔弱无辜。顾昀舟没说话,只是侧脸的线条似乎绷得更紧了些。苏玲珑见状,
像是受到了鼓舞,声音更添了几分忧虑:「而且,我听说……沈**在府里,
对下人也是呼来喝去,脾气大得很呢。表哥这般清风朗月的人物,
日后若真……岂不是要受委屈?」她小心翼翼地觑着顾昀舟的脸色,「表哥,
你……真的不觉得这桩婚事,太委屈你了吗?」好家伙!编排完我的举止,
又开始攻击我的品行了?还“委屈”顾昀舟?一股小火苗蹭地一下就从我心底窜了起来。
想撬我墙角?还使这种上不得台面的阴招?我深吸一口气,调整好表情,抱着酒坛子,
像只欢快的小鹿一样,脚步轻快地蹦跶了出去。「昀舟哥哥!」我声音清脆,
带着十足的惊喜,仿佛才刚看见他们,「咦,表妹也在呀?」顾昀舟闻声转过身,
眉头习惯性地微蹙。苏玲珑则像是被吓了一跳,脸上那点楚楚可怜瞬间僵住,
闪过一丝被抓包的慌乱,但很快又强自镇定下来,挤出一个温婉的笑容:「沈姐姐。」
我几步走到他们面前,目光毫不避讳地落在苏玲珑脸上,上上下下打量了她一番,然后,
露出了一个极其天真、极其无辜的笑容。「表妹今日……气色瞧着不大好呀?」我歪着头,
语气满是真诚的关切,大眼睛忽闪忽闪的,「这脸上抹的什么粉?怎么瞧着……」
我故意顿了顿,凑近了一点,像在仔细研究,「灰扑扑的?怪怪的。」苏玲珑的脸瞬间涨红,
连带着脖子都红了。她下意识地抬手想摸自己的脸,又猛地顿住,
表情尴尬至极:「沈姐姐说笑了……我、我用的就是寻常的珍珠粉……」「哦——」
我拖长了调子,恍然大悟地点点头,笑容越发灿烂无害,「珍珠粉呀?
我还以为是……嗯……」我故意眨眨眼,声音压低一点点,带着点促狭的调皮,
「刚从灶膛里扒拉出来的草木灰呢!表妹下次可要挑些好的用,不然旁人瞧见了,
还以为表妹勤快,亲自去挖煤了呢!」噗嗤——我发誓,
我绝对听到了顾昀舟那边传来一声极轻、极快的气音,像是……没忍住的笑?
等我飞快地转头去看他,他又恢复了那副八风不动的冰山脸,仿佛刚才那声是我的错觉。
只是……那紧抿的唇角,似乎微微向上弯起了一个极其微小、几乎看不见的弧度?
苏玲珑的脸已经红得快要滴血了,手指死死绞着帕子,嘴唇哆嗦着,那句「表哥你看她!」
堵在喉咙里,愣是没脸说出来。她狠狠地剜了我一眼,那眼神里的怨毒几乎要凝成实质,
最终只能一跺脚,带着一身快要实质化的怨气,匆匆转身跑了,背影都透着狼狈。
回廊里只剩下我和顾昀舟。我抱着酒坛子,转头看向他,
脸上是得逞后毫不掩饰的、狡黠又灿烂的笑容,像只偷吃了蜜糖的小狐狸。
我冲他扬了扬下巴,语气得意洋洋:「怎么样?我帮你赶走一只聒噪的雀儿,
是不是该谢谢我呀?」顾昀舟的目光落在我脸上,那眼神有些复杂,不再是纯粹的冰冷,
里面似乎掺杂了点别的什么,像是……审视?探究?还有一丝……无奈?他沉默了几秒,
最终只是淡淡地扫了我怀里的酒坛一眼,声音依旧没什么起伏:「沈**,自重。」
又是这句!不过这次,他说完这句万年不变的台词,却没有像往常一样立刻转身离开。
他站在原地,目光在我脸上停留的时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长那么一点点。
阳光穿过回廊的花窗,在他清俊的侧脸上投下斑驳的光影。我抱着酒坛,
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有点快的心跳声。咚,咚,咚。奇怪,
明明刚才怼苏玲珑的时候还气势十足,怎么现在被他这样看着,反而有点……不自在起来?
他薄唇微动,似乎想说什么。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少喝点。」
他终于又吐出三个字,语气还是硬邦邦的,说完,才像完成什么任务似的,转身拂袖走了。
我愣在原地,看着他月白的衣角消失在回廊尽头,抱着酒坛子的手紧了紧。少喝点?
他这是在……管我?心里那点小小的不自在,
瞬间被一股巨大的、甜滋滋的暖流冲得七零八落。我低头看着怀里沉甸甸的梅子酿,
忍不住把脸贴到冰凉的坛壁上蹭了蹭,吃吃地笑起来。顾昀舟,你完了。你露馅了你知道吗?
3日子像掺了蜜糖的流水,甜丝丝地往前淌。顾昀舟这块冰,
在我坚持不懈的“小火慢炖”下,似乎终于开始从内部融化了。
虽然他还是那副冷冷淡淡、惜字如金的样子,但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比如,
我去找他,他不会再像避瘟神一样立刻走开,而是皱着眉,一副“真拿你没办法”的样子,
任由我在旁边叽叽喳喳,偶尔还会赏脸“嗯”一声表示在听。比如,
我“不小心”把墨汁甩到他价值不菲的宣纸上,他捏着眉心,脸色黑得像锅底,
却只是咬牙切齿地说一句「沈清辞!」,然后默默换一张纸重写,竟然没把我丢出去。
再比如……那日我去马场找他,他正独自驯一匹性子极烈的枣红马。那马尥蹶子,
扬起一阵沙尘。我下意识地用手挡在眼前,咳嗽了两声。等我放下手,
发现他不知何时已经勒马停在了我面前几步远的地方。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额角有薄汗,
气息微促,目光沉沉地落在我脸上沾到的几点尘土上。他没说话,只是沉默地看了几息,
然后……从怀里掏出一方素净的帕子,动作有点生硬,甚至带着点不耐烦的意味,
直接丢了过来。那帕子不偏不倚,正好盖在我脸上。「擦干净。」
他的声音混在马场喧嚣的风里,依旧冷硬,「脏死了。」
我手忙脚乱地把帕子从脸上扒拉下来,那帕子带着他身上特有的清冽松针气息,
还有一丝驯马后的热意。我捏着帕子,看着他策马远去的背影,
那抹月白在飞扬的尘土中格外清晰。我低头,把脸埋进那方还带着他体温的帕子里,
深深吸了一口气。唔……真香。心里的小人已经开始转着圈圈跳舞了。这细微的变化,
像投入湖面的小石子,激起的涟漪大概只有我这个整天围着他转的人才能察觉。然而,
落在某些人眼里,却如同惊涛骇浪。苏玲珑出现的频率更高了。
她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柔柔弱弱地黏着顾昀舟告我的状,更多的时候,
她只是沉默地站在不远处,
用一种复杂到极点的眼神看着我和顾昀舟之间那一点点微妙的互动。那眼神里有嫉妒,
有不甘,有怨毒,还有一种……越来越浓烈的挣扎和恐慌?
像是精心守护的珍宝被人一点点撬开了外壳,露出了里面不属于她的光华。她那眼神,
看得我后背偶尔会莫名地窜起一丝凉意。像被阴暗处伺机而动的毒蛇盯上。这天,
天气有些阴沉,铅灰色的云层沉甸甸地压着,空气闷得让人喘不过气。
我应顾昀舟母亲——永宁侯夫人之邀,过府来陪她说话解闷。侯夫人性子温婉,待我极好,
拉着我说了好一会儿家常,又赏了我几匹新到的苏锦。从侯夫人院子里出来,我心情不错,
盘算着用这苏锦给顾昀舟做点什么好。荷包?他好像从来不戴。扇套?
好像也用不上……正低头琢磨着,刚走到一处僻静的假山旁,
一个人影突兀地拦住了我的去路。是苏玲珑。她今天穿了一身素净的月白襦裙,
脸色却比衣裳还要苍白几分,嘴唇抿得死紧,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
里面翻涌的情绪浓烈得近乎疯狂。我脚步一顿,心里那点轻松愉快瞬间消散,警惕起来。
「表妹?」我面上不动声色,甚至还挂着一丝惯常的、无懈可击的甜笑,「有事?」
她没有立刻说话,胸口剧烈地起伏着,像是在极力压抑着什么。那双眼睛死死地锁住我,
里面充满了怨毒和不甘,还有一种……近乎绝望的挣扎。她死死地咬着下唇,直到唇瓣泛白,
渗出血丝。「沈清辞……」她的声音嘶哑,带着一种玉石俱焚般的恨意,
「你得意不了多久了!」这话说得没头没脑,我眉头微挑:「哦?表妹这话是什么意思?」
她像是被我的平静激怒了,往前逼近一步,
压低的声音带着毒蛇般的嘶嘶寒意:「你真以为表哥对你有点好脸色,
你就能稳坐世子妃的位子?做梦!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有多少人恨不得你立刻消失!」
我的心猛地一沉。她这话……不仅仅是嫉妒的发泄!「谁?」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声音冷了下来,「谁恨不得我消失?」苏玲珑的眼神剧烈地闪烁起来,那浓烈的恨意中,
挣扎的神色更重了。她似乎想说什么,张了张嘴,却又猛地顿住,脸上掠过一丝极深的恐惧,
像是想起了什么极其可怕的事情。她猛地后退一步,用力摇头,眼神慌乱地躲闪着我的逼视。
「我……我不知道!你别问我!」她像是被烫到一样,语无伦次,
「我只是……只是好心提醒你!最近……最近没事少出门!尤其是……尤其是去城西那片!」
她几乎是吼出最后一句,声音尖锐刺耳,带着一种崩溃般的绝望。说完,
她再也不敢看我一眼,提着裙子,像身后有恶鬼在追一样,跌跌撞撞地跑开了,
很快消失在假山后。城西?我站在原地,看着苏玲珑消失的方向,
刚才那点轻松愉悦的心情荡然无存,心口像是被一块冰冷的石头堵住,沉甸甸地往下坠。
铅灰色的天空压得更低了,连带着周遭的空气都凝固了几分,沉闷得让人窒息。
她那恐惧的眼神,那句没头没尾却充满恶意的警告,还有那句突兀的「城西」
……像几根冰冷的毒刺,猝不及防地扎进了我原本甜腻平静的生活里。4不对劲。很不对劲。
苏玲珑那句带着毒刺的警告,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我心头。城西……那地方鱼龙混杂,
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我平日里去得极少。她特意提到那里,绝非空穴来风。接下来的几天,
我变得格外谨慎。连去永宁侯府,都下意识地避开了那些僻静的小路,尽量挑人多的地方走。
心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看谁都像带着三分可疑。顾昀舟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异常。
有次我在他书房里看书,眼神却总是不由自主地瞟向窗外,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衣带。
他放下手中的笔,抬眼看我,眉头微蹙:「心神不宁的,怎么了?」我回过神,
对上他那双清冷的凤眼。不知怎的,苏玲珑那张充满恐惧和怨毒的脸又浮现在眼前。告诉她?
说苏玲珑警告我城西有危险?他会信吗?会不会觉得是我在故意编排他的好表妹?毕竟,
苏玲珑在他面前,永远是那副楚楚可怜、温婉无害的样子。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我扯出一个有点勉强的笑,习惯性地想用撒娇掩饰过去:「没什么呀,
就是……就是昨晚没睡好嘛。」我凑过去,把下巴搁在他宽大的书案边缘,眨巴着眼睛看他,
「昀舟哥哥,你这里的墨好香,是什么墨呀?」他盯着我看了几秒,
那眼神锐利得像能穿透人心。我心里有点发虚,下意识地垂下眼睫,
手指在光滑的案面上画着圈圈。他没有追问,只是淡淡地「嗯」了一声,重新拿起笔。
可我却感觉,那道审视的目光在我头顶停留了许久,才缓缓移开。这种无形的压力,
加上暗处未知的危险,让我这几天一直有些恹恹的。连永宁侯夫人召我去陪她礼佛,
我都提不起太大兴致。这日午后,天气难得放晴。侯夫人要去城郊有名的慈云寺进香祈福,
点名让我陪同。慈云寺……在城西方向。我心里咯噔一下,
几乎是立刻就想起了苏玲珑那句「尤其是城西那片」。「夫人,」我试图婉拒,
「我今日有些……」「清辞丫头,」侯夫人温和地打断我,拉着我的手,笑容慈爱,
「知道你是个坐不住的,就当陪我这老婆子散散心,也去拜拜菩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