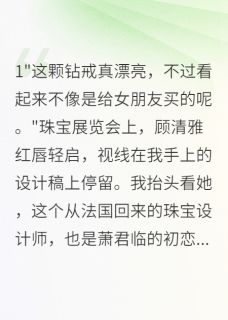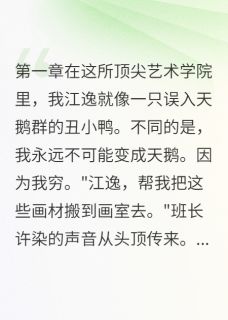直到我看到淮镇的指示牌消失在我眼中,我才对自己离开这件事有了实感。
明明早上陆鹤知还交代我买些鸡腿回家,我也应得好好的。
出门时儿子还罕见地拉着我的手和我说了很多话。
“咱们这风沙大,我看郑姨脸都被吹红了。”
“妈你今天回来记得给郑姨买个雪花膏。”
我掏出兜里还剩下的一块多钱看了又看,想着这也不能怪我。
上工的时候我特意和人打听了雪花膏的价钱,要一块九一瓶。
雪花膏和鸡腿只能买一样,我不想看到他们失望的目光。
走也没什么不好的。
到了晚上停车休息的时候,我躲在旁边啃我的杂粮饼。
司机大哥递过来一个水壶。
“妹子你这是和男人吵架了要回娘家?”
我接过水壶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又摇摇头。
“不是吵架,是我俩离婚了。”
这个年代离婚就像洪水猛兽,有过不下去硬过的,有过不下去***的。
大着胆子说自己离婚的我可能是大哥遇到的头一个。
“小两口有啥过不下去的,床头吵架床尾和,难不成你男人打你了?”
我仔细想了一下。
是因为陆鹤知半夜给郑纭盖被子?
还是因为儿子窝在她怀里撒娇说想让她当妈?
好像都不是。
“是因为一个饺子。”
“就因为一个饺子?!”
大哥觉得我在胡扯,但我语气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