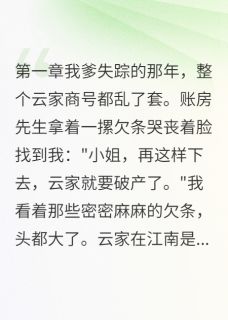结婚三周年纪念日,我熬了三个月在衬衫上绣满玫瑰。电视里却在直播他为白月光庆生,
送了她同样的高定玫瑰衬衫。他搂着白月光轻笑:“她?不过是个替身。
”我笑着剪碎所有衬衫,签好离婚协议消失。后来他翻遍全城,在雨夜找到流产大出血的我。
手术室红灯亮起时,他跪着嘶吼:“保大人!求你们保大人!
”白月光却发来短信:“当年车祸真相,你想让她知道吗?”---指尖下的棉布温凉,
带着一点属于夏夜的潮气。最后一片玫瑰花瓣的边缘被我仔细熨过,针脚细密得几乎看不见,
只留下饱满的弧度,像一颗颗凝固的、深红色的血珠。九十九朵。整整九十九朵,
从领口蜿蜒到袖口,盘踞在左胸心脏的位置,开得盛大而孤绝。我熬了三个月,
眼睛熬得通红,指尖不知被针扎破多少次,才在这件普通的男士衬衫上,
种下了这片只属于沈修瑾的荆棘花园。今天是我们的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窗外的霓虹流淌进来,在光滑的木地板上投下变幻的光斑。墙上的挂钟,
秒针不疾不徐地走着,发出轻微的、催眠般的咔哒声。十一点四十分。他快回来了。
我小心地把衬衫抖开,对着穿衣镜比划。想象着他穿上它的样子,
冷硬的线条被这浓烈的玫瑰柔化,那该多好。镜子里映出一张脸,苍白,眼下带着青黑,
只有唇角是微微翘起的,带着一点近乎虔诚的期待。茶几上的手机屏幕突兀地亮起,
是沈修瑾助理发来的信息,简洁冰冷:“太太,沈总今晚有重要应酬,晚归,不必等。
”心像是被那细密的针脚猛地刺了一下,密密麻麻的酸涩瞬间蔓延开来。
重要应酬……纪念日,也只是他日程表上一个无关紧要的备注。我攥紧了手机,
冰凉的金属外壳硌着掌心。视线有些模糊,我下意识地抬头,想找点别的东西分散注意力,
目光便落在了对面墙上巨大的液晶电视屏幕上。手指无意识地按下了遥控器开关。屏幕亮起,
瞬间被炫目的灯光和喧嚣的人声填满。是一个慈善晚宴的现场直播。衣香鬓影,觥筹交错。
镜头扫过一张张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最终,稳稳地定格在宴会厅最中心的位置。
我的呼吸停滞了。那个男人,穿着我亲手熨烫、挂进他衣柜的深灰色手工西装,
身姿挺拔如松。他微微侧着头,唇角噙着一抹我从未见过的、近乎温柔的弧度。他的臂弯里,
依偎着一个穿着珍珠白长裙的女人。苏柔。她回来了。灯光追逐着她,她巧笑倩兮,
美目流盼,像一朵精心培育、被所有人仰望的温室玫瑰。
而她身上那件礼服裙……我的目光死死钉在上面,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倒流。
那是一件极其特别的上衣,设计感十足。纯白的丝绸底料上,用暗红色的丝线,
绣满了盛放的重瓣玫瑰。从肩头蔓延至腰际,
图案、布局、甚至那浓烈欲滴的色泽……与我手中这件刚刚完成的、带着体温和心血的衬衫,
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大概是材质。她身上那件,
在聚光灯下流转着昂贵丝缎特有的、冰冷而遥不可及的光泽。而我手里这件,
只是最普通不过的棉布。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冷的手狠狠攥住,然后骤然捏碎。
碎片刺穿了血肉,带来一阵阵窒息般的锐痛。我僵在原地,指尖冰凉,
几乎握不住那件还带着我体温的衬衫。镜头贪婪地捕捉着这对璧人。
司仪热情洋溢的声音透过音响传来:“……感谢沈修瑾先生为今晚慈善拍卖慷慨解囊!
更令人惊喜的是,沈先生特别说明,这件由国际顶级大师设计的孤品玫瑰衬衫,
灵感源于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现在,就请这位‘最重要的人’,我们的苏柔**,
亲自为它揭幕!”聚光灯疯狂闪烁,几乎要灼伤我的眼睛。苏柔脸上飞起恰到好处的红晕,
眼波流转,含情脉脉地看了沈修瑾一眼。沈修瑾嘴角的弧度更深了些,
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纵容和宠溺。他轻轻颔首,姿态矜贵。主持人显然深谙炒作之道,
话筒立刻递到了沈修瑾唇边,声音带着刻意的兴奋:“沈总!
坊间一直传闻您与尊夫人感情甚笃,此刻看到您为苏**如此用心,
不知尊夫人林晚女士对此……会有什么特别的感想呢?”空气仿佛凝固了一瞬。所有的镜头,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沈修瑾那张英俊却疏离的脸上。他微微偏头,目光扫过镜头,
那眼神像淬了冰的刀锋,隔着屏幕,精准地刺穿我的心脏。薄唇轻启,吐出的话语清晰无比,
带着一种残忍的漫不经心:“她?”他低低地笑了一声,那笑声里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轻蔑,
“不过是个影子罢了。”“影子”两个字,像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我的耳膜上。
“……一个,还算凑合的替身。”世界在那一刻彻底失去了声音。
屏幕里苏柔羞涩又得意的笑,主持人夸张的表情,
台下看客们或了然或同情的目光……都变成了无声的默片,在我眼前扭曲晃动。
只有沈修瑾那张薄唇开合的画面,被无限放大,反复播放。替身。原来这三年的婚姻,
这三年的小心翼翼、委曲求全,这三年的期盼与等待,都只是一个笑话。
我林晚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填补苏柔不在时,沈修瑾身边那个模糊的位置。
一个用旧了、看腻了,随时可以被正主取代的影子。一股腥甜猛地涌上喉咙。
我死死咬住下唇,尝到了铁锈的味道。指甲深深陷进掌心,
那件耗尽了我三个月心血的玫瑰衬衫,被我无意识地攥紧,昂贵的丝线缠绕在指间,
勒得生疼,却远不及心口万分之一。客厅里死寂一片,只有电视屏幕还亮着刺眼的光,
无声地映照着我惨白的脸和空洞的眼神。不知过了多久,也许只是一瞬,
也许有一个世纪那么长。我缓缓地、极其缓慢地,松开了紧握的拳头。
掌心被指甲掐出几个深深的月牙形血痕,渗着细小的血珠。我低头,看着手里这件衬衫。
那些被我视若珍宝、一针一线绣上去的玫瑰,此刻看来如此廉价,如此可笑。
它们像一张张嘲讽的嘴,无声地咧开着,嘲笑着我的愚蠢和痴心妄想。我走到客厅中央,
将那件衬衫轻轻放在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动作平静得可怕。然后,我站起身,走向书房。
沈修瑾的书房,是他绝对的领地,平时不允许我轻易踏入。檀木书桌宽大厚重,
带着他惯有的冷硬气息。我没有开灯,借着窗外城市遥远的光,走到最底层的抽屉前。
那里放着一个保险柜,密码……是苏柔的生日。我曾偶然撞见他输入,
那时他还冷淡地警告我“不该看的别看”。指尖在冰冷的金属按键上停顿了一秒,
随即毫不犹豫地按下了那串刻在我心上的数字。0915。咔哒一声轻响,柜门弹开。
里面没有文件,没有金条。只有一件被小心折叠保存的……高中女生校服。洗得发白,
领口绣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柔”字。旁边,放着一个褪色的粉色发卡,
廉价的水钻掉了好几颗。这就是他沈修瑾锁在心脏最深处的东西。
属于苏柔的、带着廉价青春气息的遗迹。而我这个活生生的、陪了他三年的妻子,
连这个冰冷的保险柜都不配占据一角。我拿起那件校服,指尖触碰到粗糙的布料,
心已经彻底麻木。原来替身做到我这个份上,连正主一件破旧的衣服都比不过。回到客厅。
我将苏柔的校服也放在地上,就挨着我那件玫瑰衬衫。然后,我走进了主卧旁边的衣帽间。
巨大的衣帽间,有一半属于沈修瑾。整整一排衣柜,
挂满了熨烫得一丝不苟、价值不菲的衬衫。
白的、蓝的、灰的、条纹的……每一件都崭新笔挺,散发着昂贵的气息。
它们像一群冷漠的士兵,无声地列队,嘲笑着我手中那件廉价的心意。我伸出手,一件,
一件,把它们从衣架上扯下来。丝绸撕裂的声音在寂静的空间里格外刺耳。
昂贵的布料在我手中皱成一团,像被丢弃的垃圾。我面无表情,动作机械而迅速,
仿佛在进行某种神圣的净化仪式。很快,脚下便堆积起一座小山,全是沈修瑾的衬衫。
我抱着这堆象征着屈辱和欺骗的布料,走回客厅,
将它们全部堆在那件玫瑰衬衫和苏柔的校服旁边。接着,我走向厨房。拉开刀具抽屉,
里面躺着一把崭新的、闪着寒光的裁缝剪。我拿起剪刀,
冰冷的金属触感让我混沌的脑子有了一丝清明。回到客厅那座“小山”前,我蹲了下来。
目光掠过那件孤零零的玫瑰衬衫,掠过苏柔的旧校服,
最终定格在沈修瑾那堆价值连城的衬衫上。我拿起剪刀,对准了最上面一件纯白的丝质衬衫。
“嘶啦——”布料被轻易剪开的声音,在死寂的房间里显得格外惊心动魄。
像是剪断了一根无形的弦。我面无表情,动作精准而冷酷,沿着衬衫的纹理,
从领口一路剪到下摆。昂贵的丝绸在我手中变成破碎的布片。一件,又一件。
剪刀的利刃切割着精细的织物,发出单调而残忍的声响。碎片在我周围堆积,
像一场无声的雪崩。我剪得专注而投入,仿佛在进行一场关乎生死的搏斗。
指尖被剪刀磨得生疼,虎口震得发麻,但我感觉不到。心里只剩下一种近乎毁灭的快意。
当最后一堆昂贵的碎片被扬弃在脚下,我拿起那件我亲手绣制的玫瑰衬衫。
指尖抚过那些细密的针脚,那些曾经倾注了所有爱意和幻想的玫瑰花瓣。它们依旧娇艳欲滴,
像是在无声地控诉。我闭上眼,深吸一口气。再睁开时,眼底一片冰冷的荒芜。
剪刀毫不犹豫地落下。“嘶啦——嘶啦——”亲手毁灭自己的心血,
比毁灭沈修瑾的东西更痛。每一剪下去,都像是在剜自己的肉。玫瑰被从中剪开,花瓣碎裂,
丝线崩断。那片我倾注了所有心血和爱意、想要在纪念日送给他的花园,
在我手中迅速分崩离析,化为一片狼藉的、毫无价值的碎布。最后,是苏柔那件旧校服。
剪刀碰到那粗糙布料时,我甚至停顿了一下。然后,我用尽全身力气,狠狠地剪了下去!
布料撕裂的声音带着一种脆弱的抵抗,领口那个歪歪扭扭的“柔”字瞬间被一分为二。“砰!
”剪刀被我狠狠掼在地上,金属撞击大理石的声音尖锐刺耳。我踉跄着站直身体,
胸口剧烈起伏,像刚跑完一场漫长的马拉松。环顾四周,遍地狼藉。昂贵的丝绸碎片,
破碎的玫瑰花瓣,断裂的丝线,
还有那件被撕成两半的、带着廉价青春印记的校服……它们混合在一起,
构成了一幅疯狂而绝望的画面。空气里弥漫着布料被破坏后的尘埃味,
还有一种冰冷的、毁灭的气息。我走到书桌前,拉开抽屉。里面安静地躺着一份文件。
封面上,“离婚协议书”几个黑色宋体字,像冰冷的墓碑。这是我三个月前就准备好的。
在某个他彻夜未归、电话打不通的清晨,
在又一次看到他和苏柔名字并排出现在财经八卦头条之后。那时,
我还存着一丝微弱的、可笑的幻想,以为只要我再努力一点,再卑微一点,
总能捂热他那颗石头心。现在看来,真是愚蠢透顶。我拿起笔,拔掉笔帽。
笔尖悬在“乙方”签名的空白处。指尖控制不住地微微颤抖。三年的婚姻,
无数个等待的日夜,那些被他弃如敝履的真心……最终都浓缩到这一纸契约上。我闭上眼,
深深吸了一口气,再缓缓吐出。再睁开眼时,眼底只剩下死水般的平静。笔尖落下,
在纸页上划出沙沙的声响。我签得很慢,很用力,
仿佛要把这三年的所有不甘、所有委屈、所有心碎,都灌注进这两个字里。林。晚。
最后一笔落下,力透纸背。放下笔,我拿起那份签好字的协议书,
把它端端正正地放在客厅唯一还干净整洁的茶几正中央。白色的纸张,在满地的狼藉中,
显得格外刺眼。最后看了一眼这个曾经被我称之为“家”的地方,
冰冷、华丽、像一个巨大的金丝笼。空气中还残留着沈修瑾常用的那款冷冽雪松香水的气息,
此刻闻起来,却像腐朽的墓穴。没有丝毫留恋。我转身,
只拿起玄关柜上那个用了多年的旧帆布包,里面只有身份证、一点零钱和一部旧手机。
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了。打开厚重的雕花大门,外面是沉沉的夜色和城市永不熄灭的灯火。
我走了出去,没有回头。身后的门,缓缓合上。隔绝了那个充满谎言和屈辱的世界,
也隔绝了我那场长达三年的、名为婚姻的噩梦。---城市的霓虹在车窗外飞速倒退,
拉成模糊的光带。**在后排座椅上,脸贴着冰冷的车窗玻璃,
试图汲取一丝凉意来冷却脑中翻腾的混沌。司机师傅从后视镜里瞥了我几眼,
大概是我惨白的脸色和失魂落魄的样子让他有些担忧。“姑娘,看你脸色不好,
要不要去医院?”医院?我下意识地抚上小腹。那里空空如也,
却莫名地传来一阵尖锐的、下坠般的绞痛。这感觉断断续续折磨了我小半天,
从看到电视直播那一刻起,就像有一只冰冷的手在里面搅动。
我以为是情绪激荡下的生理反应,强忍着摇头:“不用,谢谢师傅,老毛病了,
送我回家就行。”声音干涩得厉害。车子最终停在一个破旧小区门口。
这是我婚前租住的老房子,合同一直没到期,钥匙也一直放在包里,像个潜意识里的退路,
没想到今天真的用上了。楼道里的声控灯坏了,我摸黑爬上四楼,
钥匙**锁孔时手抖得厉害,试了好几次才打开。一股久未住人的灰尘和霉味扑面而来。
我摸索着开了灯,昏黄的灯光照亮了狭小的一室一厅。家具上蒙着厚厚的灰,空气冰冷滞涩。
疲惫和寒冷瞬间攫住了我,小腹的绞痛变本加厉,像有把钝刀在里面反复切割。
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我几乎是挪到床边,和衣倒在冰冷僵硬的床垫上,蜷缩成一团。
身体一阵阵发冷,牙齿控制不住地打颤。意识开始模糊,沈修瑾那张冷酷的脸,
苏柔得意的笑容,还有那满地被剪碎的玫瑰和衬衫……碎片般在眼前旋转、撞击。
小腹的痛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不容忽视,像某种不详的预兆。
不行……不能在这里……残存的理智在尖叫。我挣扎着摸出手机,
指尖因为寒冷和疼痛而僵硬。通讯录划了半天,最后停在了一个名字上——程薇。
我高中时最好的朋友,也是这座城市里唯一还关心我死活的人。电话响了好几声才被接起,
那边传来程薇睡意朦胧又带着被打扰的不耐烦:“喂?谁啊?
大半夜的……”“薇薇……”我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带着自己都陌生的哭腔和虚弱,
“是我……林晚……帮帮我……肚子……好痛……”“晚晚?!”程薇的声音瞬间拔高,
睡意全无,变得无比清晰和紧张,“你怎么了?!你在哪?别怕,我马上到!告诉我位置!
”我报了小区的名字和楼栋,手机就从无力的手中滑落,掉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意识像退潮的海水,迅速模糊、远去。剧痛如同黑色的潮水,彻底将我淹没。最后的感觉,
是身下床单传来一阵温热粘稠的湿意…………刺鼻的消毒水味强势地钻进鼻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