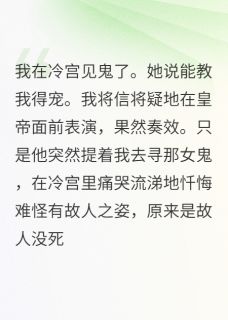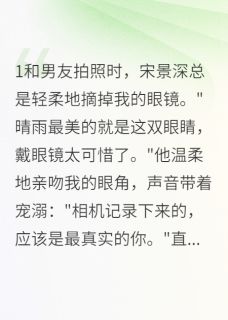雨是后半夜停的。
天蒙蒙亮时,门栓动了,我起身将枕边的小碎布塞进里衣,穿戴好从屏风出来。
他看到我,脸上闪过一丝懊恼。
「都怪我动静大了,昨日你为了等我休息不好,今日便在屋子里吧。」
我摇摇头,接过他的篮筐。
「走吧。」
救我的人叫阿牛,人如其名,身形壮实得像头耕田的老牛,性子也像牛,沉默,能吃苦。
半年前,他把我从湍急的河水里捞起来,带回了他所谓的「家」——不过是山脚边两间勉强能遮风挡雨的茅草屋。
一间垒了个土灶,算是厨房;另一间只有一张破旧的草席。
为了安置我这个「娇贵」的落难女子,他拿出了积攒不知多久、贴身藏着的几块碎银子,置办了这扇屏风,这张草席,还有几个粗陶碗碟。
我向他道谢时,他搓着手,带着点窘迫说:
「姑娘家,不比我,大老粗一个,席地就能睡。」
不知为何,我这般能言善辩之人,面对他时,竟总说不出半点好听的话。
雨后的泥路湿滑粘腻,黄泥浆没过脚踝。
他怕我湿了鞋袜,便用板车拉我,早春寒意侵入皮肤里,奇怪,却暖烘烘的。
我们到了镇上时,雾气还未消散,街上没什么人,只有刘婶的面铺里冒了一缕青烟,这饼子便是要给她送去。
刘婶是镇上有名的热心肠,谁家出了什么事,她总第一个帮忙,可她有个特点,一旦有人欠账,任谁的面子她也不给。
无论是几十年的老街坊,还是新搬来的邻居,在她的小面铺里,一碗面、一勺油的钱,都算得清清楚楚,绝无赊欠的可能。
城东肉铺的张屠夫,平日里嗓门大得能震翻屋顶,一见她拿着账本走过来,立马缩起脖子,大气不敢出。
记得她第一次见到我,就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嗓门敞亮:
「哎哟,多齐整的姑娘!咋就看上阿牛这傻小子了?他呀,心肠比棉花还软,兜里一个铜板都存不住,今儿给东街的乞儿,明儿帮西头念不起书的娃娃抄书。」
「若是知道是骗子,这傻小子反而高兴!说原来人间也没有很苦。」
她摇着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
我听了,只是笑眯眯地把刚包好的、还温热的芝麻饼塞进她手里:
「婶子,尝尝,刚出炉的。」
刘婶一愣,接过饼子,看着我,又看看旁边只会憨笑的阿牛,重重叹了口气:
「唉!傻小子娶了个傻媳妇儿!」
我笑而不语。
她若知道我曾有另一个名字——玲珑,那个在金銮殿上被赞为「七窍玲珑心」,恐怕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这些日子,总听她站在自家铺子前跟人絮叨:「等春闱,等我家小子考完了,我就歇歇!享几天清福!」
话语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期盼。
旁边打铁的李叔,抡着大锤,闻言停下动作,抹了把脸,瓮声瓮气地说:
「老嫂子,这话你说了多少年啦?之前说等他中了秀才就歇,后来说等秋闱,现在又等春闱,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刘婶脸上的笑容顿了顿,随即又扬得更高,声音也拔高了些,像是在说服别人,也像是在说服自己:
「快了快了!这回真快了!春闱眼瞅着就到了!等他中了进士,我就关门大吉,回乡下养老去!」
她挥舞着手臂,仿佛那好日子已经触手可及。
算算日子,离那场决定无数举子命运的春闱,也不过半月了。
刘婶马上就可以享福了。
可还未踏入门内,就听见里面传来一阵惊呼:
「刘婶上吊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