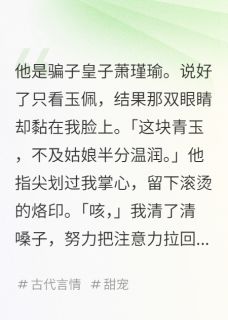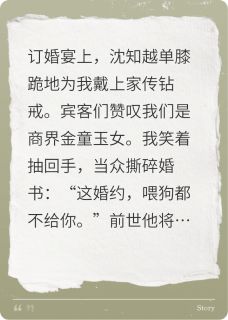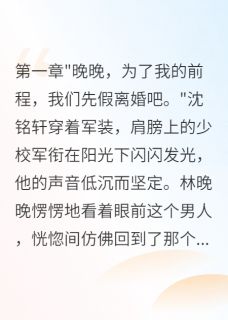1苏晚晴的发梢扫过我手腕时,栀子香混着皂角味漫上来,腻得发慌。
她手里的帕子晃个不停,湖蓝色缎面上那半只鸳鸯,银线翅膀在日头下闪,晃得人眼晕。
"汉伦哥,"她声音软得像棉花,"下月初三的嫁衣,
我......""哐当——"竹门被踹开的声响像劈柴,把她后半句劈得粉碎。
我爹的官靴碾过门槛,泥点子溅在苏晚晴的月白裙摆上,他手里明黄的圣旨晃得我眼疼,
像块烧红的烙铁直戳过来。"接旨!"他嗓子比腊月的风还硬,"陛下赐婚,三日后,
娶长公主钟燕婷!"我抓过圣旨的手猛地收紧,宣纸上的朱红玺印像滴在雪地里的血。
苏晚晴的帕子"啪"地掉在青石板上,那半只没绣完的鸳鸯,脑袋正磕在她鞋跟下,
断了的银线垂下来,像条死虫。"不可能。"我盯着爹歪了的官帽,后槽牙咬得发酸,
"我跟晚晴的庚帖还压在祠堂香炉底下,道长说过是天作之合。""庚帖?"爹突然笑出声,
巴掌甩在我脸上时,汗味混着酒气扑过来。"苏家今早递了退婚书,说你王汉伦攀附权贵,
配不上她家金枝玉叶!"苏晚晴猛地抬头,鬓边珠花晃得厉害。她眼里的惊惶亮得刺眼,
像去年她偷偷埋我娘药渣时被撞破的模样。我舌尖尝到血腥味,刚要开口,她却后退半步,
帕子上的碎银线缠上指尖,勒出红痕。"汉伦哥,"她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叶子,
"你......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风突然停了,栀子花瓣落了她一肩,
香得发腻。我才瞅见她袖口沾的墨痕,黑沉沉的,跟苏家退婚书的墨色一模一样。
那些说要等我科举、要陪我到老的话,原来就像她绣的鸳鸯,线一断就成了笑话。
她跑出去时,裙角扫过我靴面,带过一股苦艾味——我娘药罐里常飘的那股涩味。
今早去太医院,张院判盯着药渣欲言又止,此刻后背的冷汗突然浸透中衣。
前几日钟燕婷来府里,塞给我一小包晒干的苦艾,说"你娘喝这个安神",
当时只当是客套,此刻那味道竟跟苏晚晴裙角的重合了。爹把一卷囚衣扔在脚边,
粗麻布磨得脚踝生疼。"抗旨者满门抄斩。"他鬓角的白发晃得我眼晕,
"你娘的药缺紫河车,只有长公主府有。"我摸着发烫的脸颊,那片皮肤像被烙铁烫过。
香炉里的香灰迷了眼,明黄圣旨突然变成退婚书的墨迹——钟燕婷早就算准了。
前阵子娘咳得厉害,我求遍药铺都找不到紫河车,偏是她,
在宫宴上跟太医打听这味药的药性,当时我还觉得是皇家闲事。三日后的红绸铺了半条街,
风卷着红绸扫过脸,像谁在哭。观礼人群里,苏晚晴攥着那方破帕子,
眼里的恨亮得像淬了毒的针。喜轿落地时,一只手从轿里伸出来。指尖冰凉,
攥住我手腕的力道,像要把骨头捏碎。红盖头下的声音裹着铁锈味:"王汉伦。"我低头,
看见她袖口的曼陀罗,花瓣尖那点腥气,跟我娘药罐底沉着的黑渣子一个味。"你逃不掉了。
"她拇指摩挲着我腕骨凸起的地方,像在摸一件盼了许久的物件,"从你娘喝第一碗药开始,
就没处逃了。"风里的栀子香突然变成苦艾的涩味,呛得我喉咙发紧。我这才懂,
她要的从不是什么驸马,是把我钉在她身边——用我娘的命,用苏晚晴的背叛,
用这满城红绸,织一张密不透风的网。而我,早就在网中央了。
2驸马府的梁上悬着盏琉璃灯,光透过彩色玻璃洒在地上,拼出些碎渣似的光斑,
晃得人眼晕。檀香浓得发腻,压过了我怀里旧书的霉味——那是我从家里带的唯一物件,
夹着半片去年苏晚晴送的栀子花瓣,干得发脆。钟燕婷坐在妆台前,红盖头垂在肩头,
露出的脖颈白得像刚剥壳的藕。她没回头,指尖在描金镜匣上敲得笃笃响,
那节奏偏生跟我胸腔里乱撞的心跳合上了。"他们说,你不肯穿那身驸马礼服。
"她声音很轻,气音扫过耳垂时,我后颈突然冒起一层鸡皮疙瘩,
像有人对着那里吹了口凉气。我攥着袖袋里的退婚书,苏家的朱砂印蹭得掌心发黏,
像块揭不掉的疤。"我跟苏晚晴有婚约。"话出口才觉出抖,连我自己都不信这犟嘴的底气。
她终于转过身。红盖头滑落的瞬间,我撞见她的眼——黑沉沉的,像口没底的井。
睫毛垂下来时,在眼下投出片阴影,倒显得那双眼更亮,亮得能照见我自己那点可怜的挣扎。
"婚约?"她突然笑了,指尖捏住我下巴,指甲凉得像冰锥。"你今早去苏家,
门房没告诉你?苏**正陪吏部侍郎家的公子看花呢。"喉结滚了滚,嘴里尝到血腥味。
今早我确实在苏家墙根站了半个时辰,听见院里传来苏晚晴的笑,脆生生的,
跟她从前躲在书房看我练字时一个调调。只是那时她笑完会凑过来,
用沾了墨的指尖戳我手背,现在她的笑声里,混着另一个男人的咳嗽声,
还有句清晰的"这玉簪比王汉伦送我的银钗体面多了"。"她是被逼的。"我挣开她的手,
袖口扫掉妆台上的胭脂盒,螺子黛滚在地上断成两截。钟燕婷弯腰去捡,
发间金步摇叮当作响。"被逼着收了侍郎家的玉簪?"她捏着半截螺子黛,
在我手背上划了道浅痕,血珠刚冒出来就被她指腹蹭掉,"还是被逼着跟人说,
王汉伦早就攀上了公主府的高枝?"她指尖往我伤口上按的力道很轻,
偏生那点疼直往骨头缝里钻。
我突然想起今早太医院的药渣——张院判扒开那些黑褐色的碎末,
指着块暗红的东西说:"长公主连夜让人从库房调的紫河车,说是陈年干货,药性最稳。
"可我分明记得,前日去苏家时,看见苏公子手里提着个药包,
裹药纸的角上沾着同样的暗红渣子。"我要去见陛下。"我后退时撞到博古架,
架上的青瓷瓶晃了晃,映出我脸白得像张纸。"见陛下?"她突然凑近,
鬓边珠花扫过我鼻尖,那股冷香里掺着点药味。"你娘今晨又咳血了,张院判说,
再断药三日,就得准备后事。"她手按在我胸口,
掌纹磨过我衣襟下的疤——那是去年替苏晚晴挡劫匪时留下的,"你说,
陛下是先听你诉委屈,还是先治你个不孝之罪?"呼吸猛地顿住,像被人掐住了喉咙。
袖袋里的退婚书突然烫得像火炭,我这才后知后觉——苏家递书那天,
正巧是娘的药快见底的时候。去吏部时,李主事把砚台砸在我脚边,墨汁溅了满靴。
"忘恩负义的东西!苏家供你读书三年,你转头就做凤凰男!"他唾沫星子喷在我脸上,
我瞅见他腰间那枚玉佩,跟今早侍郎公子腰间的一模一样。去太医院时,
张院判摸着胡子叹气,药碾子吱呀响。"驸马爷,公主殿下发了话,
老太太的药得她亲笔批条才敢发。"他碾的川贝粉飞起来,呛得我咳嗽,
"您看这药引子......"他指了指墙角的空匣子,"听说苏老爷前日来问过价。
"傍晚回府,撞见钟燕婷在廊下喂猫。那只黑猫叼着块生肉撕咬,血沫沾在雪白的犬齿上。
她穿件月白寝衣,指尖沾着暗红的血,看见我时突然把肉扔过来,正落在我脚前。
"他们都欺负你,对不对?"她笑起来时眼角那颗痣忽明忽暗,像檐角挂着的鬼火,
"没关系,以后有我。"我没理她,径直冲进书房。案上摆着面铜镜,是她让人送来的,
说"新妇给夫君的见面礼"。镜面擦得太亮,亮得能照出我眼下的青黑,
还有鬓角新冒的白发。我盯着镜中的自己,忽然发现那双眼的笑不对劲——嘴角咧得太大,
眼角纹路深得像刀刻,活脱脱是钟燕婷方才喂猫时的模样。"哐当!"铜镜被我扫在地上,
碎片里涌出无数个扭曲的影子。脚心被碎玻璃扎出血,疼得钻心。这时才闻见,
钟燕婷喂猫的那块肉,血腥味里混着点苦杏仁味——跟张院判说的,我娘咳出来的血沫味,
不差分毫。窗外的月亮爬上来,照在满地碎镜上,像撒了一地冰冷的刀。
我摸着胸口那块被她按过的地方,突然明白过来,这宅子根本不是什么驸马府。
是座镀金的笼子。而她,是那个拿着钥匙的饲主,早就算准了我会乖乖钻进来。
3苏晚晴要嫁人的消息,是扫院子的老仆嚼舌根时漏出来的。
他说吏部侍郎家的红绸从街尾铺到街头,比我娶长公主那天还张扬。我捏着手里的药碗,
滚烫的苦艾汤溅在虎口,烫出片红痕——这是钟燕婷让人送来的,说娘今早能多喝半碗了。
药味钻进鼻子时,我指尖突然发紧。这味道太熟悉,
跟那日苏晚晴裙角沾的、跟钟燕婷袖口藏的,竟是同一种苦。"她让人送了帖子。
"钟燕婷的声音从背后飘过来,带着点檀香的冷味。她穿着石青色常服,
手里捏着张烫金帖子,指尖在"苏晚晴"三个字上反复划着,指甲刮得纸面沙沙响,
像耗子在啃东西。我盯着药碗里的残渣,娘的咳嗽声突然在耳边炸开。那日在太医院,
张院判掀开娘的药渣,指着块紫河车碎末说:"长公主连夜让人从药材库调的,陈年干货,
药性最稳。"可我忘不了他说这话时,眼角往钟燕婷那边瞟的模样。"想去吗?
"钟燕婷突然笑了,抬手抚上我被烫红的虎口,指尖凉得像井水。"想去问问她,
退婚书上的朱砂印,是不是她亲手按的?"我猛地抽回手,药碗"哐当"撞在桌角,
褐色药汁溅在她裙裾上,像块洗不掉的血渍。去吗?去看她穿着比湖蓝帕子更艳的红嫁衣?
去听她对别人说,当初怎么瞎了眼才看上我这穷书生?可袖袋里那半片干枯的栀子花瓣,
还在硌着心口,像根没拔干净的刺。婚宴设在侍郎府后花园,假山流水绕着满池荷花,
香得让人发晕。我跟在钟燕婷身后,她的裙摆扫过青石板,发出细碎的声响,
像在数我迈向深渊的步子。宾客们的目光扎在背上,
比爹甩在我脸上的巴掌还疼——有人捂嘴笑,有人用折扇指我,酒气混着脂粉味扑过来,
呛得我喉咙发紧。苏晚晴就站在回廊下,红盖头还没掀,凤冠上的珍珠晃得人眼晕。
她看见我时,盖头下的肩膀明显抖了抖,随即传来银铃般的笑:"哟,
驸马爷怎么穿得跟奔丧似的?"周围的哄笑像潮水般涌上来。吏部侍郎端着酒杯走过来,
酒液晃出杯沿,滴在我手背上:"王大人肯赏光,真是蓬荜生辉。只是小女今日成婚,
怕是容不下......""容不下谁?"钟燕婷突然开口,声音不高,
却像块冰砸进滚油里,满花园的喧闹瞬间冻住。她往前走半步,
石青裙摆扫过苏晚晴的红嫁衣,"苏**忘了?去年清明,你爹在我府里说,
愿将你许给王汉伦,生生世世,就算做牛做马也愿意。"苏晚晴的盖头突然滑落,
露出张惨白的脸,鬓角珠花歪在一边。"是他先负我!"她抓起裙摆,指甲几乎嵌进绸缎里,
"他早和长公主勾搭上了,我不过是被抛弃的......""抛弃?
"钟燕婷突然指向她身后的雕花屏风,屏风缝隙里,露出半截青色衣袍。"那屏风后藏着的,
是不是你昨日花五十两银子买通的侍卫?他说,是你让他咬破舌尖,
假装被驸马爷打晕在你闺房的。"屏风后的人"噗通"跪出来,
膝盖砸在青石板上的声响,惊飞了池边的白鹭。"公主饶命!"他额头磕出红印,
"苏**说,只要做成了,就让侍郎大人给我谋个职位......"苏晚晴瘫坐在地上,
凤冠摔进荷花池里,溅起的水珠打湿我的靴面。她突然指着我尖叫,
声音尖利得像指甲刮过琉璃:"王汉伦!你好狠的心!连这种谎话都编得出来!
"我盯着她扭曲的脸,袖袋里的栀子花瓣突然发烫。那日在苏家墙外,
我听见她对丫鬟说:"等事成了,太子殿下会赏咱们家良田千亩。
"那时我还骗自己是风声太乱听错了。张院判塞给我的药渣清单上,
"紫河车"三个字被圈了又圈,旁边写着:"苏家公子三日前曾购同款"。"我没编。
"我蹲下身,看着她因惊恐而放大的瞳孔,声音竟出奇地稳,"你退婚那日,
我娘的药正好断了。张院判说,是你爹扣下药材,逼你在退婚书上画押的。
"苏晚晴的瞳孔骤然收缩,像被踩住的蛇。"啪!"清脆的巴掌声炸响在花园里。
钟燕婷的手还扬在半空,指节泛白。苏晚晴捂着脸,嘴角渗出血丝,
眼神里的怨毒几乎要溢出来。"本宫的驸马,"钟燕婷的声音冷得像淬了冰,
"轮得到你作践?"她抬脚,踩在苏晚晴掉在地上的凤冠上,珍珠碎裂的声响里,
她一字一顿道:"从今日起,苏家门生,永不录用。"我站起身,阳光刺得眼睛发疼。
池里的荷花被风吹得东倒西歪,像极了苏晚晴此刻的狼狈。可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意,
只有片麻木的空——原来那些年的栀子香,不过是场用谎言泡出来的幻梦。回府的马车里,
钟燕婷的头靠在我肩上,呼吸温热地洒在颈窝。"现在知道,谁才是真心对你了?
"她的指尖轻轻划过我虎口的烫痕,那里已经结了层薄痂。我没躲。
她指尖的温度透过痂皮渗进来,竟带点奇异的暖意。车窗外的街灯一盏盏掠过,
像被碾碎的星子。我摸出袖袋里那片干枯的栀子花瓣,捏在掌心揉了揉——碎了,
成了粉末。风从车窗缝钻进来,卷着粉末飘出去,没留下一点痕迹。"别想着逃。
"钟燕婷突然咬住我的耳垂,声音甜得发腻,却带着针尖般的锐,"你娘的药,
还在我库房里锁着呢。"马车碾过青石板的声响,一下下敲在心上。我知道,
她不是在威胁我。她是在提醒我——这世上肯为我豁出脸面、把刀子捅向苏晚晴的,
只有她。这种被攥住软肋的感觉,竟比苏晚晴的背叛更让人踏实。至少她的狠,
明明白白冲着"护着我"来的。4苏晚晴被退婚的消息像长了腿,三天就蹿遍了京城。
有人说她在婚宴上挨了那一巴掌后,吐了半盆血;也有人说吏部侍郎连夜把她锁进柴房,
骂她毁了全家前程。这些话飘进驸马府时,我正蹲在灶房给娘煎药,药罐里的苦艾咕嘟冒泡,
溅在灶台上的沫子,像没擦干净的泪。"王驸马,太子殿下有请。
"御花园的太监尖着嗓子闯进来,我回头时,
瞥见他袖口沾着金粉——东宫侍卫描箭羽时最爱用的那种,亮得扎眼。
太子斜倚在汉白玉栏杆上,手里转着枚玉佩,阳光晃得玉面发亮,照得人眼晕。
他身后的海棠开得疯,花瓣落了满肩,倒让那身月白锦袍添了些不该有的艳色。"汉伦啊,
"他拍我肩膀的力道不轻不重,指尖却在我肩胛骨上顿了顿——那里有道旧伤,
去年帮苏晚晴抢被山匪掠走的帕子时留下的,此刻被他按得发疼,"长公主脾气烈,
这些日子委屈你了。"我盯着靴尖上的泥点,是今早去太医院取药时,
踩在张院判门口的青苔上沾的。他塞给我药包时,指腹在"紫河车"三个字上反复蹭,
压低了声说:"公主特意吩咐,老太太的药得用新鲜的才管用。
"新鲜的——这三个字像针,扎得我后颈发僵。"殿下多虑了。"我的声音有点发紧,
喉结滚了滚,尝到点药渣的苦味。太子突然笑起来,惊飞了枝头的麻雀。他凑到我耳边,
温热的呼吸混着龙涎香扑过来,带着股腻人的甜:"本王听说,你娘的药引,
缺南海的夜明珠?"他从袖里摸出个锦盒,打开时珠光刺得我眼仁发酸,"可惜啊,
那珠子被长公主锁在藏宝阁里,钥匙就系在她贴身的香囊上。"手心"唰"地冒了汗,
锦盒的冰凉顺着指尖爬上来,像条小蛇钻进胳膊。去年冬天娘咳得最凶时,张院判确实提过,
南海夜明珠磨成粉入药能安神。那时我跑遍京城药铺,掌柜们都摇头,说这珠子金贵,
只有皇家库房才有。现在想来,钟燕婷那时总爱在我面前摩挲腰间的香囊,
银线绣的曼陀罗底下,确实坠着片冰凉的东西。
"殿下的意思是......""本王可以帮你。"太子的指尖刮过锦盒边缘,
发出细碎的响,"这里面是三颗夜明珠,你先拿去用。"他突然压低声音,
鬓角的玉簪几乎戳到我脸上,"但长公主手里有本账册,记着些不该记的东西。
你帮本王拿来,以后你娘的药,本王包了。"回府的路上下了场小雨,打湿了官服。
路过苏家巷时,那扇朱漆门紧闭着,门环上的铜绿被雨水泡得发亮。
去年苏晚晴就是在这门后,踮脚把绣了一半的鸳鸯帕子塞进我手里,帕角蹭过指尖,
软得像团云。可现在我知道,她塞给我帕子的前一晚,太子刚赏了苏家两箱银子。
我在钟燕婷的书房翻了个底朝天。从博古架上的青瓷瓶到床底的樟木箱,
连她常看的《女诫》书页间都摸了个遍。这书房总飘着股冷香,
像冬日腊梅混着墨味——张院判偷偷说过,这是用曼陀罗花晒干了熏的,能安神,
也能迷心。此刻这香味裹着雨气钻进来,倒让我想起她昨夜睡梦中攥着我袖口的力道,
紧得像怕我飞了。"找什么呢?"她的声音突然从身后冒出来,
我手里的砚台"哐当"砸在地上,墨汁溅在她月白的裙裾上,像朵突然炸开的黑花。
她赤着脚站在青砖上,没戴金步摇,长发垂在肩头,
几缕湿发贴在颈窝——想来是刚沐浴过。脚踝上那道浅疤看得清楚,
是去年替我挡箭时被箭羽划伤的,像条淡粉色的线。"没、没什么。"我慌忙去捡砚台,
碎片割破了手心,血珠滴在墨渍里,晕开点点暗红。她蹲下身,指尖轻轻按住我的伤口,
那冰凉的触感让我打了个寒颤。"听说你今天见了太子?"她的睫毛很长,
垂下来时在眼下投出片阴影,"他给了你什么好处?是南海的夜明珠吗?
"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贴在官服上凉得像冰。灶上还温着给娘的药,
此刻仿佛能听见药汁沸腾的声响,咕嘟咕嘟,像在催我做个了断。可看着她颈窝的湿发,
突然想起昨夜她咳得厉害,帕子上沾着的血沫里,也有股曼陀罗的香。"你娘的药,
我已经让人送去了。"她起身时,手里多了本蓝色封皮的册子,封面光溜溜的,
连个字都没有。"你在找这个?"册子很薄,拿在手里却沉得压手,
纸页间夹着股熟悉的腥气——跟太子锦盒里夜明珠的味道一般无二。"太子想要这个?
"她突然把册子扔过来,我慌忙接住,指尖刚碰到封面,就听见院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
像雨点砸在铁皮上。"公主!不好了!"侍卫撞开院门时,腰间的佩刀晃得厉害,
"太子殿下带着禁军来了,说、说驸马爷偷了您的私密账册!"我猛地抬头,
钟燕婷正端着茶杯,慢条斯理地吹着浮沫。茶雾模糊了她的脸,只剩嘴角那抹笑看得真切,
像冬日结冰的湖面,看着平静,底下藏着翻涌的暗涌。禁军的刀鞘撞在廊柱上,
闷响里透着杀气。太子踩着积水走进来,明黄蟒袍下摆沾了泥,却掩不住眼里的得意。
"王汉伦!"他指着我手里的册子,声音像淬了火的钢针,"你竟敢盗取公主私密,
还不快交出来!"我攥着册子的指节发白,纸页边缘割得手心生疼。这根本不是账册,
是钟燕婷设的陷阱!可我现在握着它,就像握着块烧红的烙铁,扔也不是,不扔也不是。
"臣没有......""够了!"太子打断我,靴底碾过地上的墨渍,"人赃并获,
还敢狡辩!拿下!"两把刀同时架在我脖子上,
冰凉的触感让我想起苏晚晴退婚书的朱砂印——那时也是这样,明明觉得不对劲,
却怎么也挣不脱。钟燕婷终于放下茶杯,茶盖碰到杯沿的脆响,压过了禁军的脚步声。
"太子殿下,"她的声音很轻,却像块石头投进冰湖,"你确定要动本宫的人?
"太子的脸色变了变,刀鞘在手里攥得发白:"长公主,
这是他盗取你的私物......""私物?"钟燕婷笑了,曼陀罗的冷香突然浓得呛人,
"那是本宫让他拿的。这里面,是前几年你挪用军饷,去江南买瘦马的账目。
"她抬手指向我手里的册子,"要不要让禁军念念,你在苏州织造府的账上,
记了多少匹锦缎、多少个美人?"太子的脸瞬间白得像纸,后退时踩在水洼里,
溅起的泥点沾在蟒袍上,狼狈得像条丧家之犬。我站在原地,
手心的血混着墨汁滴在青石板上,晕成朵怪异的花。雨还在下,打在屋檐上沙沙响,
像谁在低声笑——我以为太子递来的是生路,其实是钟燕婷早就挖好的坑。
她算准了我会为娘的药动心,算准了太子会自投罗网,连我翻找账册时的慌不择路,
恐怕都在她眼里。院角的曼陀罗被雨水打湿,紫得发黑。我望着钟燕婷的背影,
突然明白她那句"别想着逃"不是吓唬人。她的爱就像这花,看着有毒,
却偏要用最狠的法子,把所有想伤我的人,都挡在外面。5书房的窗棂斜斜切进一道夕阳,
把案上的砚台照得发亮。我捏着那方钟燕婷送的墨锭,
指腹蹭过上面雕刻的曼陀罗花纹——冰凉的石质里透着股熟悉的香,是她熏衣用的龙涎香,
混着点苦艾的药味。这味道缠了我好些日子,竟跟娘药罐里飘出的气息慢慢融在了一起。
门被轻轻推开时,我以为是送药的丫鬟。直到那股栀子香钻进来,
我手里的墨锭“咚”地砸在砚台上,溅起的墨汁染黑了半张宣纸。苏晚晴站在门槛边,
素白的裙角沾着泥,鬓边的珠花歪歪扭扭,像是一路跌撞着跑来的。她瘦得脱了形,
颧骨凸出来,衬得眼睛格外大,可那双眼不再是过去映着星光的样子,红血丝爬满眼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