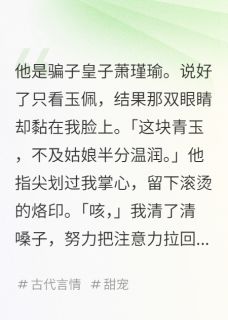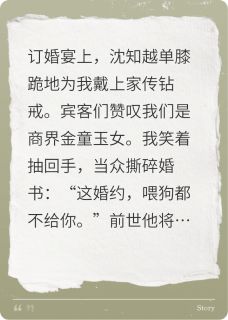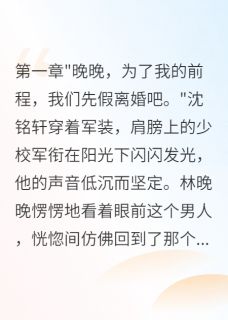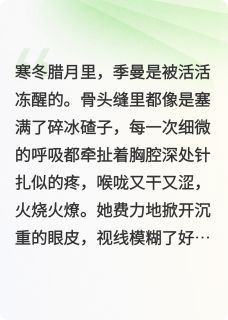
“走吧,苜蓿。”季曼的声音恢复了平静,甚至比刚才更加坚定有力,“天色不早了,我们回去。明天,还得继续出摊呢。”
她挺直了背脊,不再看那马车消失的方向,拉着苜蓿,转身汇入了西市散场的人流中。寒风吹动她打着补丁的衣角,背影单薄却透着一股倔强的力量。
那惊鸿一瞥带来的短暂悸动和恐惧,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只泛起一丝微不足道的涟漪,迅速被更汹涌的、名为“生存”和“自立”的浪潮所吞没。聂桑榆?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路人甲罢了。现在,搞钱才是硬道理!
---
“醉花颜”和“凝玉雪”的名声,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荡开的涟漪越来越大,终于不可避免地触碰到了京城脂粉行当某些人的利益。
西市最大的胭脂铺“玉香阁”的掌柜钱有福,最近就有点坐不住了。他捏着伙计买回来的几盒“凝玉雪”和一小罐“醉花颜”,眉头拧成了疙瘩。
“掌柜的,您看这粉,”伙计指着那罐细腻雪白的香粉,“确实比咱们最便宜的那档货要细得多,味道也清淡好闻,关键是……她们喊的是‘无铅养颜’,不少客人都信了,都跑去她们那小破摊子上买!咱们铺子这个月最便宜的‘玉屑粉’都少卖了三成!”
钱有福用指甲抠了一点“凝玉雪”在掌心捻开,细腻柔滑的触感骗不了人。他又闻了闻那罐胭脂,清甜的花香,颜色也调得自然。他经营脂粉铺子几十年,是内行里的内行,一眼就看出这东西虽然包装简陋,但用料和心思都透着巧劲儿,尤其那个“无铅”的噱头,简直打在了他的七寸上!他铺子里那些最赚钱的低档货,哪个离得开铅粉增白?
“哼,不知天高地厚的野丫头!”钱有福把罐子重重顿在柜台上,眼中闪过一丝阴鸷,“在西市地头上抢食,问过我钱有福了吗?去,给我查清楚!那摆摊的丫头什么来路?背后有没有人?”
很快,消息就传回来了:是两个年轻姑娘,看着像是小户人家的,没什么背景,就靠着点新奇玩意儿在西市外围瞎折腾。
钱有福冷笑一声:“没根基就好办!去,找几个机灵点的‘闲汉’,明天去她们摊子上‘照顾照顾生意’!”
第二天,季曼的摊子刚摆开不久,生意正好。几个穿着短打、流里流气的汉子就晃晃悠悠地围了过来,为首的是个脸上有疤、绰号“刀疤刘”的地痞。
“哟,小娘子,生意不错啊?”刀疤刘一脚踩在季曼铺着粗布的摊子边缘,咧着嘴,露出满口黄牙,眼神不怀好意地在季曼和苜蓿身上扫来扫去。
周围的客人一看这架势,纷纷面露惧色,悄悄后退。
季曼心头一紧,知道麻烦上门了。她强自镇定,脸上挤出一丝笑容:“几位大哥,想看看胭脂水粉吗?我们这‘凝玉雪’香粉……”
“看什么看!”刀疤刘粗暴地打断她,拿起一罐“凝玉雪”,在手里掂了掂,然后猛地往地上一摔!
“啪嚓!”粗陶罐子应声而碎,细腻雪白的香粉撒了一地。
“啊!”苜蓿吓得尖叫一声,脸都白了。
“就这破玩意儿?”刀疤刘指着地上的狼藉,声音陡然拔高,充满了恶意,“什么狗屁‘凝玉雪’!老子婆娘用了你这粉,脸都烂了!又红又肿,现在都出不了门!你这黑心的丫头片子,卖的什么害人的东西!赔钱!今天不赔个十两八两银子,老子砸了你这破摊子!”
他身后的几个混混也跟着起哄:
“对!赔钱!”
“害人的东西!砸了它!”
“不赔钱别想走!”
周围的摊贩和行人远远看着,敢怒不敢言。谁都知道这是玉香阁钱掌柜惯用的手段,这新来的小姑娘怕是得罪人了。
季曼看着地上那罐辛苦制成的香粉,心在滴血,但更多的是愤怒。她瞬间明白了这是冲着她来的,是恶意打压!她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掐进掌心。硬碰硬?她和苜蓿两个弱女子,对方人多势众,还都是地痞流氓,根本是自取其辱。报官?这种小纠纷,官差来了也是和稀泥,说不定还会被反咬一口。
怎么办?季曼脑子飞快地转着。示弱?赔钱?那以后就别想在这西市立足了!对方只会得寸进尺!
就在刀疤刘狞笑着伸手要掀翻整个摊布时,季曼猛地抬起头,脸上没有丝毫惧色,反而扬起一个极其夸张、带着浓浓讽刺的笑容,声音清亮地拔高,穿透了周围的嘈杂:
“哎哟!这位大哥,您婆娘脸烂了?那可真是天大的冤枉啊!”
她这一嗓子,带着一种唱戏般的抑扬顿挫,瞬间吸引了更多路人的目光。
刀疤刘被她这突如其来的反应弄懵了,动作一顿:“你……你什么意思?”
季曼上前一步,指着地上碎裂的罐子和散落的香粉,声音更大,字字清晰,确保周围所有人都能听见:
“诸位街坊邻居都看看!都评评理!这位大哥说他婆娘用了我们这‘凝玉雪’,脸就烂了?可真是奇了怪了!”
她弯腰,从地上沾了一点没被污染的粉末,直接抹在了自己脸上,动作干净利落:“大家伙儿瞧瞧!我这脸,天天用这粉!怎么没烂?反而越来越细嫩了?我小丫鬟苜蓿,大家伙儿眼熟吧?天天风吹日晒的,以前那脸糙得跟砂纸似的,现在用了这粉,是不是也光溜了不少?”她拉过吓得发抖的苜蓿,指着她的脸颊给众人看。
苜蓿虽然害怕,但**的话让她本能地挺直了背,她脸上确实因为用了自家产品,比之前细腻红润了许多,这是不争的事实。周围的街坊邻居仔细一看,纷纷点头,小声议论起来。
季曼不给刀疤刘插嘴的机会,语速飞快,气势逼人:“再说了,大哥!您口口声声说您婆娘脸烂了,是用了我们的粉!证据呢?您把她请来让大家伙儿看看啊!空口白牙就想讹人?我们这小本生意,辛辛苦苦赚点糊口钱容易吗?您这一张口就要十两八两?十两银子够买多少斤上等白面了?您婆娘的脸是金子镶的还是银子打的?这么值钱?”
她连珠炮似的发问,句句在理,又带着市井泼辣劲儿。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
“是啊,空口无凭就想讹钱?”
“这粉我看挺好的,我媳妇用了也没事啊……”
“十两银子?狮子大开口啊!摆明了欺负人小姑娘!”
刀疤刘被季曼这一套组合拳打得有点懵,脸上青一阵红一阵。他本来就是受人指使来找茬讹钱的,哪有什么证据?更不可能把他那根本不存在的“婆娘”叫来。眼看周围人的舆论风向不对,他恼羞成怒,凶相毕露:“臭丫头!牙尖嘴利!老子说烂了就是烂了!今天这钱你赔也得赔,不赔也得赔!”说着就要动手强抢摊子上的东西。
“慢着!”季曼猛地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高高举起——那是一块小小的、不起眼的木牌,上面刻着一个模糊的“聂”字纹样!这是她前些日子偷偷用木头仿刻的侯府徽记,一直藏在身上以备不时之需,没想到今天真用上了!
“这位大哥,还有各位街坊!”季曼举着木牌,声音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神秘和警告,“我们姐妹俩出来讨生活不易,但也不是毫无根底的!我家主人最是护短!您要是觉得这粉有问题,尽管去京兆府衙递状子!自有官府公断!可若是有人想仗势欺人、强抢硬讹……”她故意停顿了一下,目光冷冷地扫过刀疤刘几人,“那也得掂量掂量,惹不惹得起我家主人背后的……侯府!”
“侯府”两个字,如同惊雷炸响!尤其是在这平民聚集的西市,这两个字代表着绝对的权势和不可招惹!
刀疤刘伸出的手僵在了半空,脸上的凶悍瞬间被惊疑不定取代。他死死盯着季曼手里那块不起眼的木牌,虽然粗糙简陋,但那个“聂”字纹样……京城姓聂的侯府,只有那一家!宁远侯府!难道这丫头真是侯府里出来的?哪怕是侯府里最低等的下人,那也不是他这种地痞能随意欺辱的!钱有福可没告诉他这丫头有这层关系!
周围的议论声也瞬间低了下去,看向季曼和苜蓿的目光带上了敬畏和忌惮。宁远侯府!那可是真正的高门大户!
季曼见镇住了场面,趁热打铁,语气放缓,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强硬:“这位大哥,您婆娘的脸若是真出了问题,我们愿意请大夫、赔汤药费,该怎么着就怎么着!但若是存心找茬……”她掂了掂手里的木牌,冷笑一声,“那咱们就换个地方说话!”
刀疤刘额头冒出了冷汗。他不过是拿钱办事,可不想真惹上侯府这种庞然大物。他狠狠地瞪了季曼一眼,色厉内荏地撂下一句:“哼!算你狠!走着瞧!”便带着几个手下灰溜溜地挤开人群走了。
一场风波,被季曼一番连消带打、虚张声势地化解于无形。
看着刀疤刘等人狼狈离去的背影,季曼紧绷的神经才猛地一松,后背的冷汗已经浸湿了里衣。她放下举着木牌的手,才发现手臂都在微微颤抖。
“**……”苜蓿带着哭腔扑过来,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吓死奴婢了……您……您怎么敢……”
季曼拍了拍她的手,安抚道:“别怕,没事了。”她弯腰,心疼地收拾着地上碎裂的罐子和散落的香粉。看着那一片狼藉,她眼中没有丝毫退缩,反而燃起更烈的火焰。
权势!这就是权势带来的力量!哪怕只是狐假虎威,只是虚张声势,也能让那些魑魅魍魉退避三舍!
她想要安稳地赚钱,想要在这世上堂堂正正地立足,仅仅靠一个小摊,靠这点小聪明,是远远不够的!她需要一个更坚实的堡垒,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
“苜蓿,”季曼的声音带着一种破釜沉舟的决心,“从今天起,我们赚的每一文钱,除了必要开支,都存起来!我们要尽快,租一间铺子!一间属于我们‘醉花颜’和‘凝玉雪’的铺子!”
---
当季曼终于在西市边缘,一条不算太繁华但人流尚可的小街上,用积攒了大半年的辛苦钱盘下一间小小的、只有一丈见方的临街铺面时,那种脚踏实地的感觉,让她几乎落下泪来。
铺子很小,墙壁灰扑扑的,地面坑洼不平,但季曼和苜蓿却视若珍宝。她们自己动手,花了整整三天时间,用买来的最便宜的白灰刷了墙,找来平整的木板铺了地面。小小的柜台是请隔壁木匠铺的学徒用边角料打的,虽然粗糙,但打磨得很光滑。墙上钉了几排木架,用来摆放她们的产品。
开张那天,没有鞭炮,没有花篮。季曼请街口识字的老秀才写了块简单的招牌——“季记胭脂水粉铺”,端端正正地挂在了门楣上。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醉花颜”和“凝玉雪”终于有了一个固定的、体面的家。再也不用担心风吹日晒雨淋,再也不用担心地痞流氓随时掀摊子。
有了铺面,季曼的心思更活了。除了基础的胭脂和香粉,她开始尝试拓展产品线。利用鲜花提取的花露,她做出了带着自然花香、清爽滋润的“花露水”(当然,和现代的花露水功效不同,主要是护肤提神)。尝试用蜂蜡混合天然油脂和花瓣色素,做出了滋润唇部的“口脂膏”。虽然品种不多,但每一样都坚持“天然”、“安全”、“有效”的原则,价格依旧亲民。
口碑的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季曼那套“无铅养颜”的理念,加上产品实实在在的效果,逐渐赢得了越来越多回头客的信任。小铺子虽然位置偏僻,生意却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铜钱叮叮当当地流进来,渐渐变成了碎银子,又变成了小小的银锭子。
季曼没有停下脚步。她深知产品需要不断更新迭代。她开始尝试更复杂的配方,比如在“凝玉雪”里加入少量磨得极细的玉容散粉末(一种相对安全的中药美白方剂),提升养肤效果;尝试用不同的花瓣搭配,调出更丰富、更贴合不同肤色的胭脂颜色。
这天午后,阳光透过小铺子糊着素纸的窗户,洒下温暖的光斑。铺子里没有客人,季曼正伏在柜台后面一块干净的木板上,全神贯注地调配着一种新的胭脂膏体。她小心翼翼地滴入几滴新蒸馏的栀子花纯露,又加入一点点磨碎的紫草根粉调整颜色。鼻尖几乎要碰到陶碗,神情专注得仿佛在进行一项神圣的仪式。
苜蓿在一旁整理着货架上的小罐子,嘴里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心情显然极好。
就在这时,铺子那扇单薄的木板门被轻轻推开,门轴发出轻微的“吱呀”声。
季曼以为是熟客,头也没抬,习惯性地招呼:“欢迎光临,想看看什么?新到的栀子花露水,香气清雅,滋润不腻……”
“看看胭脂。”一个低沉清冷的男声响起,语调平淡,听不出什么情绪。
这声音……季曼握着小木勺的手猛地一僵,心头瞬间警铃大作!她倏地抬起头。
门口逆着光站着一个人。身量很高,穿着一身玄色暗纹的锦袍,腰间束着玉带,身姿挺拔如松。午后的阳光勾勒出他冷峻清晰的侧脸轮廓,正是那日在马车上惊鸿一瞥的宁远侯世子——聂桑榆!
他怎么会在这里?!
季曼的心跳瞬间漏跳了好几拍,随即又狂跳起来,几乎要撞出胸膛。不是心动,是惊疑、警惕和一种强烈的“麻烦上门”的预感!他认出自己了?来找茬的?还是……路过?
聂桑榆的目光淡淡地扫过这间狭小却收拾得干净整齐的铺子,掠过货架上那些粗陶小罐子,最后落在了柜台后季曼那张写满惊愕的脸上。他的眼神依旧深邃淡漠,看不出什么波澜,仿佛只是在打量一件普通的物品。
季曼强迫自己迅速冷静下来。她现在是“季记胭脂铺”的老板季曼,不是侯府那个卑微痴缠的庶女季曼!她深吸一口气,压下翻腾的情绪,脸上迅速堆起职业化的、无可挑剔的笑容,微微屈膝行了个礼,语气恭敬却疏离:“原来是世子爷大驾光临,小店蓬荜生辉。不知世子爷想看什么样的胭脂?是送人还是自用?小店有‘醉花颜’系列,色泽自然,都是鲜花汁子调制的。”
她刻意强调了“世子爷”这个称呼,点明身份,也划清界限。态度不卑不亢,完全是一个小商人面对贵客的恭敬姿态。
聂桑榆的目光在她脸上停留了片刻。眼前的女子,穿着半旧的细棉布衣裙,头发简单地挽着,脸上未施粉黛,却比记忆中那个在侯府后花园总是低着头、眼神躲闪的庶女要生动、明亮得多。尤其是那双眼睛,此刻虽然带着警惕和刻意的恭敬,却清澈有神,透着一股子蓬勃的生气和……防备?
他缓步走到柜台前,修长的手指随意地点了点季曼面前那个装着半成品栀子胭脂的粗陶碗:“这是什么?”
“回世子爷,这是新调的栀子胭脂膏,还在试验阶段。”季曼谨慎地回答,身体微微后倾,保持着距离。
聂桑榆微微倾身,靠近了些。一股清冽的、如同雪后松针般的冷冽气息若有若无地传来。他并未看季曼,目光落在陶碗里那呈现出温柔浅粉色的膏体上,鼻翼似乎几不可察地翕动了一下,捕捉着那清雅的栀子花香。
“花露?”他低声问了一句,听不出是疑问还是肯定。
季曼心头又是一紧。这世子爷鼻子倒是灵!“是,用了些新蒸的栀子花露。”她含糊道,不想透露太多细节。
聂桑榆直起身,目光重新落到季曼脸上,那眼神似乎带着一丝极淡的探究,又似乎什么都没有。他沉默了几息,就在季曼觉得空气都要凝固的时候,他才淡淡开口,语气依旧没什么起伏:“手法倒是新奇。只是……”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货架上那些简陋的包装:“终究是些小把戏,难登大雅之堂。”
这句话,像一根细小的冰刺,瞬间扎进了季曼刚刚因为事业小成而建立起的自信堡垒里。小把戏?难登大雅之堂?他凭什么如此轻描淡写地否定她的心血和努力?
一股强烈的屈辱感和不服输的劲头猛地冲上头顶!季曼脸上的职业化笑容几乎要维持不住。她紧紧攥住了袖中的拳头,指甲深深陷入掌心,才勉强压下那股顶撞回去的冲动。
她深吸一口气,再抬起头时,笑容反而更灿烂了几分,眼神却冷了下来,带着一种针锋相对的锐利:“世子爷说的是。小女子这点微末伎俩,不过是糊口的小营生,自然入不了您的眼。大雅之堂自有珠玉在前,小店只求为市井姐妹添几分颜色,便心满意足了。世子爷若是想寻那大雅之物,出门右转,玉香阁的东西或许更合您的心意。”
她这番话,绵里藏针。先是自贬,承认自己“小把戏”、“难登大雅”,紧接着却点明了自己的定位和客户群体——为市井女子服务。最后,更是直接把这位高高在上的世子爷往竞争对手“玉香阁”那边推,意思很明显:您这种“大雅”之人,就别屈尊降贵来我这“小把戏”的铺子了,慢走不送!
聂桑榆的眉梢几不可察地挑动了一下。似乎没料到这小商人敢如此……伶牙俐齿地回敬他。他看着季曼那双强压着怒火、亮得惊人的眼睛,里面没有半分痴迷和怯懦,只有清晰的抗拒和不服输的倔强。
他薄唇微抿,并未因季曼的顶撞而动怒,只是那深邃的眼眸里,似乎掠过一丝极淡、极快的,类似于……兴味的光芒?快得让人以为是错觉。
他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看那些胭脂水粉,只是又淡淡地扫了季曼一眼,仿佛只是确认了什么,便转身,步履沉稳地离开了小铺。玄色的衣袍消失在门口的阳光里,如同他来时一样突兀。
铺子里恢复了安静,只剩下季曼有些急促的呼吸声和苜蓿大气不敢出的紧张。
“小……**……”苜蓿的声音带着哭腔和恐惧,“您……您怎么敢那样跟世子爷说话啊!他会不会……”
季曼站在原地,胸口还在剧烈起伏,方才强压下去的愤怒和屈辱感此刻才后知后觉地翻涌上来,烧得她脸颊发烫。她看着聂桑榆消失的方向,眼神复杂,有后怕,但更多的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决绝和莫名的委屈。
“怕什么?”季曼的声音有些发哑,却异常坚定,“他说得对,我就是个小商人,做的就是市井小民的生意!我的东西好不好,我的客人说了算,轮不到他一个高高在上的世子爷来评头论足!”她猛地转过身,拿起那个装着栀子胭脂膏的陶碗,看着里面柔和的粉色,眼神重新变得锐利而专注,“登不登大雅之堂?哼!我偏要做出名堂来!苜蓿,关门!今天不营业了!我们研究新配方!”
聂桑榆那句轻飘飘的“小把戏”,像一根刺扎在了季曼心上,非但没有将她打倒,反而彻底激起了她的斗志和野心。她要搞钱,要搞大钱!要做出让所有人都无法轻视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