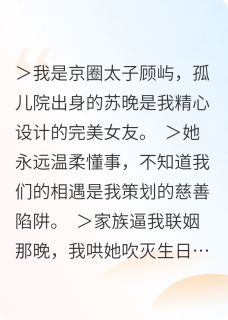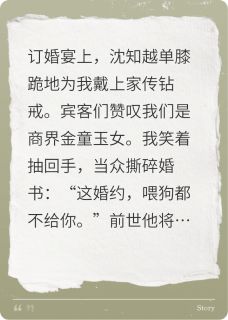1饥饿之吻雨停后的第七天,空气里的霉味混着远处隐约的腐臭飘进窗缝,
林深把最后半块压缩饼干掰成几乎均等的两瓣,指尖蹭过苏晚干裂起皮的唇角时,
她忽然偏头咬住他的拇指,不是调情,是真的用了点力气,
像只饿急了的小兽在确认食物的真实性。“省着点吃。”他低声说,声音哑得像被砂纸磨过,
另一只手却摸出藏在床垫下的玻璃罐,里面是前几天冒险找到的半罐蜂蜜,
用干净的木片刮了薄薄一层,先抹在她唇上,才小心地舔掉自己指腹上的那点湿意。
罐头空了三个,打火机还剩四分之一油,苏晚昨晚咳得厉害,
他翻遍了整个药店只找到半盒过期的止咳糖浆,
现在正用酒精棉片仔细擦着她发梢沾到的泥点——那是今早为了抢一袋未开封的全麦面包,
她被一只瘸腿的感染者扑倒时蹭上的,他开枪打碎那东西的头骨时,
子弹擦着她的耳朵飞过去,现在耳垂还泛着不正常的红。“明天去东边的罐头厂看看。
”他把最后一口饼干塞进她嘴里,看着她费力地咀嚼,忽然低头在她额角亲了一下,
那里有块新结的疤,是上次为了护他,被碎玻璃划的,“找到黄桃罐头,给你当嫁妆。
”苏晚笑出声,牵扯到喉咙又开始咳,他赶紧把那半盒糖浆递过去,看着她皱着眉喝下去,
忽然想起灾难前,她最讨厌吃罐头,说防腐剂太多,那时候他总笑她娇气,现在却觉得,
能让她皱着眉吃下去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窗外传来感染者嘶哑的嘶吼,
他把苏晚往怀里紧了紧,摸了摸腰间的砍刀,刀刃上的血迹还没擦干净,但他知道,
只要他还有力气挥刀,就能让她多睡一个安稳觉。后半夜起了风,
卷着碎玻璃碴子打在窗板上,像有什么东西在外面磨牙。林深把苏晚往墙角推了推,
自己抵着门板坐,手里的砍刀被体温焐得温热,刃口却泛着冷光。苏晚睡得不安稳,
呼吸里总带着点痰音,手在黑暗里摸索,抓到他的衣角才踏实些。林深低头看她,
月光从窗缝漏进来,刚好照在她眼下的青黑上。前几天为了找干净的水源,
他们在地下停车场困了整整两天,她一直抱着那桶五加仑的矿泉水,说什么也不肯松手,
直到现在手腕还有圈红印。“渴……”她迷迷糊糊地哼唧,林深赶紧摸过床头的军用水壶,
拧开时特意放慢了动作,怕金属摩擦声引来不该来的东西。壶里的水只剩小半,
是昨天在超市顶楼的消防栓接的,带着股铁锈味。他先喝了一口,确认没异味,
才小心地往她嘴里送。2生死相依水流过喉咙的声音在寂静里格外清晰,
苏晚吞咽时忽然睁开眼,睫毛上沾着点灰,像只受惊的鸟。“听到了吗?”她抓着他的手腕,
指尖冰凉,“好像有东西在撞门。”林深侧耳听,风声里确实混着钝重的撞击声,一下一下,
带着某种规律。他把水壶塞回她手里,抄起砍刀站起身:“你躲进衣柜,锁好门。”“不要。
”苏晚攥着他的裤腿,指节泛白,“我跟你一起。”她的声音发颤,
却把那把他给她防身的折叠刀握得更紧了——那是灾难前他送她的生日礼物,
当时包装成了拆信刀的样子,现在刀刃上已经崩了三个小口。撞击声越来越急,
门板开始吱呀作响,最下面的缝隙里,能看到一只沾满黑泥的手在胡乱抓挠。
林深突然想起下午路过三楼时,看到走廊尽头有个穿保安制服的感染者,
脖子被扭成了九十度,走路时总往左边偏,现在这撞门的力道,倒像是那东西。“数到三,
你往左边躲。”他压低声音,脚往门后垫了个铁皮箱,“我开门时会吸引它注意力,
你趁机去拿桌子上的消防斧。”苏晚点头,牙齿咬着下唇,
把水壶塞进怀里——那是他们现在最宝贵的东西。林深最后看了她一眼,
突然想起三年前在公司楼下,她也是这样咬着唇看他,说被主管刁难了,
当时他还能搂着她去喝杯奶茶,现在却只能让她跟着自己提心吊胆。
门板“咔嚓”一声裂了道缝,那只手猛地伸进来,指甲缝里全是暗红的血垢。林深数到三,
猛地拉开门闩,铁皮箱被撞得往后滑了半米,他借着惯性往右侧翻滚,
砍刀劈下去时带着风声,正砍在那东西的肩膀上。腐肉的腥臭味瞬间涌进来,
比垃圾桶里发酵的烂菜叶还冲。感染者嘶吼着转身,歪着的脖子让它只能用一只眼瞪人,
涎水顺着下巴往下滴,落在林深的裤脚上。苏晚没按计划去拿斧头,反而扑过来抱住它的腰,
尖叫着往墙上撞——她的力气其实小得可怜,平时拧瓶盖都要他帮忙,现在却像只炸毛的猫,
指甲深深抠进那东西后背的烂肉里。“滚开!”林深吼着拽开她,
刀刃从感染者的下颌**去,搅了半圈才**。黑红色的液体喷了他一脸,他抹了把脸,
刚想骂她不要命,就看见苏晚蹲在地上干呕,手指在发抖。“不是让你躲起来吗?
”他的声音硬邦邦的,却蹲下去拍她的背,掌心能摸到她肩胛骨硌人的形状。
这几个月她瘦得太快,以前穿的牛仔裤现在要系两根腰带才能不掉。
“它要咬你……”苏晚咳得眼泪都出来了,抓着他的胳膊看,“没咬到吧?有没有伤口?
”她的手指划过他的手腕、脖颈,
摸到他耳后那道旧疤时顿了顿——那是灾难刚开始时被碎玻璃划的,当时她抱着急救箱哭,
说要是他死了她也不活了。林深把她拉起来往屋里走,关门时特意用铁链缠了两圈。“没事。
”他拿过毛巾擦她脸上的灰,“下次不许这样了。”“那你也不许逞英雄。
”苏晚抢过毛巾给他擦脸,摸到他下巴上的胡茬,忽然踮脚亲了亲,“你死了,
谁给我找黄桃罐头当嫁妆。”3罐头之约窗外的风停了,远处传来几声枪响,断断续续的,
像在敲闷鼓。林深把她抱到床上,往她手里塞了个暖水袋——是用输液瓶灌的热水,
裹了两层旧毛衣。“睡会儿,天亮了去罐头厂。”苏晚点头,
却睁着眼睛看他整理装备:子弹还剩七发,砍刀需要磨,背包里的压缩饼干只剩两包,
她的止咳糖浆见底了。林深把那半盒糖浆塞进内袋,又把她的折叠刀换了个新刀片,
才躺到她身边。“林深,”她忽然开口,声音很轻,“你说我们能活到冬天吗?
”林深沉默了一下,冬天意味着要找取暖的东西,意味着感染者可能会更活跃,
意味着食物会更难寻。但他摸了摸她的头发,说:“能。找到罐头厂,
我们就找个带地下室的房子,生个炉子,我给你腌酸菜,像我老家那样,用大缸,
一层菜一层盐,能吃到开春。”“你还会腌酸菜?”苏晚笑了,往他怀里钻了钻,
“以前怎么没说过。”“你以前只关心哪家奶茶店出了新品。”他捏了捏她的脸,
那里的皮肤比以前粗糙多了,却还是软的,“等安定下来,我给你做。
”其实他根本不会腌酸菜,只是小时候看奶奶做过。但他知道,现在的苏晚不需要真相,
只需要个盼头。天蒙蒙亮时,林深被冻醒了。苏晚把腿压在他肚子上,睡得正香,
嘴角还沾着点糖浆的痕迹。他小心翼翼地挪开她的腿,起身检查装备,
发现打火机的油比昨天少了些——昨晚为了让她睡得暖和,他在铁盆里烧了半张报纸。
收拾东西时,苏晚醒了,揉着眼睛看他把最后一点干粮塞进背包。“我做了个梦。”她说,
声音还有点哑,“梦见我们在电影院看电影,你买了桶爆米花,上面撒满了糖。
”林深把她的鞋带系成死结,抬头时看见她眼里的光,像蒙尘的星星。“等找到安全区,
带你去看。”他说,“买最大桶的,让你吃到腻。”其实他知道,安全区早就成了空城。
上周在广播里听到断断续续的信号,说北边的基地被攻破了,幸存者寥寥无几。
但他不能告诉她,有些希望,哪怕是假的,也得攥在手里。出门时特意绕了远路,
避开主干道。街面上散落着翻倒的汽车,有的还在冒着青烟,玻璃碎片像鱼鳞一样铺在地上。
苏晚紧紧跟着他,脚步很轻,像只训练有素的猫——以前她总爱踩水坑,
说溅起的水花像烟花,现在却能在碎玻璃上走得悄无声息。路过一家便利店时,
林深让她在门口等着,自己进去翻找。货架倒了大半,罐头全被人撬开过,只剩下些碎纸屑。
他在冰柜后面摸到个硬纸包,打开一看,是袋没开封的巧克力威化,包装上落着层灰,
生产日期是灾难前三个月。“找到了好东西。”他走出去,把威化递给苏晚。她眼睛亮了亮,
却没立刻拆开,而是塞进他的口袋:“你留着,你昨天没怎么吃东西。”“给你就拿着。
”林深把威化拆开,塞了一块进她嘴里。巧克力在舌尖化开,带着点廉价的甜,
苏晚眯起眼睛,像只吃到糖的小兽。他看着她,忽然想起灾难前的情人节,
他送她的那盒费列罗,她嫌太甜,只吃了一颗就全给了他。
4感染者突袭走到罐头厂附近时,林深让她躲在废弃的卡车后面,自己先去侦查。
厂门被撬开了,地上有新鲜的脚印,还有几滴没干透的血。他握紧砍刀,贴着墙根往里走,
仓库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有人在翻东西。“谁在那里?”他低喝一声,
砍刀横在胸前。角落里站起来个瘦高的男人,手里攥着根钢管,看到林深手里的刀,
往后缩了缩:“别、别动手!我没恶意!”林深皱眉,那人穿着件破棉袄,脸脏兮兮的,
怀里抱着个铁皮盒,里面装着半盒发霉的饼干。“就你一个?
”“还有我女儿……”男人指了指旁边的麻袋,麻袋动了动,露出个小脑袋,
大概五六岁的样子,眼睛又大又亮,正怯生生地看着他。
林深松了松握着刀的手:“有感染者吗?”“东边仓库有几只,被我锁起来了。
”男人咽了口唾沫,“我就来拿点吃的,马上走。”苏晚不知什么时候跟了进来,
手里还攥着那半块威化,看到麻袋里的小女孩,愣了一下,把威化递了过去。
小女孩怯怯地看了看男人,男人点点头,她才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啃着。“你们要去哪里?
”男人看着林深,眼神里带着点试探,“罐头厂早就被搬空了,后面还有几只厉害的,
会爬墙。”林深心里一沉:“什么时候的事?”“昨天下午来的,
我亲眼看见它们从围墙上翻过去,跟猴子似的。”男人叹了口气,
“本来想带女儿找点开罐...林深的衣角,指尖在布料上掐出几道白痕。
他顺着她的目光看向仓库深处,那里堆着半人高的纸箱,阴影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走。”他当机立断,拽起苏晚的手腕就往外退,同时朝那男人低喝,“带孩子跟紧!
”刚跑到厂区门口,身后就传来“哐当”一声巨响,像是铁架被撞翻了。苏晚回头看了一眼,
脸色瞬间白了——三只感染者正从仓库顶上爬下来,四肢着地,动作快得像野猫,
其中一只的肋骨都露在外面,却丝毫不受影响,爪子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声。“它们来了!
”男人抱着女儿往前冲,小女孩吓得闭紧眼睛,死死搂着父亲的脖子。
林深把苏晚往身后护了护,挥刀劈向扑过来的第一只感染者。刀刃卡在那东西的锁骨里,
他猛力一拧,黑血溅了苏晚一裤腿,她却没像往常那样躲,反而捡起地上的根钢管,
往另一只感染者的膝盖砸去。“砰”的一声闷响,那东西踉跄了一下,
林深趁机抽刀砍断了它的脖颈。第三只已经扑到眼前,他能闻到它嘴里的腐臭味,
情急之下拽过旁边的铁桶挡了一下,桶身被撞出个凹坑,他借着反作用力把苏晚推出大门,
自己跟着滚了出去。“快跑!”他爬起来就拽她,厂区的铁门早就锈得不成样子,
现在被撞得摇摇欲坠。男人已经跑出了十几米,怀里的小女孩还在哭,
哭声在空旷的街道上格外显眼。跑过第三个路口时,林深突然停住脚。苏晚喘得说不出话,
扶着他的胳膊弯腰咳嗽,指缝里漏出的气都带着颤音。他往身后看,感染者的嘶吼声远了些,
但没彻底消失,像条甩不掉的影子。“进那边的楼。”他指着街角的居民楼,
楼道口堆着些废弃家具,看着像是有人清理过。男人也跟着停了下来,额头上全是汗,
怀里的孩子哭累了,趴在他肩上抽噎。楼道里弥漫着股消毒水的味道,林深打头阵往上走,
每一步都踩得极轻。二楼的防盗门虚掩着,他推开门时,里面传来“咔哒”一声,
像是金属扣被碰响了。“谁?”一个苍老的声音响起,紧接着是拐杖敲击地面的声。
林深握紧刀,看到沙发上坐着个老太太,怀里抱着只黑猫,猫的眼睛在昏暗里亮得吓人。
“我们路过,想借个地方歇歇脚。”林深放缓语气,注意到老太太身边的茶几上摆着个空碗,
碗边还有点粥渍。老太太没说话,只是用浑浊的眼睛打量他们,
视线在苏晚沾血的裤腿上停了停,又移到男人怀里的孩子身上。黑猫突然弓起背,
冲着门口“喵”了一声,林深立刻回头,看到楼梯口有团黑影晃了晃。“把门锁上。
”老太太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像磨砂纸,“第三级台阶松了,别踩。
”5地窖逃生男人赶紧过去锁门,林深扶着苏晚走到沙发边,
才发现这屋子收拾得异常干净,地板擦得能照见人影,窗台上还摆着盆仙人掌,绿油油的,
在末世里显得格外突兀。“喝口水。”老太太指了指茶几上的水壶,“凉白开,今早刚烧的。
”苏晚倒了杯水,手还在抖,水洒了些在桌面上。老太太看着她笑了笑,
那笑容里带着点苍凉:“小姑娘胆子倒大,刚才拿钢管砸那东西的时候,眼睛都没眨。
”苏晚脸一红,低头盯着自己的鞋尖。林深替她解释:“她就是急了,平时连杀鸡都不敢看。
”“现在哪有时间怕。”老太太摸了摸黑猫的背,“我家老头子以前是屠夫,杀了一辈子猪,
结果呢?被隔壁楼的小王啃了半张脸。那孩子以前总来我家蹭红烧肉,
说我做的比他娘做的香。”男人抱着孩子在旁边的小马扎坐下,低声问:“您一个人在这儿?
”“还有煤球。”老太太拍了拍怀里的猫,“它会抓老鼠,饿不着。
”林深注意到墙角堆着十几个矿泉水瓶,都装满了水,标签上的日期都是最近的。